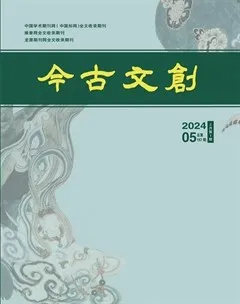后人類視域下看科幻作品中的靈肉觀
【摘要】本文嘗試在后人類相關理論的研究基礎上,通過對讀《攻殼機動隊》和《電子螞蟻》這兩個文本作品,具體分析兩部作品的藝術構思,解讀文本中所呈現的權力運作機制,以及它們各自致力于探討的身份體現形式與判斷標準,逐步切近后人類文藝中關于靈與肉之間的相關思考與探討,同時也是對后人類時代生命形式的多樣性與不確定性的一種分析式解讀。
【關鍵詞】后人類;《電子螞蟻》;《攻殼機動隊》;靈肉觀
【中圖分類號】I106?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4)05-003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05.011
一、對讀兩個文本的藝術構思
(一)《攻殼機動隊》的賽博格特色
《攻殼機動隊》是賽博朋克電影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影片,自上映起就引起了轟動。這說明在科技迅速發展的過程中,人類社會慢慢進入后人類社會的場域中。科技的進步能讓人類通過生化技術、電子零件將自己變得電子機械化,從而不斷地刷新生物技能的極限,強化人類的身體機能,以此更好地來適應后人類社會中科技高速發展的沖擊。在后人類領域中賽博格的形態來源于控制論和有機體,是機器與生物體的混合體。后來這個概念被放大,是指為了讓生物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將人與非有機體結合而形成新的生命形態。賽博格的出現,引發了人們對于“人”的定義的重新釋義和理解。
在真人電影版《攻殼機動隊》中,影片一開始就介紹了政府出資成立研發的軍用生化人,使得人和機器的界限更加模糊。主人公草薙素子就是這么一個混合體式的存在,草薙素子是典型的“賽博人”,她在一次事件中受到了攻擊,身體完全破損,無法挽救,只有大腦功能正常,因此公安九課給素子安上了新的義肢,將她的大腦植入到新的身體中去,可以說接受了移植的素子現在是一種人機結合的新生物。素子的大腦移植到生化電子義體內,同時擁有了機器的能力和人類的情感。
在未來社會,人類也許會進入到“義體化時代”,通過接受義體手術,獲得了肉體的強大機能。哈拉維在她的《賽博宣言》中曾說:“我們都是賽博格。”[1]這種說法有其極端性,但是科技的發展似乎正在逐漸驗證她的觀點。隨著科技和信息的高速發展,互聯網、大數據無形中結成一張網將所有人都連接起來,手機成為人們獲取信息的重要工具,可以說,人與手機的“結合”關系就是人的初級賽博格化。這一點,在真人版電影《攻殼機動隊》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影片中除了故事情節的編排充滿了賽博格特色外,畫面的呈現和城市的設定也充滿了賽博朋克的特點。影片背景設定的是未來的日本,但城市中隨處可見的中文,日文,英文等影像交雜其間,體現了未來文化的多樣性、交互性,與更徹底的混雜性,似乎也在呼應著人的多種成分構成的軀體。
(二)《電子螞蟻》的人工智能特色
《電子螞蟻》是菲利普·迪克《少數派報告》中的一篇短篇小說,以后人類時代人工智能和生化技能為背景來進行描寫。主人公加森·普爾是一個電子仿生人,也就是小說中所描述的電子螞蟻。與賽博格不同,電子螞蟻不是人機結合的產物,而是純粹的人工智能。在小說中,普爾被植入記憶來幫助人類管控地球上的公司,在他受傷后知道自己仿生機器人的身份后,人們對他的稱呼從“普爾先生”變成“普爾”,這說明在后人類社會中人工智能即使發展進化到相當成熟的程度,其地位和人類相比還是差殊有別的。人工智能作為一種人造生命形式,即使發展到了“形神兼備”能獨當一面的階段,依然是人類的附屬品與工具,這就提出了人工智能與人類之間的倫理問題。而加森·普爾在知道自己是電子螞蟻的時候,多次做實驗自證存在形態。這也說明人工智能從弱人工智能發展到強人工智能的過程中逐步產生的社會問題。
(三)靈肉的后人類式優化與毀滅
在后人類社會中,人類生命形態的越來越多樣化與復雜化,使得身體與心靈的靈肉關系問題成為一個必須面對的倫理問題。笛卡爾在《方法論》(Discourse on the Method)的開頭就說過:理性“是使人成其為人、將人與野獸區分開來的唯一東西”;理性賦予主體以判斷和思考的力量,也成為衡量人之所以有別于其他物種而成其為人的標準,因而有所謂“我思故我在”的著名斷言。[2]這就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假設:假如打破了人類生理的自然進化規律,靈與肉結合的最終出路到底在哪里?這兩部作品向人們提供了兩個不同的思考視角。在《攻殼機動隊》中,草薙素子作為第一個全身義體化的賽博人,她幾乎無所不能,擁有了人類所不能擁有的超級能力。但是她同樣有自己的困惑,那就是靈魂與肉體之間難以找到一個平衡性,無法找到判斷自己生命存在的真正依據,靈魂的獨一無二性和肉體的可修復性使素子不斷地對自己的身份認定產生疑惑。在這種疑惑與釋疑的過程中,素子逐漸找到了接近心中的答案的路徑——根據記憶來追尋自己的過往。在和傀儡師的對抗中,素子找到了自己的價值,也完成了更高階的進化。所以素子應該算是完成了人類向后人類的最終進化,成為人類形態的終結但同時也是后人類形態的起始,最終完成了靈肉的后人類式優化。
在《電子螞蟻》中,加森·普爾作為一個人工智能性的機器人,已經屬于一種強人工智能,他在知曉自己的電子螞蟻身份后的第一反應就是用自殺來尋求自證和自我毀滅。普爾在自己身上一共做過四次試驗來證明和拆解自己所感知過的現實世界的存在機理。在最后一次實驗中,他同時經歷了各種各樣的視覺、觸覺、味覺、嗅覺和聽覺體驗以及“所有的語言”。這剎那的永恒后,他的自我已經隨著報廢的處理系統消失,他也“死”了。在感受過一陣短暫的永恒之后,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這與《攻殼機動隊》里的素子代表的賽博格不同,普爾所代表的人工智能無法承受這種存在的虛無感而最終走向毀滅。這也說明在后人類時代,人工智能雖然作為一種工具比賽博格更容易操控,但也會產生自我意識,為了尋求掌握自我而進行飛蛾撲火的毀滅。
二、后人類靈肉觀背后的權力機制
(一)靈肉錯位背后的權力博弈
在《攻殼機動隊》和《電子螞蟻》中,最突出的藝術構思就是靈與肉之間的撕裂與糾纏。在《攻殼機動隊》,素子一直在靈魂與肉體錯位之間做選擇,作為第一個全身化的義體人,素子雖然重新獲得了自己的容貌和軀體,但是這個并非是獨屬于她一個人的肉身或外殼特征。雖然素子擁有獨立意識,但是靈魂的獨一無二性和肉體的可操控性、隨意更換之間呈現出一種割裂甚至對立的關系,這種人工匹配讓素子產生了困惑。因為肉體缺乏獨特性而無法確定自己靈魂的真實性。素子雖然擁有自己的靈魂,但是目睹運送垃圾車的駕駛員被隨意篡改記憶一事引起了素子更深層次的迷惑,如果記憶都可以是虛假的,誰又能保證自己所擁有的靈魂也是真實的呢?在這種靈肉不斷博弈的過程中,素子選擇了前者,那就是靈魂的不可或缺性。
而在《電子螞蟻》中,普爾對于肉體的執念相比素子來說更加深刻,盡管是一個仿生機器人,但他渴望人皮表層覆蓋著真肉,鮮血充滿靜脈和毛細血管,而并不是線圈電路與微型組件。在知道自己是電子仿生人的身份后,在靈肉博弈之間選擇了肉體,在感受過短暫的永恒之后,選擇了自我的毀滅。在未來社會,電子人被增強的力量使他們成為人類理想的奴工。對于人工智能來說,支撐他們存在的基礎就是自己的記憶,記憶成為他們與社會互動所留下的痕跡,但基礎被毀滅,痕跡被抹去,仿生人陷入一種虛無的絕望之中。普爾的絕望并在于身體的異類性,而在于自己對人造記憶真相發現后的憤怒、絕望。
在后人類時代,不管人工智能還是賽博格,都必須要有技術的支撐才能得以更好地發展。西方學術界談論的一個新概念——技術奇點,很好地說明了后人類社會科技給社會帶來的影響。技術奇點的含義是:技術的進步可能由量變產生突然的質變,在極短的時間里徹底改變人類世界的狀態。[3]而技術的成熟在逐漸證實這一命題。不管是賽博格還是人工智能,都是在技術成熟下催生的科技產品,背后獲利的只是少部分擁有權力資源的人。
(二)靈肉觀與其引發的倫理關系
科技的高速發展必定是一把雙刃劍,在這種情況下,隨著人機結合的程度越來越普遍,人和機器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背后的科技倫理關系也開始逐漸引發人們的關注和討論。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引起關注的不只是科技發展帶來的爭議,而且還有涉及情感、道德、政治、經濟等倫理關系。在《攻殼機動隊》中,公安九課是政府最得力的權力機構,阪華機械工業的背后也是政府出資建設的。盡管科技急速發展,但最終也是為擁有更高權力的統治階層服務,作為第一個全身義體化的賽博人,素子的存在一開始只是作為政府的一個武器,作為政治的附屬品,人類創造出完美的接近“上帝”的賽博格,擁有一切常人難以擁有的非凡能力,即使擁有獨立意識,也不能避免成為政治的附庸物。賽博格的出現是經濟全球化的產物,是資本、權力、商品經濟的奴隸,“與剝削的技術,權威的順從和豐富的時尚緊密結合在一起”。[4]
所以在《電子螞蟻》中,貝氏夫婦居住到普羅克斯四號星球上,地球上的各種公司事務交給仿生機器人處理。仿生人成為被剝削的對象,擁有著虛假的記憶,成為人類的理想的奴工。在迪克的其他小說中可以看到,后人類時代,科技發展的愈加成熟。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所說的“剝削現象”會更加突出,優勝劣汰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顯得更加殘酷和血腥。
三、后人類靈肉觀背后的身份體現
(一)記憶與身份的關聯
科幻作品中關于賽博格和人工智能最大的特點離不開記憶的設定。如果說后人類時代的主要標志是以人為進化取代自然進化的話,那么,以記憶人為植入取代記憶自然形成便是上述標志的具體化。[5]在這兩部作品中,也均有這種記憶的設定。
《攻殼機動隊》中素子的對自身生存困境的困惑正是來自對于記憶的不牢固性。記憶可以隨意被植入,被篡改。如果連記憶都是虛假的,那生命存在的基礎是什么?由此引發的身份認同危機引起人們的反思。賽博格作為一種人機結合的生命體,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雖然具備了人的實體屬性,但缺少了社會身份的認同。在這種尋求真相的過程中,素子因運送垃圾車的司機隨意植入的虛假的記憶而受到沖擊,開始陷入一種主體身份的認同危機中。記憶都可以是虛假的,那靈魂還能保持真實嗎?人格同一性問題開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記憶的“虛假性”和當下意識的“瞬間性”都源自人類的內感覺。而前者在電影里用來解構人格同一性問題。在電影中,大家可以看到,素子第一時間就去找尋記憶中的真相。在影片最后,素子體會到了存在的真正意義,不管記憶是真是假,只有人性才是我們的優點。這也是《攻殼機動隊》給予大家的一種后人類式價值認定。
但在《電子螞蟻》中,主人公因為知道自己所擁有的記憶是植入的,認為自己只是一個傀儡,是一個努力模仿活人,自己卻沒有生命的東西。于是他多次對自己的現實磁帶做出改變,以此來感知自我的存在。對于主人公加森·普爾來說,記憶被突然告知是虛假的,打破了他在社會中存在的根基,對于他來說,自我存在的基礎就是自己的記憶。記憶的虛假性,直接宣告了他在現實世界中身份的破敗,瓦解了他心中生命存在的神圣性,于是最終選擇自殺。這可能也是人工智能最終不同于賽博格的特點,自我存在的人造性特征難以擺脫,而只有自主身份獲得認同才能喚起他們對于存在的意義感知。所以在后人類文藝作品中,人類總是通過植入記憶使仿生人獲得依賴感,獲得合理的人類可接納的身份,從而使他們可以更好地被操控,同時也是引發倫理問題的根源。
(二)肉身與身份的構建
在后人類社會中,靈肉關系一直是討論的一個重要維度。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認為身體和靈魂可以分開而獨立存在,“我思故我在”,只要意識存在,那么我就存在。技術只不過是身體的外化或延伸,最重要的是人的主體性精神。但是尼采提出“靈魂假設”拒絕這一理性思維,明確提出一切以身體為出發點。也就是說身體是人的根本,身體規定人的本質,人首先是身體的存在,而理性不過是身體的附著物。持這一觀點的還有福柯,他認為社會的實踐形式和組織內容都是圍繞著身體來展開的。德國學者克里斯蒂安·馮·沃爾夫的“一元論”認為身體和靈魂不過是同一種更高等級的物質在此世的不同表現形式。《攻殼機動隊》里素子就是因為肉體被取代而產生生存困惑。就如同“特修斯之舟”一樣,船身的零件被慢慢替換,直到最后,所有的零件都被替換成功,那它還是原先的那艘船嗎?在義體取代肉身的過程中,一開始與機械肉身緊密貼合的靈魂又是否是最原始的那一個呢?即使義體生產出來的型號也只有一個,但改變不了的是肉體已經被替換。素子無法回到當時靈肉合一的狀態,所以才會無法順利建構自我存在的合理身份。
同樣《電子螞蟻》中,普爾對于肉體的執念更深,雖然作為一個仿生電子人,他已經完全適應人類的生活,但是支撐他生活的是一個人類的自然生命,并不是一個傀儡人的身份。在小說中,當他電子螞蟻的身份被證實的時候,人們對于他的稱呼也從普爾先生變成了普爾,人們賦予電子螞蟻的社會倫理價值立即消解為一種工具性符號。所以一旦這種存在的基礎被打破,無法完成對于身份的建構,且無法獲得社會的認同,自我認知無法獲得重構,最后結局走向消亡。
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一種后人類主義理論逐漸出現在大家眼前,無數科幻作品向人們展現了后人類社會的什么,人類又該如何重新定義自己?而人之所以為人,并不是在于其所能,而是在于其所不能,若一旦突破某種肉體和精神的壁壘而逐漸走向無限時,必將承受重新釋義自我本身的困惑。雖然科技的發展,必會催生一種身份危機。這也說明,人類在進化過程中也將會重新認識世界,認識自我。而在這個過程中,立場一旦被確定,不管是正義的還是非正義的,都意味著選擇了一種對應的身份,來完成自己的生命軌跡。
參考文獻:
[1]段慧.英美后女性主義媒介批評研究[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18.
[2]孫邵誼.當代西方后人類主義思潮與電影[J].文藝研究,2011,(9).
[3]劉慈欣,吳巖.劉慈欣談科幻[M].武漢: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
[4]王逢振.外國科幻論文精選[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
[5]黃鳴奮.科幻電影創意:后人類視野中的記憶體系(三)——挑戰與應對[J].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1).
作者簡介:
晉華敏,女,山西大學文學院文藝學專業在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