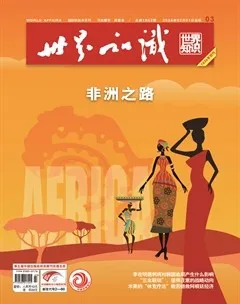政治自主之路:民主為先還是治理為重
曹文娟?沈曉雷
2023年,非洲政治形勢在總體穩(wěn)定之下仍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動蕩,其中尼日爾和加蓬因軍事政變引發(fā)政局變動,廣受外界關(guān)注。非洲自2020年以來進入新一輪“政變潮”,這被西方學(xué)界普遍視為非洲民主衰退的標志,但他們卻有意忽視了西式民主并不適合非洲現(xiàn)實和將民主輸出置于國家治理之上的危害,罔顧相關(guān)國家反對西方新殖民主義的呼聲。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意識到西方強加給非洲的模式并不適合這片大陸,更加傾向于自主探索政治發(fā)展之路。
自2020年8月西非國家馬里發(fā)生軍事政變以來,非洲進入新一輪“政變潮”。2021年,馬里再次發(fā)生軍事政變,幾內(nèi)亞和蘇丹也發(fā)生軍事政變,尼日爾則發(fā)生未遂政變,乍得政權(quán)更替也被普遍視為“軍事政變”。2022年,布基納法索先后發(fā)生兩次軍事政變,幾內(nèi)亞比紹、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與岡比亞則發(fā)生未遂政變。2023年,尼日爾和加蓬發(fā)生軍事政變,布基納法索、塞拉利昂和幾內(nèi)亞比紹則先后發(fā)生未遂政變。

2023年9月2日,數(shù)千名尼日爾民眾聚集在法國駐尼日爾首都尼亞美的軍事基地門前舉行抗議示威,反對法國軍隊留在尼日爾。2023年12月22日,最后一批法國駐軍撤離尼日爾。
相關(guān)國家發(fā)生軍事政變后,軍政權(quán)均建立過渡政府、設(shè)定過渡期并承諾過渡期結(jié)束后舉行民主選舉以“還政于民”。然而由于軍事政變是以“違憲”方式更替政府,因而遭到了非洲聯(lián)盟和西非國家經(jīng)濟共同體等組織的強烈譴責(zé)與制裁。美國等西方國家也對此異常關(guān)注,不但對相關(guān)政變進行譴責(zé),更宣稱這些政變標志著非洲民主出現(xiàn)重大衰退。事實上,自2016年以來,西方學(xué)界便不斷鼓吹非洲民主衰退的論調(diào),宣稱“非洲民主化進程已經(jīng)停滯甚或出現(xiàn)逆轉(zhuǎn)”“非洲仍是威權(quán)國家最為集中的大陸”。在他們眼中,新一輪“政變潮”只是提供了新的“論據(jù)”。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無一例外,非洲國家均是在20世紀90年代民主化浪潮中,在自身條件并不具備的情況下被西方國家強行輸出西式民主。對于非洲國家而言,政治民主化既非經(jīng)濟增長的內(nèi)生要求,也非政治發(fā)展的自然進程,而是非洲各國當權(quán)者在20世紀80年代經(jīng)濟危機及其所引發(fā)的社會危機與政治危機面前,在國際金融機構(gòu)和美西方國家以政治改革換取援助和貸款的壓力下,被迫做出的政治妥協(xié)。非洲政治民主化最廣為人知的例子是“貝寧模式”,即在野的政治精英借助內(nèi)外壓力迫使執(zhí)政當局召開由各派政治勢力參加的“全國會議”,以相對和平的方式推翻原有政治體制并開啟民主化進程。但并非所有國家的民主化進程都像貝寧一樣順利,不少國家出現(xiàn)流血沖突、政治動蕩乃至軍事政變,盧旺達甚至爆發(fā)了震驚世界的種族大屠殺。
非洲30多年來的政治發(fā)展進程證明,這種外來的民主模式并不適應(yīng)非洲的現(xiàn)實,雖然多黨選舉已基本在非洲各國成為常態(tài),但選舉騷亂、輸家政治、庇護政治和競爭環(huán)境不公等問題仍普遍存在,而且還給一些國家?guī)砹藝抑卫淼睦Ь成踔琳謩邮幍娘L(fēng)險。非洲國家已經(jīng)充分認識到了這一問題。2023年9月21日,幾內(nèi)亞過渡總統(tǒng)馬馬迪·敦布亞在聯(lián)合國大會的講話中明確表示西式民主在非洲大陸失敗了,因為這一模式是西方國家根據(jù)自身歷史進程設(shè)計的,難以適應(yīng)非洲的現(xiàn)實。2023年11月20日,尼日利亞前總統(tǒng)奧盧塞貢·奧巴桑喬在一場主題為“反思非洲西方自由民主”的高級別磋商會中指出,西方自由民主不適合非洲,沒有推動非洲的良治與發(fā)展,應(yīng)該對其進行反思和調(diào)整。
對于非洲政治發(fā)展而言,以民主為先還是以治理為重,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20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強行推動非洲開展民主化,美國更是自克林頓政府時期便開始大力向非洲推進價值觀外交和輸出西式民主。在西方國家看來,西式民主可以包治百病,可以幫助非洲國家完成國家建構(gòu),完善國家治理和推動社會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然而現(xiàn)實情況是,外部強加的西式民主給非洲帶來了一系列國家治理問題,并因此加劇了國家治理的困境。
縱觀非洲新一輪“政變潮”,國家治理不善應(yīng)是相關(guān)國家發(fā)生軍事政變的最主要原因,這其中包括:因政治治理不善所引發(fā)的執(zhí)政集團內(nèi)部權(quán)力斗爭和腐敗等問題;因經(jīng)濟治理不善所引發(fā)的經(jīng)濟低迷、失業(yè)率高漲、貧富分化嚴重和民生危機等問題;因安全治理不善所引發(fā)的恐怖活動頻發(fā)、軍政關(guān)系失調(diào),尤其是軍隊因反恐戰(zhàn)爭損失嚴重而對文官政府不滿等問題。以恐怖主義問題為例,根據(jù)澳大利亞經(jīng)濟與和平中心公布的《2023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shù)報告》,布基納法索、馬里和尼日爾的恐怖主義指數(shù)分別排在第二、第四和第十位;在全球最為致命的20次恐怖襲擊中,有12次發(fā)生在這三個國家。
除了上述發(fā)生軍事政變的國家之外,非洲其他國家的國家治理能力也亟待改善。根據(jù)世界銀行“世界治理指數(shù)”,非洲絕大多數(shù)國家在發(fā)言權(quán)和問責(zé)制、政治穩(wěn)定和不存在暴力/恐怖主義、政府有效性、監(jiān)管質(zhì)量、法治、控制腐敗等六項治理指標中均排在末端。易卜拉欣非洲治理指數(shù)也表明,非洲治理在2012~2021年間雖有小幅改善,但仍有19個國家呈惡化態(tài)勢,而就安全和法治與民眾參與、權(quán)利與包容這兩個關(guān)鍵指標而言,則分別下降了1.3分和0.8分。非洲深陷國家治理的困境充分說明,美西方強行向非洲輸出民主,事實上是顛倒了非洲政治發(fā)展的先后順序。對于當前非洲政治發(fā)展來說,應(yīng)當以國家治理為重,而非以政治民主化為先,一旦出現(xiàn)順序顛倒,只能導(dǎo)致政治失序。這也是美國學(xué)者福山從強調(diào)自由民主轉(zhuǎn)而強調(diào)國家建構(gòu)與國家能力的重要原因,因為真正的政治發(fā)展在于國家建設(shè)、法治和問責(zé)制政府(民主)之間的平衡,而對于非洲而言,其發(fā)展的關(guān)鍵阻礙是國家治理的缺失。
非洲新一輪“政變潮”與以往政變不同的是,無論是政變領(lǐng)導(dǎo)者還是普通民眾都發(fā)出了反對西方新殖民主義的呼聲。2023年8月17日,非盟前常駐聯(lián)合國代表阿里卡娜·奇霍姆博里·夸奧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馬里和尼日爾等國的軍事政變是對西方國家仍在掠奪非洲自然資源的反應(yīng),是反抗西方新殖民主義“非洲革命”的開始,這一革命由“我們的人民領(lǐng)導(dǎo)”,肯定將會繼續(xù)進行下去。學(xué)者貝蒂娜·恩格爾斯在《非洲政治經(jīng)濟評論》雜志上發(fā)表的文章指出,當前非洲新一輪“政變潮”與相關(guān)國家高漲的反西方新殖民主義和謀求自主的呼聲具有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
從新殖民主義的視角來看,馬里、幾內(nèi)亞、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均為前法屬殖民地,盡管它們已經(jīng)獨立了半個世紀,但法國仍然通過經(jīng)濟滲透、軍事干預(yù)和長臂管轄等手段,繼續(xù)在這些國家推行新殖民主義,以繼續(xù)操縱其政府、掌控其經(jīng)濟和剝奪其資源。如法國通過“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體系掌控包括上述國家在內(nèi)的14個非洲國家的貨幣主權(quán),并藉此對它們的經(jīng)濟與政治事務(wù)施加異乎尋常的影響力。又如法國通過實施“新月形沙丘”行動協(xié)助薩赫勒地區(qū)國家反恐,并藉此介入這些國家的政治與安全事務(wù),但最終卻導(dǎo)致越反越恐的局面。法國還長期操控尼日爾鈾礦資源,尼鈾礦為法國核能產(chǎn)業(yè)作出了巨大貢獻,但尼日爾只有不到20%的人口能夠用上電。
可以說,法國推行的新殖民主義是這些國家治理不善、經(jīng)濟不佳、安全不穩(wěn)和民生不保,并進而引發(fā)軍事政變的一大誘因。法國前駐美國大使熱拉爾·阿羅2023年8月1日通過撰文承認,法國與非洲的新殖民主義關(guān)系遭到前法屬殖民地國家民眾普遍反對并被政變領(lǐng)導(dǎo)者所利用,從而成為導(dǎo)致政變的核心原因之一。馬里、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在政變后成立的過渡政府均與法國關(guān)系出現(xiàn)根本性轉(zhuǎn)折,尤其是要求法國撤出駐軍。此外,馬里還在2023年7月宣布取消法語的官方語言地位。
近年來,非洲國家謀求戰(zhàn)略自主和聯(lián)合自強的意識進一步增強,在經(jīng)濟領(lǐng)域推動非洲大陸自貿(mào)區(qū)建設(shè)以加快經(jīng)濟一體化進程,在安全領(lǐng)域堅持“以非洲方式解決非洲問題”強化地區(qū)自主安全治理,在國際關(guān)系領(lǐng)域堅持不選邊站隊并在烏克蘭危機、氣候變化和巴以沖突等重大議題上提出非洲方案。
在政治領(lǐng)域,非洲國家自主探索發(fā)展之路,這其中包括挖掘非洲傳統(tǒng)民主和習(xí)慣法等對當今非洲政治發(fā)展的借鑒意義,以此推動建立內(nèi)生式民主制度,即在非洲傳統(tǒng)政治文化的基礎(chǔ)上構(gòu)建具有非洲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通過延長總統(tǒng)任期,建立強政府或強政黨等方式來保持政局穩(wěn)定和政策的連續(xù)性,如盧旺達在保羅·卡加梅的領(lǐng)導(dǎo)下妥善處理政治與經(jīng)濟的關(guān)系,注重安全與穩(wěn)定,堅持公平與公正,強調(diào)和解與和諧,踐行協(xié)商政治和有為政府,經(jīng)濟常年保持5%以上的增長率,盧旺達也被譽為“非洲的新加坡”;將國家治理置于政治建設(shè)的首位,并通過重新審視酋長等傳統(tǒng)領(lǐng)袖在國家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等方式,探索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相結(jié)合的治理模式,如加納以憲法保障酋長的土地分配權(quán),莫桑比克通過立法保障酋長在司法、警察、稅收、分配土地和實施經(jīng)濟開發(fā)項目等領(lǐng)域的權(quán)利,南非賦予傳統(tǒng)領(lǐng)袖參與立法的權(quán)利;加強政府官員的專業(yè)性建設(shè),讓更多的技術(shù)官員進入各層政府管理體系;進行權(quán)力下放,推進中央與地方的權(quán)力均衡;對女性和青年進行賦權(quán),并增加他們在政府中的代表性等。
非洲國家之所以堅持自主探索政治發(fā)展之路,一方面在于非洲國家已經(jīng)越來越意識到西式民主的危害性,其以外部強行嵌入的方式人為割裂了非洲國家自然的政治發(fā)展進程;另一方面則在于隨著21世紀以來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地區(qū)一體化不斷深入以及與域外大國交往全方位展開,非洲國家越來越自信地意識到它們既有權(quán)利也有能力基于本國歷史、文化和社會經(jīng)濟條件,結(jié)合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探索出一條具有非洲特色和符合非洲實際的政治發(fā)展之路。
然而,非洲自主探索政治發(fā)展之路肯定不會是一蹴而就和一帆風(fēng)順的,在此過程中,必須要將國家治理放在首位,并正確處理好改革、發(fā)展與穩(wěn)定的關(guān)系,從而盡可能在較長時期內(nèi)保持政局穩(wěn)定、經(jīng)濟發(fā)展和民生改善,唯有如此才能頂住西方國家的壓力和獲得國內(nèi)民眾的支持。在這方面,中國有別于西方的現(xiàn)代化之路可為非洲國家提供有益的借鑒,加強中非治國理政和發(fā)展道路之間的交流與互鑒,有助于鼓舞非洲人民探索適合自己的政治發(fā)展之路。
(曹文娟為中國社科院信息情報院編輯,沈曉雷為中國社科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中國非洲研究院〉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