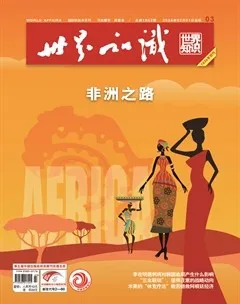伊朗克爾曼慘案是否將成為地區戰爭導火索
劉嵐雨

2024年1月3日,伊朗克爾曼市發生連環爆炸案,人群在現場聚集。
當地時間2024年1月3日14時55分與15時15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朗克爾曼市舉行的紀念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高級將領蘇萊曼尼遇襲身亡四周年活動上制造了兩起自殺式爆炸襲擊,致使至少103人死亡、200多人受傷,這是自1979年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以來該國發生的最嚴重的一次恐怖襲擊,也是“伊斯蘭國”在伊朗境內成功實施的第五起恐怖行動。慘案發生后,伊朗最高決策層宣稱“伊斯蘭國”只是實施恐襲的“雙手”,而“大腦”則是以色列和美國。這一表態使國際社會對伊朗直接卷入本輪巴以沖突,進而引發地區性戰爭的可能產生擔憂。而此前為報復并制止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被認為由伊朗支持的地區什葉派武裝組織,如黎巴嫩真主黨、敘利亞國民防衛軍、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和也門胡塞武裝,已在黎巴嫩和也門分別對以色列本土及途徑紅海的船只發動襲擊,并頻繁襲擊美國在敘伊境內的軍事基地,導致地區安全形勢趨于緊張。
那么,克爾曼連環爆炸慘案是否會成為地區戰爭的導火索?
克爾曼連環爆炸慘案發生后,伊朗的一系列行動不斷加深外界對其直接卷入地區沖突并使地區安全局勢急劇惡化的擔憂。例如,1月11日,為報復2023年5月美軍在馬六甲海峽強行扣押載有伊朗原油的“蘇伊士·拉詹”號油輪并侵占其15萬噸原油的行為,伊朗海軍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阿曼海域扣押了裝有美國14.5萬噸原油的“圣尼古拉斯”號油輪。同日,胡塞武裝也向紅海附近的亞丁灣航道發射了一枚反艦導彈。作為回應,美英軍隊在1月12日凌晨發動了對也門境內胡塞武裝的空襲,這是自2016年以來美國首次對也門武裝組織進行打擊。美英軍隊的空襲并未換來胡塞武裝的退讓,后者稱將打擊“美英的所有利益存在”,并在14日向美國在紅海的驅逐艦發射巡航導彈,紅海安全局勢不斷惡化。1月15日夜間,為報復美以策劃克爾曼恐襲案,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航空部隊向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的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駐處發射了11枚彈道導彈,并向敘利亞伊德利卜的“伊斯蘭國”武裝及其北部的其他恐怖主義團體發射了共13枚彈道導彈。1月16日晚,為報復俾路支斯坦遜尼派恐怖組織“正義軍”1月10日對伊朗拉斯克警察局的襲擊,伊朗還對“正義軍”位于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境內的兩個據點展開無人機與導彈打擊。

2024年1月16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對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發動襲擊,當地建筑被摧毀。
然而,其實在1月4日晚“伊斯蘭國”聲明對克爾曼慘案負責之前,伊朗官方就已將其定性為恐怖襲擊,該國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根據作案方式推斷可能是“伊斯蘭國”所為。也就是說,伊朗從一開始就沒有將慘案發生的直接責任歸結到美以兩國。1月3日,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表態中明確區分了慘案的直接實施者和策劃者,他表示:“沾滿無辜者鮮血的雙手,及導致他們犯下這一邪惡罪行的腐朽大腦,今后都將成為鎮壓和正義懲罰的對象”,其中“雙手”暗指直接實施襲擊的恐怖分子,而“腐朽大腦”則暗指以色列和美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總司令侯賽因·薩拉米與負責海外行動的圣城軍司令伊斯梅爾·卡尼也在同日的表態中響應了最高領袖的觀點。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在次日的官方聲明中甚至沒有提及美以,而是直接表示“克爾曼慘案是恐怖主義行為,旨在增加伊朗國內的不安全感”。
伊朗最高決策層對如何在本輪巴以沖突不斷產生外溢影響的情況下做出回應表現得非常謹慎,并未沖動地將美以列為報復對象。1月4日,作為伊朗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最高機構,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召開會議集中討論美以是否牽涉其中及懲罰兇手的方式。從時間上來看,伊朗在克爾曼慘案發生12天后才實施報復,這也表明伊朗采取的報復措施經過了深思熟慮。從最初就將慘案定義為恐襲,到在應對上表現出的審慎與克制,說明伊朗決策層并不追求激化地區緊張局勢,更不想直接卷入巴以沖突。因為若是伊朗有此意愿,完全可以在第一時間將慘案的責任歸結到以色列身上并對其展開報復。
伊朗決策層之所以表現出審慎與克制,一個重要原因可能是其懷疑美以是慘案的幕后指揮,而引誘伊朗主動挑起戰爭是他們的重要目的。1月8日,替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聲的“努爾新聞”網站發表了一篇題為《暗戰》的評論文章。文章指出,伊朗方面不能相信地區情報機構,尤其是不能相信摩薩德事先對克爾曼恐襲行動毫不知情,也不能排除恐襲行動就是在地區和國際情報機構支持下展開的可能。一是發動如此規模的恐襲需要廣大的地區網絡支持,至少包括資金、運輸與通信網絡。即便假設“伊斯蘭國”擁有這樣的網絡,其運行也不可能毫無信息泄漏。因此,作為地區老牌情報組織的摩薩德不可能對此次恐襲一無所知。二是基于此前披露的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郵件門”事件與前總統特朗普的相關表態,伊朗相信“伊斯蘭國”是美國和地區情報組織的雇傭兵。文章強調“摩薩德的目的是通過暗戰刺激伊朗公眾神經,引誘伊朗主動挑起戰爭”,并呼吁伊朗“不應受情緒左右卷入敵人想要的戰爭”。
伊朗議長加里巴夫1月8日在議會的表態也部分呼應了上述觀點,他認為恐怖分子背后的雇主是以色列和美國,恐襲的目的是在伊朗社會中制造恐怖心理,而這一目的已經被伊朗民眾挫敗。這種“恐襲本身意味著敵人失敗”的敘事在伊朗總統萊希、圣城軍司令卡尼的公開表態中也有體現,其目的可能是為伊朗在采取報復行動的時間和方式上爭取靈活性,避免本國在伊斯蘭革命意識形態要求和外部煽動下迅速卷入與美以的直接對抗。
自2017年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伊朗逐步實施極限施壓政策以來,伊朗維護國內安全的壓力大幅增加。除打擊分裂主義勢力、偵查間諜破壞活動、防范恐怖組織滲透、應對網絡攻擊與管理日益增多的阿富汗難民外,還要應對日益頻繁的社會運動,伊朗安全力量長期處于超負荷運行狀態。正是在這一時期,“伊斯蘭國”在伊朗的活動日益頻繁并成功在克爾曼慘案發生前制造了三起恐襲事件。2017年7月5日,“伊斯蘭國”對德黑蘭議會和伊瑪目霍梅尼陵發動恐襲,造成17人死亡,52人受傷;2022年10月對位于設拉子的什葉派“光明之王”圣陵發動恐襲,造成13人死亡,三人受傷;2023年8月13日,“伊斯蘭國”再次對“光明之王”圣陵發動恐襲,造成兩人死亡、七人受傷。在克爾曼慘案發生前不久,安全部門在克爾曼省曾搜查出16枚炸彈,還逮捕了23名準備進行自殺式襲擊的“伊斯蘭國”成員。
面對境內急劇增加的“伊斯蘭國”活動,蘇萊曼尼遇襲身亡周年紀念活動指揮部從一開始就設置了兩個安保委員會來討論活動的安防部署。據克爾曼檢察官馬赫迪·巴赫什稱,指揮部加強了克爾曼紀念活動的安保力量,除警察、革命衛隊和情報部門人員外,軍隊也參與了安防工作,使用了無人機和熱成像儀等先進設備。正是因為安防部署如此強力,導致制造慘案的自殺式襲擊者無法進入陵園內,只能在陵園外數百米處引爆炸彈。
盡管如此,大量的人員傷亡,恐襲指揮者在恐襲前離境,官方在傷亡數據和恐襲實施方式說法上的頻繁調整,使伊朗安全情報部門在公眾眼中呈現出安保能力漏洞百出的形象,提升了恐怖組織和反叛勢力在伊朗境內開展行動的信心。例如“伊斯蘭國”在聲明中便稱將在伊朗展開更多行動。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伊朗決策層無意挑起地區戰爭,但考慮到國內安全挑戰進一步增加的風險,伊朗政府也需要通過高調報復來強化對恐怖組織和境內反叛運動的威懾力,這可能也是伊朗在慘案發生后通過發射彈道導彈進行報復的重要原因。
然而,雖然伊朗在報復手段和打擊目標的選擇上頗具冒險性,但其在對報復行動破壞力的追求上卻展現出了克制。從1月16日夜間伊朗向美國支持的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區首府埃爾比勒發射的11枚彈道導彈的打擊目標來看,除射向摩薩德駐地外,還射向了美國領事館周邊的八處地點,極具挑釁意味。但是,從結果上看,此輪襲擊并未造成美國人員和財產損傷,也沒有造成以色列人員傷亡。這不禁令人聯想到2020年1月8日伊朗報復美軍殺害蘇萊曼尼的行動,當時伊朗向美國在伊拉克境內的兩個軍事基地共發射了22枚彈道導彈,也未造成美國的人員傷亡。據事后美國披露,伊朗在襲擊前曾向美國透露行動的相關信息。此次伊朗在報復行動中再次采取“虛張聲勢”的策略表明,伊朗報復的目的并非是加劇地區緊張局勢或挑起地區戰爭,而是通過展現其“睚眥必報”的決心來強化對境內外安全威脅的威懾力。
(作者為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