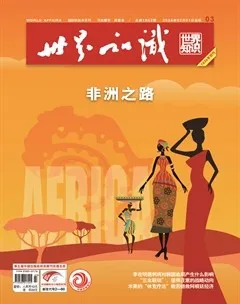“三北聯動”,值得注意的戰略動向
王克宇?胡欣

2023年6月1日,挪威空軍F-35戰斗機參加“北極挑戰-2023”聯合軍演。這是挪威、瑞典、芬蘭共同舉行的第六次軍演,來自14個國家的共150架飛機和約2700人參加。?
在國際安全事務中,北極長期被視為“例外之地”,該地區所形成的國際合作與和平對話機制也使其得到了“和平之極”的美譽。然而,隨著烏克蘭危機和大國博弈的升級,“和平之極”正向“不穩定之極”轉變,表現之一就是美、俄、歐和北約在北極的所謂“地緣政治覺醒”。其中,北歐國家置身美俄歐“交叉影響”的場域中,其傳統的平衡主義、和平主義立場受到陣營身份選擇和戰爭危機感的疊加沖擊,引發戰略認知和安全立場的轉變。芬蘭已經加入北約,瑞典也站到了入約門檻上,美國因此得以增強對北歐的戰略捆綁,進而策動北歐、北約、北極“三北聯動”,攫取戰略競爭優勢。
烏克蘭危機爆發前,北歐五國有三個(挪威、丹麥、冰島)為北約國家。在西方總體與俄二元對立的環境下,北歐國家加速向美國靠攏,成就了北約“北擴”的天賜良機。
美國是北約內部支持瑞典、芬蘭入約調門最高的國家。2022年5月19日,美國總統拜登在會見兩國領導人時表態“兩國完全符合加入北約的所有要求”,承諾將“全力以赴支持兩國的申請”。同年8月9日,拜登正式簽署批準兩國入約的議定書。在得知土耳其為瑞典入約設置障礙后,美國不惜以拒絕出售F-16戰機為籌碼,向土耳其施壓。美國還鼓動盟友為兩國入約助威造勢,挪威、丹麥、冰島三國發表聯合聲明,稱如果瑞典、芬蘭在正式成為北約成員國之前遭到攻擊,將全力予以幫助。英國也與兩國簽署安全協議,明確如三國遭受他國攻擊,三國軍隊將相互提供支持。
在美國主導下,北約與瑞典、芬蘭兩國的防務合作快速推進,質量不斷提升,包括:拓寬軍事技術合作,如美國空軍與挪威航天公司宣布共同執行“北極衛星寬帶任務”,美國雷神公司和挪威防務公司共同開發“聯合打擊導彈”和“海軍打擊導彈”,等等。美軍除在北約框架下與北歐國家開展“北極邊緣”“寒冷反應”“北極挑戰”等多邊聯合軍演外,還單獨與部分國家開展雙邊軍演,如2023年5月與芬蘭舉行聯合地面演習,6月與瑞典開展空中聯演,9月與挪威開展特種部隊聯合訓練,等等。2023年12月,芬蘭、瑞典與美國簽署雙邊防務合作協議,美軍可“不受阻礙”地使用兩國境內所有軍事基地,開展人員部署、訓練演習、物資轉運等活動。丹麥同時與美國達成新的防務協議,允許美國的軍人和裝備長期部署在丹麥,這也是丹麥首次允許外國軍隊進入其領土,標志著丹麥國防政策的“新突破”。
美國還積極推進多領域國際合作,以共同開發、外交互助為主要抓手,強化與北歐國家的利益捆綁。2021年5月,美國國際開發署公布了對丹麥格陵蘭地區約1000萬美元的援助計劃,用于發展當地礦業、旅游和教育。2023年6月1日,拜登政府宣布將在挪威北部的特羅姆瑟開設美國第一個北極外交站點。7月13日,拜登與北歐五國領導人舉行峰會,同意加強5G和6G、人工智能、網絡安全、量子技術等方面的技術合作。這一系列舉措高調展示了美國欲以北歐為跳板經營北極的戰略導向。
北極的戰略價值體現在六個方面:一是潛力巨大的軍事用途,二是豐富的自然資源,三是對全球戰略優勢的競爭場域,四是貿易航道,五是旅游業發展潛力,六是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性。美國尤其重視北歐國家得天獨厚的地緣戰略價值,急于下“先手棋”以贏得在北極這個“新邊疆”的競爭優勢。
一是打造“北極前哨”,強化威懾力。戰略家們都認同,從地緣政治上看,北歐國家的地理稟賦為美軍提供了前沿部署作戰優勢。比如,丹麥的圖勒空軍基地距北極圈1200公里,挪威的奧蘭空軍基地距北極圈僅500公里,挪威特羅姆瑟港緊鄰俄北方艦隊駐扎地科拉半島。美國力求將這些基地打造為“抗俄前哨”,圖謀部署具有戰略威懾和打擊意義的裝備。2021年,美國首次將B-2轟炸機部署在冰島,如今B-2已成為該地區“常客”,身影也曾出現在挪威。2023年初,美國空軍首次將可攜帶核彈的F-35戰斗機部署在圖勒空軍基地,被稱為“核戰指揮機”的E-6B也飛抵冰島為“極端情況”做準備,美國海軍還派遣戰略核潛艇頻繁停靠挪威、冰島的港口。2023年9月,美軍“全球鷹”無人偵察機首次進入芬蘭領空,沿著俄芬邊界飛行并偵察俄軍動向。與此同時,美國力推北歐防務一體化,支持丹麥、挪威、芬蘭、瑞典四國組建“北歐聯合空軍”,鍛造對俄威懾的“北歐力量”。在美國和北約鼓動下,四國同意組建一支規模為250架戰機的聯合空軍,為此預計向美國采購143架F-35戰機,未來將成為美國與北約麾下最大一支空中威懾力量。
二是把小多邊同盟協作引入北歐,構建北極盟友圈。美國國防部2022年發布的《北極地區國家戰略》強調要“最大限度地開展與北極盟國的合作,深化伙伴國家合作關系,增強與盟國間的互通性與互操作性,共同維護美國與其他北約國家在北極地區的利益”。美國對北歐的外交拉攏,顯露出其構建北極盟友體系、打造排他性合作機制的考量。美國有意在北極博弈中建立起復合型同盟網絡,打造以美國為核心的彈性“小多邊”,進而構建“基于規則的北極秩序”。美國可憑此制定排他性、歧視性的標準,為特定國家參與北極事務設置障礙。這種彈性“小多邊”,可能日趨變得與美英澳三方安全聯盟(AUKUS)、“芯片聯盟”、美日印澳四方合作機制(QUAD)、“五眼聯盟”等“小圈子”相似,體現出強烈的零和博弈特征。
三是擴大影響,爭奪北極開發“主導權”。北歐國家在北極能源開發方面擁有雄厚的技術優勢和平臺資源,美國希望以盟友關系為紐帶,將北歐的地理優勢轉化為在商業上進軍北極的主導優勢。在2023年7月的美國—北歐領導人峰會期間,拜登政府明確表示將與北歐國家加強在清潔技術、能源效率、關鍵礦產資源及彈性供應鏈等方面的合作。美國還糾集北歐國家,針對俄羅斯的北極能源開發活動實施制裁,如禁止北歐國家向俄出口能源勘探與開采設備,敦促挪威國家石油公司終止與俄在“北極天然氣二號”項目上的合作,等等。通過這些舉措,美國誘導北歐國家在北極能源開發和其他“低政治領域”與美國保持“戰略一體”,借北歐之力謀北極之利。
當今世界處于新的動蕩變革期,美西方對北極地緣政治價值的重新審視,意在重塑國際規則,應對“大國競爭挑戰”。美國與北歐國家加強“戰略捆綁”,更是蘊含爭奪北極利益、謀求北極霸權的長遠運籌。這種貪圖霸權私利的戰略取向,與國際社會倡導、北歐國家過去十分推崇的北極合作精神背道而馳,將加劇北極問題的“安全化”,加大地區形勢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
北歐國家過度倒向美國和北約,勢必將俄逼入更艱險的“角落”,引發更大安全焦慮,加深不同國家間的“安全困境”。2022年芬蘭、瑞典宣稱要加入北約時,俄對北歐國家實施了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驅逐北歐國家外交官,將挪威、冰島、丹麥列為“不友好國家”,暫停對芬蘭電力供應等。隨著北歐國家與美國日益貼近,俄以軍事威懾行動予以回應,包括在科拉半島試驗高超音速導彈,在加里寧格勒部署具有核打擊能力的“伊斯坎德爾”導彈,在波羅的海與北約針鋒相對開展軍演,向俄芬邊境增兵,等等。其他北約國家對北極地區的關注度也在不斷增強,英、法、德等國紛紛表示將加強在北極地區的軍事存在。未來,北歐國家將被頂在一線,充當對抗俄羅斯、爭奪北極控制權的角色,是否還能像以前一樣在國際變局中獨善其身,充滿不確定性。
從全球治理角度看,北歐、北極地區態勢的變化將引發連鎖效應。首先,北極地區力量格局面臨“失衡”危險。俄羅斯、北美、北歐在該地區曾經形成的穩定“三角關系”將轉變為北約與俄羅斯的二元對立,刺激北極局勢走向“極化”。其次,北極地區合作機制有可能被迫“停擺”。目前,北歐國家在北極理事會、巴倫支—歐洲北極理事會、北極海警論壇等區域合作機制中追隨美國大搞對俄“脫鉤斷鏈”。美國、歐盟、北約還持續渲染中國為“潛在敵手”,傳播俄中或在北極結成“權宜同盟”的戰略敘事,污蔑中國對北極的關注不僅是出于經濟、環境和能源原因,更包含在2030年前成為“北極大國”的“軍事野心”。第三,全球公域治理的效能將遭削弱。大國戰略競爭和利益分歧進一步弱化國家間互信合作,議題的“安全化”乃至“泛安全化”將加劇戰略猜疑與敵對,拉低國際社會共同參與北極治理的效能,給本已困難重重的全球公域治理帶來持續消極影響。
(王克宇為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研究助理,胡欣為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

2023年5月3日,北歐五國領導人在芬蘭赫爾辛基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峰會。圖中從左至右依次為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丹麥首相弗雷澤里克森、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冰島總理雅各布斯多蒂爾、挪威首相斯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