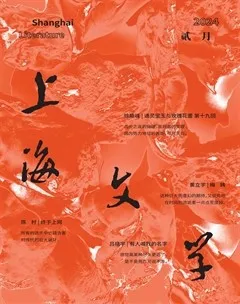匯文三題
肖復興
我在匯文中學讀書八年,初中高中各三年,文化大革命兩年。一九六○年,我考入這所中學的時候,它已經改名為北京市第二十六中。數字化的名字,遮蓋了悠長的歷史痕跡。它最早是用庚子賠款建立起來的一所教會學校。
我報到的時候,還在匯文老校,老校在崇文門內的船板胡同。印象最深的是,校園里有一則匯文校訓的醒目牌子,是當年蔡元培先生題寫的手書:“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說實在的,當時,我并沒有看懂,但是,蔡元培這個人還是知道的,他當過北京大學的校長,而北京大學的前身就是匯文學校。請蔡元培來題寫校訓,應該不簡單,心里便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面對著這則校訓,看了許久。
如今,校名由二十六中又改回匯文中學。匯文中學,建校已經一百二十二年。一晃,不覺舉頭已是千山綠。
百年滄桑如海,只掬一瓢飲。
扁桃
我們學校的墻報《百花》,就是學校的文學雜志,盡管只短短存活五年左右的時間,但是,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曾經讓大家引以為豪。
和當時的《少年文藝》《兒童文學》不一樣,和如今專門給學生看的文學雜志如《東方少年》《中國校園文學》也不一樣,它基本沒有兒童文學所彌漫的孩子氣,更像一本成人文學雜志。我想,這大概是因為在《百花》上面寫文章的大多是老師,除語文老師寫的閱讀指導和散文小說之外,物理老師余朝龍在《百花》上開設有專欄“大科學家的小故事”,每期講一個科學家的小故事,很受歡迎。學生在它上面寫的文章,和一般的作文拉開明顯的距離,大多創作的是小說散文,作者大多是愛好文學的高中生。如我一樣的初中生,很少也很難在上面露面。它有自己的門檻。
我非常喜歡看《百花》。盡管它上面的文章水平并不能完全趕上正規的文學雜志,但是,由于是自己的老師和學長寫的,會感到親切,讀起來有一種走進學校食堂里吃飯的感覺,而沒有進飯館的那種距離感和陌生感,吃起來的味道便格外愜意。我特別愛讀學生的文章,他們常會學著作家也給自己起個筆名。看到那些寫得好的文章,心里很是佩服,總讓我忍不住猜測會是哪個班的哪個同學寫的,很有一種“但愿一識韓荊州”的感覺,會萌生起見見這個同學的想法,向他討教一下學習寫作的方法。那時候,我是那樣癡迷于文學寫作。
大約是我讀初二的第二學期,有一件事,突然在同學中議論開來,是說《百花》上高三同學寫的一篇名叫《扁桃》的文章。這篇文章,我看過,大概意思是寫他童年時喜歡班上的一個女同學,一直從小學到初中,兩人都在同一所學校,考高中后,他考上了匯文,是男校,女同學考入一所女校,兩人分別,彼此想念。寫的是男女同學之間的友情,有那么一點朦朦朧朧的感情漣漪。我并沒有完全看懂,只是覺得挺美好的。
問題出在了“扁桃”上面。記得文章中提到,這個女同學從小愛吃扁桃,有時候,男同學會買來送給她。已經過去了六十年,記憶中隱隱約約是這樣的,也許會有偏差,但大概意思是差不太多的。不就是一個扁桃嘛,我沒覺得會有什么問題。
但是,超出我的認知,也超出我的想象,“扁桃”的問題,一下子變得嚴重起來。同學之間的議論多了起來,卻都是含混不清,遮遮掩掩,欲言又止。最后,我聽明白了問題嚴重的根結,說“扁桃”形容的是女同學。為什么要拿扁桃形容女同學呢?拿扁桃形容女同學,又為什么成為了嚴重的問題呢?這在當時,我和我的同班同學都是不解的,只有面面相覷。我們很想問明白,但找誰問呢?找老師嗎?老師會瞪著一雙疑惑甚至責備的眼睛,反問你為什么對這樣的事情感興趣。
于是,扁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成為了一個不解之謎。
聽說,寫《扁桃》的這個高中同學,和同意把這篇文章登載在《百花》上的語文老師,都受到學校嚴厲的批評,至于最后怎么處理的,這位馬上就要高考的同學,影響沒影響到考大學,我就不知道了。事情很快就平息了,學校不想鬧大,大家的興趣轉移了,緊張的復習考試也來臨了,扁桃的季節,過去了。
一直到長大以后,我才明白,有一位老師首先對文章發出質疑,認為扁桃象征著女性的性器官。這可不是小問題了,一個學生,居然將扁桃寫成性器官,不僅是大逆不道,而且是下作,是思想意識問題了。只是,我不知道,這真的是這位學長自己想到的象征,還是老師自己敏感的想象,從文學到道德到思想意識階梯式的聯想?事情已經過去了六十年,“扁桃”已經成為了無頭案。
在學生時代,特別是進入高中的青春期,男女之間的情感,性的朦朧迷惑乃至沖動,其實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在當時的環境下,尤其是在我們男校里,沒有這方面的教育,對這樣的問題,是諱莫如深的,只能沖撞在同學自己的心里。這位寫《扁桃》的同學,或是隱晦曲折的表達,或是美好抒情的想象,無論哪一種,都是真實的。作為老師,可以引導,可以幫助,也可以批評,但是,首先要弄清到底是哪一種,而不能僅僅以成年人的思維先入為主地進行主觀武斷的判斷。這樣做,很容易把不是問題的事情,小題大做,一下子從青春心理上升到道德乃至思想問題,這對正處于青春期的同學來說,傷害是極其大的,也是無法彌補的。作為老師,這是和知識與思想教育同等重要的問題。在我讀書時的匯文中學,是重視同學的學習、思想與身體方面的教育的,但是,坦率地講,學生青春期的情感與生理教育方面,是缺乏的,甚至可以說是空白的。當然,在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教育情勢下,這不僅是我們匯文一所學校的問題。
在我讀高三第一學期的那年年底,即一九六五年底,和我們班一墻之隔的高三四班,發生了一件令人觸目驚心的事情。在全班同學的眾目睽睽下,一位姓趙的同學突然被警察帶走,最后以“猥褻幼女罪”被發配長春勞改。這在我們學校是一件非常轟動的事情,遠超過當年的“扁桃”事件。
其實,它和“扁桃”事件一樣,也屬于誤判。趙同學品學兼優,初中畢業,作為優良獎章獲得者,保送匯文中學。不過是他和鄰居的一個女孩有了青春期懵懂的感情,女孩的家長發現了,不干了,把事情鬧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居然把一個優秀的學生,就那么輕易送進了勞改農場。
高三四班的班主任是王璦東老師。那時候,她三十五歲,正年輕,班上出現了這樣的事情,令她措手不及,面對警察突然闖進教室,她不知如何是好。警察帶走趙同學,經過講臺邊的時候,趙同學望了一眼她,眼光中充滿驚恐,還有無辜和一絲絲求救以及悲傷的復雜情感。
她不相信一直表現良好的趙同學會是罪犯,可是,她能說什么,又能做什么呢?警察帶走趙同學后,教室里死一般寂靜,她只能對全班同學含糊其辭地說:“這是青春期好奇心理所犯的錯誤吧,大家要引以為戒。”
已經過去了五十多年,這件事,很多人都早已經忘記,卻一直盤桓在王老師心中。去年,王老師年整九十,健康如舊。她所教的高三四班同學為她祝壽,全班同學都找齊了,唯獨缺少了趙同學。她再一次想起了他,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怎么一下子淪為階下囚呢?她想起“文革”期間,自己被扣上那么多莫須有的惡毒污穢罪名而被批斗,無力反駁,只能沉默不語。設身處地想,在那樣一個有口難辯的極左年代,一個只有十七歲的學生,怎么來證明自己的清白無罪?她堅信自己的這個判斷。當年,自己作為趙同學的老師,無力阻止這樣荒誕行為的發生,現在,應該找到趙同學,起碼讓他在當年高三四班的全班同學面前,證明是清白的,也彌補當年眼瞅著趙同學從自己的眼皮底下被警察帶走的遺憾,她無法忘記那時趙同學望著自己無辜而悲傷的眼神。
王老師開始尋找趙同學。這成為九十歲這一年王老師要做的一件大事。去年夏天,我見到王老師的時候,王老師對我說:我已經九十歲了,想做的事就去做,不給自己留遺憾。
尋找五十五年前被注銷北京戶口的一個人,如同大海撈針。其中的艱難,可想而知。架不住王老師桃李滿天下,可以幫她如海葵的觸角伸向大海深處,一身化作身千百;更架不住王老師心如鐵錨,堅固地沉在海底,等待船遠航歸來。終于,在這一年的年末,王老師找到趙同學故去父親戶籍上有一女的登記信息,沒有名字,只有一個電話號碼。王老師迫不及待打去電話,問接電話的女子知道不知道趙同學的名字。她說那是我大伯!但是,她沒有她大伯的電話,說他在河北遷安,他的兒子在北京工作,她問問后再給王老師回電話。五分鐘過后,電話打過來了,沒有想到,竟是趙同學。
一個只教過自己兩年半的老師,居然還記得五十五年前的一個學生,而且,相信他是被冤枉的。這樣的老師,是少見的。她理解學生青春期的心理秘密,她相信學生青春期的感情萌動。
聽到王老師終于找到趙同學的消息,我想起了當年的“扁桃”事件。在同一所學校,老師和老師是不一樣的,我不知道當初思想敏感和想象力豐富的那位發現“扁桃”秘密的老師,會不會還記得當年的“扁桃”事件?我也不知道寫作《扁桃》這篇文章的學長,會不會有趙同學類似的命運?園墻
學校的墻報《百花》,每一期掛在大廳里,都特別吸引我。那上面的很多文章,是高年級的師哥們寫的,盡管他們比我年齡大,也都不認識我,但對我極具誘惑力。和正式的雜志比如《北京文藝》《人民文學》的高高在上相比,《百花》開在自己的校園里,有一種平等平易的感覺,仿佛一推門就能進去。
我最喜歡的是一個叫“園墻”的師哥寫的文章。在《百花》上,他寫了一組“童年紀事”,每期一篇,回憶他童年的種種趣事和他的大小朋友,文筆清秀淡雅,像散文,又像小說,我非常喜歡讀。特別是在我讀初三的那年寒假,看到了他在《北京文藝》上發表了一篇散文《水仙花開的時候》,心里更是特別崇拜他,覺得只有作家才能夠在《北京文藝》上發表文章啊,他真了不起!以前在書中見到的那些作家,離我都很遙遠,但這個園墻就在我們的學校里,在這同一幢大樓里呀。也許,每天放學或上學,匆匆走在樓梯的臺階上,我們早已擦肩而過。
我特別想認識他。我打聽清楚了,他是我們學校高三的同學,名叫李元強,園墻是他的筆名。我覺得這個筆名取得特別好,比他的原名元強好很多。園墻,園子的一道墻,什么園子呢?花園?菜園?魯迅的百草園?巴金荒蕪的憩園?契訶夫的櫻桃園?……不管什么園子的墻,都會比一般的墻要漂亮,要引人遐想。如果換作院墻,或者宮墻,就差多了。
那時,我也想給自己取個筆名,似乎正兒八經的作家,都應該有一個自己的筆名。你看人家魯迅就是筆名,園墻也是筆名。但是,我想了好久,也沒有想好哪一個筆名適合自己。
我已經忘記了最后是怎么認識他的。記得一直到初三畢業,放暑假之前,我才第一次見到他。他個子不高,其貌不揚,但是,一點兒沒有影響我對他的崇拜之情。那時,他剛剛參加完高考不久,在焦急等待著大學錄取通知書。我向他表達了敬意,他沒有什么驚訝或得意的表情,或者說臉上根本沒有任何表情的流露。他很平靜地對我說:我知道你!看你們班辦的《小百花》的時候,就知道你了。《小百花》,是我們班模仿《百花》辦的板報,每一期也搬到大廳里,擺在《百花》旁邊。學校里,曾經一時有大《百花》《小百花》之說,很鼓勵我們叫陣。
我接著對他說起他在《百花》上寫的專欄“童年紀事”,覺得寫得特別好,希望他能對我說說是怎么寫的。他打斷了我的話,只對我說了句:我是看了田濤的小說集《在外祖父家作客》,學著寫的。你知道田濤嗎?這話把我問住了,我不知道田濤,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茫然而有些羞愧地望著他。
那時候,我不知道他的心里塞滿著蒺藜,讓他有一種難以言說的難受,這樣的刺痛感,他不會對一個比他小很多的我訴說,覺得即使說了,我也不懂。我卻磨著他,希望他能給我傳授一點寫作的經驗。大概是被我磨得沒有辦法了,便說:哪天你到我家去,我借你兩本書看!
按照他給我的地址,我找到他家。離我家很近,就在我家前那條老街東頭路南的一條小胡同里。胡同雖小,他住的院子卻和我們大院一樣,也是一個三進三出的大四合院,院子很深,后來搭蓋起的小廚房小偏廈,雜亂擁擠著。他家在院子的最里面。
那天,我在他家沒有久留,他拿出早為我準備好的上下兩冊《莫泊桑小說選》給我,我看到書的封面上印著李青崖翻譯的字樣。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法國還有個作家叫莫泊桑,也第一次知道李青崖這個翻譯家的名字,心里非常好奇,很希望他能對我介紹一下李青崖和莫泊桑。但是,他沒有說別的,只是說看完了再到他家里換別的書。我很感謝他,覺得他很了不起,看的書那么多,都是我不知道的。我渴望從他那里開闊視野,進入一個新的天地。
我看完這兩本,到園墻家還書,他已經不在家了。他的母親告訴我,他沒有考上大學,原因是出身問題。他被分配到南口農場上班去了。
那天,從園墻家走出,我心里很悵然。想起莫泊桑,想起李青崖,想起園墻,這三個名字,一下子都變得很傷感了,讓我的眼前彌漫起一層世事滄桑難預料的迷霧。
南口農場
高中三年,每年都有一次下鄉勞動,一般是在新學年開始后的秋天。這時候,天氣不冷不熱,是北京最好的時節,而且,也正是農村的秋收季節。記得高一去的懷柔,高二去的南口,高三去修京密引水工程,住在密云的西流水村,一個好聽的村名。
印象最深的是高二,在南口農場。這里以前是一片荒沙灘、古戰場,亙古荒無人煙。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人們才在這里建立起了農場。這里號稱有“三多”和“三少”:“三多”是石頭多、風多、酸棗棵子多;“三少”是土少、水少、樹木少。所以無法種莊稼,便在這里種果樹,有桃樹、杏樹,也種有葡萄,主要是蘋果樹,逐漸把它改造成一片挺大的果園。南口的蘋果,有過出口的聲譽,一度是個響亮的名字。最初來這里的大多是復員軍人、下放干部、當地的農民,和一些頭頂著“右派”帽子的人。六十年代以后,北京城里沒有考上大學的學生,也有很多來到這里。可以說,這里也是北京知青最早“上山下鄉”的地方之一。我們興致勃勃地來到這里,并不知道,幾年之后,我們也將成為知青,走和他們一樣的道路,獲得和他們一樣的頭銜。
到達這里,正趕上農場在搞“擴坑運動”。所謂“擴坑”,就是把布滿在果樹四周的石頭全部取出來清走,然后換上新土,澆上秋水,目的是讓果樹的根系能夠舒展開來,更好地吸收水分和營養,更好地生長,結果更多更好。這是農場的一項關乎未來發展的基本建設。我們來的時候,看到宿舍、食堂、禮堂的墻上,到處貼滿了農場職工的決心書、挑戰書,原本計劃是六天時間擴一個坑,被他們的豪情壯志和苦干硬干,硬是提前到兩天完成。那時,他們的口號是“敢叫日月換新天,為了萬畝果園早日建成”!
六天變兩天!這速度的飛躍,讓初來的我們嘆為觀止,也敬佩不止,自然摩拳擦掌,不甘落后,和他們一起干了起來。不過,這真的不是容易干的活兒,和我們以前下鄉幫助老鄉收麥子、修水利,完全不一樣。實在想象不到,坑里面的石頭,竟然那么多,那么硬,一鎬頭刨下去,只會聽到“咣當”一聲響,看見石頭上出現一個牙咬似的白印而已,石頭卻紋絲不動。農場的老職工沒有笑話我們,幫助我們一鎬一鎬、一鍬一鍬,挖出了一塊又一塊頑固的石頭。
南口農場,留給我的記憶,卻不是這樣艱苦而新奇的勞動。如今,記憶猶新的,是這樣兩件事。
一件是老傅喝粥。
那時候,中午送飯到工地,大家吃完,接著干活。那個年月,每人每月有糧食定量,我們學生是每月三十二斤,吃飯要交糧票,每頓飯便也每人各分一份。有一次午飯有粥,每班同學拿著一個大洗臉盆去打粥,大家隨便喝,喝完之后,拿著洗臉盆可以再去打。對于正處于青春期幾乎個個都是大肚漢的我們,是難得敞開吃的機會。老傅和我是同班同學,不過,我和老傅不熟。這天中午,看見很多同學圍著老傅叫喊著,不知在干什么,我便也圍上去看熱鬧。不知什么原因,是老傅和同學打賭,還是老傅實在肚子餓了,在大家的起哄中,他竟然抱著洗臉盆,把滿滿一盆粥都喝了下去。
很久很久以后,我還總會想起那個場面。一九六四年的十月,秋陽之中,蘋果樹蔭里,眾目睽睽下,老傅抱著洗臉盆,仰著脖子,“咕咚咕咚”,牛飲一般,把滿滿一盆粥喝光。那時候,大災荒剛剛過去,可是,余燼未散,依然纏繞在很多人的心里。
另一件是夜讀《二月》。
那時候,我從別的班的同學那里借到一本柔石的小說《二月》,是一本小開本薄薄的小冊子。一年前,電影《早春二月》剛剛上映,孫道臨、謝芳、上官云珠主演,很是轟動,大家是從這部電影知道柔石的這個小說的。但是,在我們來南口農場前不久,也就是國慶節之前,電影就遭到批判。《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好多報紙上,刊登了長篇文章,直斥電影是“大毒草”,批判電影“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美化逃兵宣揚階級調和”。這樣鋪天蓋地的輿論之下,大家對這個小說更充滿好奇。
聽說我的手里有這本小說,好多同學都想看。可是,已經說好了,書在我手里只能有一天時間,明天就得還給人家,而我自己還沒看完呢。記得當時最想看的,是我們班的團支書老朱。他對我說:你看完了,借給我看。我說行。收工吃完晚飯,我就抓緊時間看,等我看完了,已經到了快熄燈的時間。我把書遞給老朱,有些歉意,這么晚了,一屋住著十幾個同學,到了時間,老師就要過來關燈的,半夜時分,老師還會來查崗,他怎么看呢?他沒有說什么,只是笑著把書接過去,躺在自己的鋪位上看書了。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書看完的,第二天早晨,他把書還我時,我問他,他告訴我,他是躺在被子里打著手電筒,看完這本《二月》的。他看完之后,還有另外一個同學在等著呢,那位同學如法炮制,也是打著手電筒躲在被窩里看的,看完之后,天已經亮了。這樁夜讀柔石《二月》的事情,在我們班上傳為佳話。傳到我們的班主任張老師那里,他搖搖頭,笑了笑,沒有批評我們,也沒有表揚我們,水過地皮濕一樣,過去了。
南口勞動歸來,我寫了一篇作文《沙石荒灘變果園》,受到老師的表揚。但是,這篇作文,只寫了我勞動的體會、對南口農場擴坑運動的贊揚、對萬畝果園建成后碩果累累的未來美好生活的憧憬,沒有寫老傅喝粥和老朱夜讀《二月》。不是忘了寫,是根本沒有想到這樣的兩件事,其實也是可以寫進作文里的。那個年代的作文,不興這個,興的是楊朔《雪浪花》《荔枝蜜》那樣的寫法,要有點兒意義,要有點兒升華。
沒有寫的,還有一點,便是剛到南口農場和離開那里的時候,我都想起了園墻學長。他當時在這里工作的呀。可是,在這里,我沒有見到他。我曾經向老職工打聽過他,但是,他們對我搖搖頭,說農場里的職工太多,沒有聽說過這名字。望著滿山的蘋果樹結著累累的果子,有一種那個年紀無法訴說清楚的難言感覺。
山風呼呼拂面而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