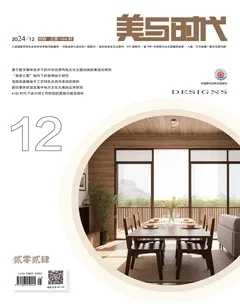地景藝術在藝術鄉建中的應用研究
摘" 要:在城鄉融合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為避免鄉村城市化、同質化發展,以設計帶動當地文化特色與資源的發展理念,對建設和諧鄉村、美麗鄉村、生態鄉村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目前中國的藝術鄉建尚處于發展探索階段,一些地方要么故步自封,要么過度商業化,許多傳統村落原有的文化特質正在逐漸消失。中國的鄉村文化根脈起源于土地,土地賦予鄉村文化和生機。在鄉村開展地景藝術帶動鄉村文化和旅游,是藝術鄉建的有效途徑之一。本文就鄉村如何利用土地資源,依托設計賦能開展鄉村地景公共藝術進行分析探討,提出將地景藝術運用于藝術鄉建需要考慮自然資源與當地文化的多元組合,以及空間關系與景觀引導等建議,肯定地景藝術在藝術鄉建中的應用可能性。
關鍵詞:鄉村振興;藝術鄉建;地景藝術
近年來,在美麗鄉村建設和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進程中,隨著國家三農政策的引導以及人們對鄉村田園生活的向往,藝術鄉建在鄉村發展進程中越來越體現出其不可替代的文化價值,這也是改善我國鄉村滯后的文化和經濟環境的重要力量。鄉村文化在我國傳統文化中占據至關重要的地位,它是我國傳統信仰的承載,是中國文化的根基[1]。地景藝術作為人與自然互動交流的作品,具有天然的屬性,是藝術家利用自然環境素材進行創作的藝術品。如大地、森林、草地、農田、山岳、河流、沙漠、峽谷、平原,甚至石柱、橋、墻、建筑物、遺跡等都是藝術家常用的材料。而他們大多會保持材料的自然本質,巧妙地運用藝術創作的手法,加以造形,架構視覺意象,引起人們的共鳴和思考。地景藝術于鄉村腹地的廣泛應用,已成為勾勒鄉村獨特風貌、豐富鄉村文化內涵的重要途徑。地景藝術不僅能為鄉村景觀設計和建筑改造等披上藝術的華彩,使之成為傳承與創新文化意象的載體,而且能在潛移默化中提升鄉村居民的審美鑒賞能力和對美好家園的認同感,同時為鄉村振興助力,促進文化和經濟的繁榮。然而,現狀表明,部分鄉村在推進振興過程中,雖不乏諸如山林、草地、稻田等地景藝術的涌現,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帶來了短暫的經濟效益,但普遍面臨著過度商業化和風格同質化的現象,這些地景藝術不僅未能充分彰顯鄉村的個性與文化獨特性,也未能有效提升村民的審美素養。鑒于此,深入探索鄉村地景藝術的本質與潛能,讓鄉村振興的理念與鄉村現實情境深度交融,顯得尤為重要。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激活鄉村的每一個角落,賦予鄉村以鮮活的藝術氣息,讓村民們在日常生活中直觀感受到美的熏陶,從而在心靈深處播下文化自信與美學自覺的種子,促進鄉村社會的全面發展與進步。
一、地景藝術與藝術鄉建的交響
藝術鄉建的根本目的是促進鄉村經濟和文化發展,鄉村發展的本質是人的發展,鄉村振興的要義是人的振興,只有村民參與和主導的鄉村振興才是真正的鄉村振興[2]。當前的藝術鄉建舉措多集中于硬件的翻新與美化,如建筑整修、商業布局優化及環境綠化。這些雖有必要,但若僅停留在表層改造,未深入觸及鄉村的內在肌理,無意中可能會損害鄉村的自然生態與文化平衡,引發同質化和過度商業化的風險。地景藝術的引入,為鄉村文化探尋自然之美和促進旅游發展不啻為一種可行的路徑。地景藝術在藝術鄉建過程中主張與自然和諧共生,利用鄉村自然地形、原生材料、農作物等進行藝術創作,既能減少對鄉村自然景觀的人為干擾,又能深挖地域特色,促進藝術與鄉村生態、文化的深度融合,增強村民的文化自豪感和身份認同。“藝術就像嬰兒,需要有人照顧。”[3]地景藝術需要社會的廣泛關注與支持,方能在鄉村的土壤中生根發芽,茁壯成長,確保藝術實踐深植于鄉土,擁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源自本土的傳承價值。這豐富了鄉村文化的多樣性,也賦予了鄉村振興以更強的文化自信和生態可持續性,為實現全面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創新路徑和精神支撐。通過地景藝術的巧妙構思,使鄉村的自然風貌、歷史沉淀與現代審美得以完美融合,既點亮了鄉村環境,又激發了鄉村內在的生命力與創造力,讓鄉村振興之路綻放出獨特的文化光芒與生態活力。
二、地景藝術對于藝術鄉建的價值
在藝術鄉建的實踐探索中,地景藝術的巧妙融入,不僅是對鄉村景觀的美學加持,更是一種深刻的文化表達與生態理念的傳遞。其深遠意義不僅限于藝術本身的彰顯,更重要的是,它通過與鄉村土地的深度融合,展現了鄉村獨有的生態智慧與文化脈絡,揭示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傳統哲學。
(一)通過地景藝術開展藝術鄉建,達到鄉村文脈的詩意演繹
地景藝術,作為藝術鄉建的新進路,不僅僅是對自然景觀的簡單修飾,而是將藝術創作深深植根于鄉村的地理、歷史與文化脈絡之中。它超越了傳統藝術形式的邊界,通過與環境的對話,實現了一種空間敘事的詩意構建。藝術家們不再是外來者,村民也不是單純的生產者,而是鄉村故事的共同書寫者,他們的作品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與鄉村的日常、村民的記憶緊密交織。
“2020回巢·榮昌建筑裝置藝術展”是鄉村復興論壇第十一站。榮昌峰會的重頭戲展覽以榮昌非遺為主題,創作了《契約劇場》《布·景》等作品,讓非遺概念與當代文化形成聯系,營造視覺、聽覺、觸覺多重感官的奇妙感受,成為當代藝術介入鄉村的創新探索。
其中《契約劇場》設計創意來自中國鄉村寫契約時按手印的靈感,以榮昌紅陶堆砌而成,指紋是鄉土社會中“契約”的符號,充滿力量。紅色的陶土、紅色的手印,也是為了喚醒大眾對于契約的尊重。該作品不僅成為村民集會場所,同時指印按在大地上更是代表了國家對振興鄉村的承諾。
榮昌建筑裝置藝術展是鄉建團隊對榮昌村的重新表達,融合大眾審美,尊重自然環境、歷史遺存、本地文化和村民意愿,承載鄉村記憶。正如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說:“我們對于過去的概念,是受我們用來解決現在問題的心智意象影響的,因此,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的一種重構。”[4]
地景藝術成為連接鄉村過去與未來的橋梁,這既是對本土文化的深刻挖掘,也是對未來鄉村形態的創造性想象。
(二)通過地景藝術實現藝術鄉建,成為藝術家與村民共創的場域
地景藝術實踐的核心在于藝術家與村民的深度互動,這一過程不僅是藝術創作的需要,更是鄉村文化自覺與自信心的培養過程。藝術家通過工作坊、訪談、共同創作等方式,深入了解村民的生活習慣、民間故事、傳統技藝,從而創造出既有藝術美感又富含鄉土情懷的作品。村民參與地景藝術創作,不僅讓藝術作品更具生命力和地方特色,而且還有效激發了他們對本土文化的自豪感,促進了文化的自我傳承與發展。
中國貴州省大方縣內的古彝梯田是藝術家與村民共創的典范。藝術家的到來為當地村民帶來了外界的文化視角,同時也為藝術家提供了深入了解大方縣傳統文化的機會。這種交流有助于雙方的文化認同和尊重。藝術家利用色彩、線條和形狀等視覺元素,在村民的辛勤勞作下將當地特有的觀賞茶樹和玫瑰花等植物種植于梯田之上,從高處俯瞰,宛如一枚指紋,并隨著四季更替展現出不同的色彩,從春季的碧綠到秋季的金黃,再到冬季的銀白,梯田的色彩如同調色板一樣豐富,加之晨霧晚霞的光影變幻,創造出一幅幅生動的自然畫卷,吸引了眾多游客前來觀光,在助推當地旅游發展的同時,為周邊易地扶貧搬遷群眾增收提供了產業支撐。
地景藝術的在地性有助于避免藝術鄉建中常見的商業化與同質化傾向,還能夠提升鄉村的文化內涵與生態價值,推動藝術鄉建向可持續和深層次發展。
(三)通過地景藝術融入藝術鄉建,激發人與自然的共鳴
藝術鄉建的本質是一種利用藝術介入鄉村拉近人與自然、城市與鄉村關系的手段,地景藝術可以進一步拉近彼此的關系,初衷是重建現代人類和自然的相互依存關系,地景藝術的本質包括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社會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5]。
坐落于甘肅省瓜州的雕塑作品《大地之子》,憑借其巨大且孤獨的熟睡嬰兒形象,于廣袤無垠的戈壁沙漠間矗立,深刻寓意了人類初始狀態下的純潔無瑕與自然界的緊密聯系,映射出對大地母體深切的依賴與眷戀。該藝術品的創制與呈現過程,不僅彰顯了藝術與周遭自然景觀的無縫對接,更在于不破壞環境的前提下,融入自然,成為大自然中一道和諧的風景線。
可見地景藝術讓人與自然產生共鳴,在藝術鄉建的同時,用人類的思想,通過藝術的語言介入鄉村的方方面面,推動鄉村快速、健康的發展。
三、地景藝術在藝術鄉建中的應用路徑
結合上述案例與分析,地景藝術的方向不止于著重鄉村建筑、道路、橋梁、庭院、水塘、公共設施等改造,更在于發揮鄉村豐富的自身潛在的可創造性的資源,通過藝術家的創新理念,力求創造一個新的視覺藝術作品,以達到藝術賦能鄉村振興的目的。
(一)自然資源與當地文化的多元組合
為了推進地景藝術在藝術鄉建中的應用,合理地利用自然資源與當地文化必不可少。地景藝術汲取的靈感與素材直接來源于所在地域,卻又超越單一維度,展現多元化的表達。例如,我國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他們依托梯田、稻田與起伏的山巒,創造出既支撐生活又富含審美價值的農耕景象。這些場景不僅是生存之本,更深層次地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意涵與美學追求。在地景藝術的具體表現上,從細微處著眼,諸如以五谷雜糧為媒介的糧食畫,將日常食材轉化為富有創意的藝術品。再到宏觀層面,比如村民們共同創作的、旨在贊頌豐年的大型田園雕塑,這些都是對自然資源及地方文化的生動詮釋與再創造。在放大當地的資源優勢與文化優勢的同時,做到在藝術鄉建的過程中融入人文關照,并且產生差異性,滿足設計中的個性表達。
(二)空間關系與景觀引導
在地景藝術的創作與體驗中,多以空間關系與景觀引導巧妙地調動游覽者的多元感官,在著重于視覺和聽覺的同時,恰當地結合嗅覺、觸覺及心理元素,以此深化人與自然景觀之間的互動,激發場地的生命力。在高黎貢山西麓,帕連藝術村以其傣族傳統村落的風貌吸引著無數目光。村口的墻上,一幅名為《愛拍照的小女孩》的巨大壁畫栩栩如生。每當有人站在這位“小攝影師”的鏡頭前擺出姿勢,便與壁畫共同構成了一件生動的藝術作品。這幅畫不僅是村莊的標志性地景,更像是一位無聲的向導,引領著游客們的好奇心,使他們迫不及待地想要跟隨相機的視角,探索村落的每一處角落。地景藝術通過這種沉浸式的感官體驗,不僅能夠強化藝術品與鄉村環境的聯系,使其自然地融入鄉土肌理,還能在美化鄉村面貌的同時,忠實地踐行藝術鄉建的理念核心。
(三)當地村民與藝術家之間的互動
地景藝術活動中,當地村民與藝術家之間的互動顯得至關重要。藝術家與村民發生矛盾也不占少數,多因藝術家在創作時可能無意中使用了不恰當的文化符號或主題,觸犯了村民的禁忌或文化傳統,適得其反。藝術家應與村民相處中深挖當地的風土人情與文化傳承,從而激發創作靈感。如河南省洛陽市洛寧縣的前河村,村民與藝術家合力利用村中燒制的大口水缸擺出了一個巨大的藝術造型,好似身形婀娜的少女隨風翩翩起舞。藝術的魅力和山水的靈動交織,引來許多人駐足拍照,成為當地促進旅游的新地標。村民與藝術家的互動讓村民切實感受到地景藝術這種春風化雨的力量,提升傳統村落的文化氣氛,逐漸實現自我建設,從而促進“文化富民”的產業發展。
(四)商業化與同質化的反思與規避
地景藝術在藝術鄉建中的應用,還需警惕過度商業化和同質化的問題,它不同于簡單的旅游景觀打造,地景藝術的核心價值在于其地域性、獨特性和長期的可持續發展特性。因此,項目規劃時,必須超越短視的經濟效益追求,轉而聚焦于深層的社會文化價值與長遠影響。通過深入挖掘每個鄉村的獨特藝術創作資源,如歷史、生態、民族風情等,創作出不可復制的藝術場景,避免出現馮驥才先生所擔憂的“村落如果這樣發展下去,再過10年或15年,幾千個傳統村落就會和現在的大城市一樣千村一面的情況出現”[6]。
四、結語
地景藝術融入藝術鄉建,挖掘鄉村自然與文化資源。藝術家和村民共創出充滿創意情感的作品,美化景觀,提升建筑美學,注入人文導向,激發鄉村活力與個性。讓地景藝術超越地域空間、觸及精神共鳴,實現藝術品講述鄉村故事、播撒文化種子、催生豐富生態的有效價值,為人們提供沉浸式體驗,讓游客感知鄉村歷史,體驗“多維”美感。地景藝術鄉建互動模式的開展從藝術家主導轉至村民共創,也標志鄉村由外驅向內生發展,村民掌握文化脈絡,形成自我賦能循環。從而使地景藝術在藝術鄉建助力鄉村文化持續發展與品質提升方面發揮獨特的價值和優勢。
參考文獻:
[1]渠巖,王長百,許村.藝術鄉建的中國現場[J].時代建筑,2015(3):44-49.
[2]吳重慶,張慧鵬.以農民組織化重建鄉村主體性:新時代鄉村振興的基礎[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3):74-81.
[3]渠濛.大地藝術節的十個創新思想:日本鄉村藝術節如何振興社區?[J].公共藝術,2019(5):106-109.
[4]哈布瓦赫.論集體記憶[M].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85.
[5]劉鄭楠.地景藝術介入的建筑設計——以“鼓浪嶼計劃”為例[J].城市建筑,2022,19(1):145-150,155.
[6]胡春艷.中國傳統村落“千村一面”如何留住鄉愁[N].中國青年報,2016-11-24(8).
作者簡介:
宋遜,新疆師范大學藝術設計專業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藝術鄉建。
李文浩,碩士,新疆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生態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