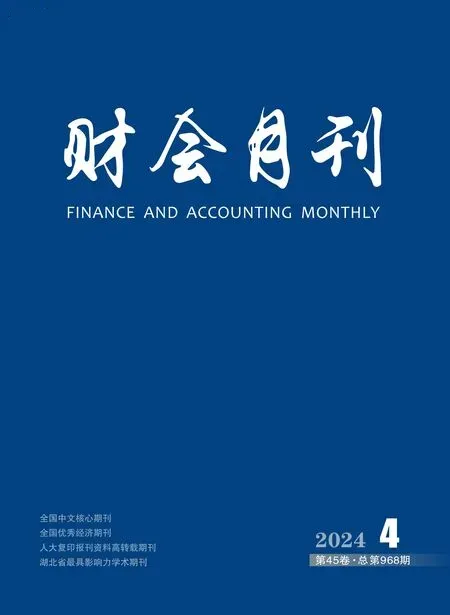企業漂綠研究綜述:動因、后果與治理
張長江(教授),楊 葉,王文韜
一、引言
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乃當前經濟社會重大命題,企業ESG(環境、社會和治理)理念由此備受重視。隨著ESG 規范不斷增多,企業傾向于開發更環保的產品和服務。然而,企業可能出于成本等因素考量并未真正履行綠色承諾,其環保主張模棱兩可、具有欺騙性,漂綠的概念由此誕生(Seele 和Gatti,2017)。企業不符實際的“漂綠”式溝通既容易誤導消費者和投資者,也不利于企業聲譽的持續構建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漂綠”議題受到企業界、金融界、學術界的廣泛關注(黃世忠,2022),對漂綠問題的深入研究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業漂綠行為(姚瓊等,2022)。在“漂綠”綜述研究方面,De Freitas Netto 等(2020)對漂綠的定義和形式進行了系統性綜述;Delmas和Burbano(2011)構建了由“外部—組織—決策者”三個層面組成的漂綠動因分析框架。我國學界開展漂綠研究較晚(李大元等,2015),現有研究主要基于漂綠個案展開,且主題較分散,缺乏對漂綠問題研究成果的系統梳理。
Web of Science(WOS)數據庫是全球最大、國際公認的反映科學研究水準、覆蓋學科最多的綜合性學術信息資源庫。筆者在WOS 核心合集中檢索主題含“green?washing”的文獻,共獲得2011 ~2022 年的334 篇相關論文。WOS 收錄的第一篇“漂綠”論文是Parguel 等(2011)發表的“How Sustainability Ratings Might Deter‘Green?washing’:A Closer Look at Ethical Corporate Communica?tion”一文。樣本文獻篩選過程如下:①“篇關摘”初選。閱讀334篇論文的篇名、關鍵詞和摘要,初步剔除不符合主題的論文,剩余190篇。②全文精讀再選。對文獻逐一閱讀,排除研究內容、方法不符的論文,最終篩選出相關論文88 篇(見圖1)。其中SSCI 論文55 篇、SCI 論文20篇、SSCI/SCI 論文13 篇,發文量排名前五的期刊分別是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13 篇)、Sustainability(9 篇)、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7 篇)、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6篇)、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3 篇)。本文擬從企業漂綠概念界定、漂綠形式、漂綠解釋理論、漂綠動因、漂綠后果和漂綠治理機制等方面進行總結歸納,以期為該領域研究提供參考。

圖1 2011 ~2022年WOS“漂綠”論文時序分布
二、企業漂綠的理論研究
(一)企業漂綠界定
漂綠涉及多方面,對其進行嚴格界定較為困難,學界對其定義經歷了從單一維度向綜合視角發展的軌跡。Delmas和Burbano(2011)從溝通虛假信息的角度,將漂綠定義為“環境績效不佳,但針對環境績效問題進行積極溝通”。該定義的缺陷在于將漂綠行為的認定局限于積極溝通的企業中,缺乏對回避溝通企業亦存在漂綠可能的考慮。比如,Lyon和Maxwell(2011)就認為漂綠不僅包括有意提供虛假信息,還包括刻意不充分披露負面信息的選擇性披露行為。Lyon 和Montgomery(2015)還提出了視覺圖像范疇的漂綠,即模糊的綠色價值主張和視覺圖像的使用(如使用有綠色含義的圖像或卡通人物)。鑒于企業可持續發展相關話題具有跨學科性,僅考慮環境問題的漂綠概念過于狹窄。Seele和Gatti(2017)從綜合視角定義了漂綠,主張在討論漂綠時納入環境、社會和經濟維度,將漂綠定義為“社會面對企業發布誤導性的環境相關信息的共同指責”;Pizzetti等(2021)進一步將漂綠的范疇拓展到“與企業自身運營無直接關系,發生在供應鏈層面的漂綠”。
(二)企業漂綠形式
首先,根據發生層面的不同,漂綠可分為公司層面漂綠和產品層面漂綠(Delmas和Burbano,2011)。前者指企業在對外宣傳其環保努力、塑造良好形象的同時,卻做出環境不友好行為。相較而言,學界對后者的關注更多。美國環境營銷公司Terra Choice 曾從法律、道德角度出發,歸納出產品層面漂綠行為的七宗罪,包括流于表面、毫無憑據、用詞含糊、混淆視聽、避重就輕、欺騙公眾、崇拜認證,它們成為企業以環境主張誤導消費者的主要方式(Baum,2012)。Lyon和Montgomery(2015)也將漂綠分為七類,與上述分類有較多重疊,但更關注企業綠色欺騙行為和利用外部各方建立信譽的情形。
其次,按照表達方式的不同,漂綠可分為聲稱式漂綠和執行式漂綠。聲稱式漂綠被普遍關注,是指在廣告中使用文字性觀點來產生誤導性的環境主張(Lyon和Maxwell,2011)。Parguel 等(2015)提出了早期被忽略的“執行式漂綠”,指在廣告中使用自然的元素而不直接用語言表達,如使用顏色(藍色、綠色)、聲音(鳥類、海洋)和自然景觀(山脈、森林)。
再次,漂綠的其他形式。一是根據企業的“作為”與“不作為”將漂綠分為“轉移注意力”和“解耦”兩類(Siano等,2017)。前者指通過虛假披露來隱藏不道德的商業實踐,轉移利益相關者注意力的行為;后者指企業聲稱滿足利益相關者的綠色期望,卻不對其商業實踐進行任何實質性改變。“轉移注意力”和“解耦”策略都基于描述企業在可持續性實踐方面正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來滿足利益相關者的期望,這種傳統方法認為溝通是行動的次要內容,公眾只能被動接收企業傳遞的社會責任信息。Siano 等(2017)據此提出第三類漂綠形式,即企業因難以完成先前的綠色承諾而做出一些不利于其可持續發展的行為。二是傳導性漂綠。例如,Pizzetti 等(2021)提出了供應鏈層面的漂綠形式,即直接漂綠、間接漂綠和替代漂綠。直接漂綠是指關于可持續性的言行不一發生在公司內部;發生在供應商層面的言行不一屬于間接漂綠,供應商的不當行為對客戶的負面影響較小;替代漂綠是指關于可持續性的言行不一發生在供應鏈中間,這種情況發生于一家奉行綠色發展的公司被指控漂綠,因為它從不符合可持續性標準的供應商那里購買原材料或服務。一家公司因所在供應鏈上其他企業的行為遭受了漂綠指控,雖然自身沒有行為不端,但它沒有監控或制約供應商漂綠,也意味著其未全力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三)企業漂綠的理論詮釋
1.制度理論。制度理論假設企業戰略已通過了一系列適應過程的制度化(Dubey,2017),并解釋了組織同構現象(Heras-Saizarbitoria,2016),即一個組織的程序或結構與另一個組織的程序或結構相似,這是在一定約束下進行模仿的結果,組織同構的動機是實現制度壓力賦予的合法性(Walker 和Wan,2012)。制度環境制約著組織同構的社會責任行為,影響著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行為和溝通(Ruiz-Blanco 等,2022)。根據制度理論,企業為取得合法利益而存在異質性反應,外部環境不同是影響企業漂綠的關鍵因素,如企業所處行業的環境污染程度和對客戶的信息透明度會影響企業漂綠的概率和形式。
2.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最終意圖是影響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認知。如果企業參與漂綠,他們可能會通過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來呈現社會責任績效較高的形象,并通過這些手段歪曲事實(Ruiz-Blanco 等,2022)。承受較大利益相關者壓力的企業具有更高的聲譽風險,因此漂綠的動機更弱。利益相關者施加的壓力及其評估組織行為的能力涵蓋在聲譽風險評估中,這是理解漂綠的一個關鍵因素。目前,公眾對環境議題高度敏感,環境問題給公司帶來了巨大壓力。公眾對環境問題的日益重視,強化了社會公眾在懲戒漂綠行為中的作用。然而,如果漂綠被發現的可能性很小,或者漂綠成本低于如實報告的成本,企業仍會為了應對利益相關者的壓力而漂綠。Perez-Batres等(2012)就利益相關者壓力對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公司對不同水平的利益相關者壓力的反應不同,象征性還是實質性履行環境制度取決于利益相關者壓力的類型和強度,以及手頭應對這些壓力的資源。Testa等(2018a)調查表明,盡管制度壓力普遍促進企業積極主動地展開環境實踐,但利益相關者的影響可使這些實踐僅被表象化實施。
3.信號理論。信號理論探討了代理人如何使用不同的信號來改善信息不對稱和溝通低效率問題(Berrone等,2017)。信號理論可解釋“為什么企業發布虛假的綠色聲明可以誤導利益相關者”。首先,企業可通過對環境問題的承諾來獲得競爭優勢。Connelly等(2011)認為,每個企業均有機會決定是否向外界發出真實信號,這意味著低績效企業在發布虛假信息時也能得到預期的合法性收益。因此,利益相關者無法根據企業參與綠色傳播或綠色廣告來區分企業是實質性實施綠色發展還是純粹的漂綠行為。其次,綠色溝通的必要性源自信號發出者和接收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評估企業環保行為對公眾來說非常具有挑戰性,因為大多數人對企業生產流程的真實環境績效、清潔技術等缺乏直接了解。Ruiz-Blanco 等(2022)用信號理論闡釋了可持續發展報告作為一種合法性工具對企業的影響。企業決策者用顯性的可觀察信息來表明不可觀察的隱性信息(綠色承諾等),以緩解信息不對稱,試圖傳達其不太可能漂綠的正向信號。
綜上,現有文獻主要將制度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信號理論作為理論基礎,從企業所處的行業、利益相關者壓力和信息溝通角度研究企業漂綠動因。制度理論和利益相關者理論詮釋了外部環境和利益相關者壓力對企業漂綠行為的影響,信號理論解釋了漂綠的動力機制。亦有學者用GONE 理論解釋漂綠形成機制(Chen 等,2022)。相比之下,針對企業漂綠后果研究的理論基礎更為缺失和分散,如基于社會認同理論(Xiao 等,2022)、心理契約理論(Sun和Shi,2022)研究漂綠對消費者的影響,以前景理論為基礎研究公司的漂綠行為對財務業績的影響(Walker和Wan,2012)。
三、企業漂綠的動因與后果實證研究
(一)企業漂綠的驅動因素
漂綠沒有一個固定的形成機制,而是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現有文獻對漂綠動因的關注尚不全面。經文獻整理發現,漂綠動因研究主要包括外因(政府、社會)與內因(包括企業自身各種特征)(見表1),內因與外因既獨立作用也相互影響。

表1 企業漂綠動因的研究發現
漂綠的外因包括來自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等非市場主體以及消費者等市場主體的壓力。首先,消費者的綠色需求使企業為了提高聲譽而產生漂綠傾向(Baum,2012)。其次,消費者與企業之間存在的信息不對稱、政府監管力度不足也為漂綠提供了可能性。Garrido等(2020)基于信號理論,認為消費者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導致了漂綠,強制性綠色認證可作為明確的信號,對消費者的綠色消費決策產生影響。Kim 和Lyon(2015)研究發現,往往是受到嚴格監管的大公司實施漂綠,但來自環保組織的壓力降低了漂綠的可能性。Marquis等(2016)也證實不易受到審查的企業更有可能實施漂綠。
漂綠的內因涉及企業規模、組織能力、財務或非財務表現等。規模較大、成長型企業為了滿足利益相關者需求而更傾向于漂綠(Delmas 和Burbano,2011)。Blome 等(2017)利用德國118家公司的數據研究發現,漂綠受到權威的領導風格影響,并受到道德激勵的抑制。Delmas 和Burbano(2011)也研究了公司激勵結構和公司內部溝通有效性等漂綠的內因,發現內外因存在相互作用——寬松的外部監管使得內因對漂綠產生更顯著的影響。Kim 和Lyon(2015)的研究表明,處于競爭激烈環境中的企業在出現虧損時可能會運用漂綠手段建立聲譽,這與Zhang(2022)的研究結果相同。因此,企業環保溝通是由內外因素相互作用決定的。
漂綠的動因涉及政府、社會和企業內部因素三個方面,當前文獻對漂綠動因的研究更集中于企業特征、組織能力、業績表現等內部因素,可能的原因是變量相對單一、數據更便于獲取。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和對生態保護的追求,媒體影響力不斷加強,環境相關的制度法規更加完善,企業可能面臨更復雜的外部環境和風險,因此外部驅動因素值得深入探討。
(二)企業漂綠的經濟后果
1.漂綠對消費者的影響。漂綠對消費者的影響研究包括兩類:一是消費者感知到的漂綠對消費者的影響,二是企業漂綠行為本身對消費者的影響。感知到的漂綠指消費者對綠色廣告信息和企業實際社會責任履行之間差異的反應(Nyilasy 等,2014)。感知到的漂綠會導致消費者產生不信任感。Chen 和Chang(2013)實證檢驗了漂綠感知對綠色消費者困惑(green consumer confusion)、綠色感知風險和綠色信任的影響,結果顯示漂綠感知與綠色信任負相關,與綠色消費者困惑和綠色感知風險正相關。這意味著漂綠不僅直接對綠色信任產生負面影響,而且通過綠色消費者困惑和綠色感知風險間接對其產生負面影響。
企業漂綠行為本身對消費者具有正負兩方面的影響。Parguel 等(2015)認為,漂綠對消費者產生何種影響的關鍵問題是消費者是否認識到企業發布綠色聲明的內在動機。企業社會責任溝通的兩種因果歸因包括對行為者傾向的歸因(內在動機)和對環境因素的歸因(外在動機)。當面對企業社會責任溝通時,消費者可能會推斷企業存在兩種動機:具有真正的環保意識(內在動機)或試圖利用可持續發展趨勢的機會主義優勢(外在動機)。然而,歸因理論假設消費者相信漂綠企業實際上踐行了綠色發展,且企業只因這種行為產生不同的動機。De Jong等(2018)為了修正這一缺陷,推導出漂綠效應的雙向理論,討論了消費者可能質疑企業綠色聲明的情形。因此,漂綠既可能帶來消費者對企業綠色認知的負面影響,也可能在沒有明確證據的情況下讓消費者對漂綠企業產生積極認知。
2.漂綠對企業自身的影響。漂綠對企業自身的影響包括對企業聲譽和財務績效的影響。漂綠對企業聲譽的影響表現在對品牌滿意度和投資意圖的影響上。Leonidou等(2013)發現,消費者在感知到企業不負責任的行為后,對其品牌的滿意度會降低。Akturan(2018)對500 名消費者的調查發現,漂綠對綠色品牌信譽產生了負面影響。漂綠會損害客戶滿意度,即使它此前并沒有造假(Xiao等,2022)。Gatti 等(2021)研究發現,漂綠這一欺騙行為對投資者的投資意圖產生負面影響。企業聲譽的負面影響也會進一步影響企業經營業績與財務績效,但這僅限定于漂綠行為被暴露后的情形。
有許多學者采用不同樣本對漂綠在一般情況下對企業績效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已有研究發現,漂綠對企業整體績效指標沒有積極影響。一項來自中國的實證研究表明,漂綠與累積超額收益率(CAR)負相關,而企業環境績效與CAR 顯著正相關(Du,2015)。Walker 和Wan(2012)針對加拿大污染行業漂綠企業的研究發現,漂綠有損企業財務績效。Wu和Shen(2013)以22個國家的162家銀行為樣本進行研究,發現社會責任行為與財務績效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但有漂綠行為的銀行則不然。Testa等(2018b)對58個國家的19個行業上市公司的實證結果顯示,漂綠并未給企業帶來市場價值和運營績效方面的回報。
3.漂綠對社會的影響。漂綠會導致市場的逆向選擇和環境披露信號失效。漂綠產品和綠色產品混合于市場中,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消費者無法辨別真偽,即使他們愿意以較高價格購買綠色商品,理性的消費者也只能支付平均價格。這導致綠色商品市場開始萎縮,甚至真正的綠色商品只能退出市場(Lee 等,2018)。真正的綠色商品不能得到認可,由此環境問題也無法得到改善。環保消費者由于難以信任綠色營銷活動,導致社會交易費用增加、交易效率低下(Polonsky 等,2010)。漂綠行為的普遍發生增加了政府監管和制度實施的難度,漂綠行為的曝光不僅會放大企業不當行為的負面影響從而進一步弱化投資者的投資意向(Gatti等,2021),還會使公眾喪失對法律制度的信任,不利于社會穩定。而整頓市場、重塑消費者信心的努力又會進一步增加監管成本,從而損害社會福利。
綜上所述,現有文獻關于企業漂綠對消費者的影響研究較為透徹,從消費者感知到的漂綠和企業漂綠行為本身兩個緯度展開,且有利影響與不利影響均獲解釋。關于漂綠對企業自身影響的探究,多位學者以不同樣本對于漂綠對財務績效的影響進行了驗證。除此之外,還可以對非財務績效方面進行拓展,如組織韌性、創新績效等。從長遠看,漂綠對企業沒有益處,但漂綠在短期內是否存在對企業某些方面的積極作用尚未得到論證。漂綠對社會的影響最為復雜且深遠,既涉及經濟角度又涉及非經濟角度,該領域實證研究存在較大空白。
四、企業漂綠的治理機制研究
(一)政府監管
政府監管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可以維護經濟總量平衡,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彌補市場固有缺陷。政府對漂綠實施監管,意味著政府利用公共權力規范企業的漂綠行為(Parguel等,2011)。根據制度理論,環境規制可作為制度壓力,通過監管合法性來影響企業環境戰略。
首先,政府制度監管作為強制性外部壓力,是政府部門應對漂綠的關鍵制度因素。其次,行政處罰也是一種強制性壓力,是控制環境污染的傳統規制手段。行政處罰機制可以有效控制企業的漂綠行為,機制有效的必要前提是行政處罰額應高于漂綠行為的溢價(Sun和Zhang,2019)。為提升地方政府控制企業漂綠行為的積極性,還應完善地方綠色發展和創新能力等指標的評價體系。最后,政府綠色補貼在一定條件下對漂綠行為產生影響。Sun和Zhang(2019)認為,如果政府補貼金額足夠大,那么企業最終會傾向于選擇綠色創新戰略;如果政府補貼金額較小,那么只有一些占主導地位的企業可以選擇綠色創新戰略;如果政府補貼足夠低,那么企業最終會選擇漂綠策略。因此,為了鼓勵企業更積極地參與綠色創新,政府必須使補貼數量合理化。
(二)社會監督
Lyon 和Montgomery(2015)為社交媒體對漂綠的影響研究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他們假設社交媒體使政府更容易發現和懲罰貪婪,從而有助于控制漂綠。社交媒體降低了政府監管成本,也促進人們對被漂綠企業的關注和抵制。來自獨立機構的可持續性評級通過總結利益相關者對公司履行社會和環保責任的評價來提供信息。Parguel 等(2011)認為,ESG 評級會影響消費者對企業內在動機的看法,進而影響企業聲譽。因此,ESG評級可以有效阻止漂綠,并鼓勵有道德的公司加強企業社會責任實踐。作為規范性壓力,不誠實的名單披露也被認為是治理漂綠的有效方法。外部監管機構可以通過互聯網、報紙和其他公共論壇發布這份不誠實的名單,導致參與漂綠的企業遭受重大聲譽損失。統一的綠色認證標準體系可以規范綠色認證市場,充分有效地發揮環境信息傳輸的作用(He 等,2020)。然而,優質和劣質的認證評估系統混合在一起,容易對消費者造成誤導。
(三)市場透明
Lee等(2018)采用雙重壟斷模型進行研究發現,如果對漂綠進行監管,企業將在成本和價格上進行競爭,最終要么都變成綠色,要么都變成棕色,從而達到平衡狀態。因此,僅僅針對漂綠行為進行監管并不能杜絕漂綠,企業還要考慮價格競爭。而如果市場信息量增加,市場上有一些知情的客戶,公司之間的競爭會促使其中一家公司走向綠色,進而促使市場競爭改善公司環境績效。因此,決策者不應該監管漂綠,而應該完善市場機制,提升消費者的環保意識及其所需的信息透明度,并降低公司環境實踐的成本。消費者所需的信息透明度提高、懷疑態度減少與消費者行為之間有直接聯系,消費者只能在信息透明度高、可信度高且抵制漂綠行為的競爭市場中做出合理的購買決定(Lemke和Luzio,2014)。
總體而言,企業漂綠難以通過某單一因素的解決得以治理,多種治理方法為漂綠的控制提供了可能性。法律法規作為強制性壓力起著根本性作用,政府的懲罰和補貼機制應足以規范企業行為;社會監督通過同構機制引導企業行為,可加強相關措施的有效性研究;市場透明度作為非監管手段提供了治理漂綠的新思路,但還需深入研究具體舉措。
五、結論與展望
(一)結語
ESG 研究之“火”催生了漂綠研究之“熱”,漂綠研究給“火熱”的ESG研究帶來了新的“冷思考”。回顧近12年國際高水平“漂綠”論文,筆者有如下發現:第一,從論文刊載情況看,“漂綠”論文數量總體呈快速增長趨勢,近三年出現“爆棚”式增長,SSCI收錄期刊發文量占80%以上,主要發表于企業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管理領域期刊。可見,隨著環境問題的日趨嚴峻,研究公司環境治理相關主題的意義越發重大。第二,在漂綠理論研究方面,以制度理論、利益相關者理論、信號理論等理論為基礎,對漂綠能夠產生的基礎背景進行了解釋,對漂綠概念和形式的研究實現了由環境行為漂綠、社會責任漂綠向ESG 漂綠、供應鏈漂綠拓展,由環境披露漂綠、價值主張漂綠向視覺形象漂綠、可持續戰略漂綠拓展,由聲稱式漂綠與執行式漂綠向注意力型漂綠和傳導性漂綠拓展。第三,在漂綠的因果研究方面,初期研究者單向探討企業漂綠的內在動因或外在動因,近期研究者開始關注外因和內因的聯動調節分析,漂綠動因研究不斷深入系統。漂綠的后果研究從關注漂綠對消費者、企業自身的影響,向對社會的影響等更廣泛范疇探究。第四,在漂綠治理機制研究方面,研究者從政府監管(如制度監管、行政處罰、綠色補貼)、社會監督(如社交媒體、ESG評級、綠色認證)和市場透明等方面提出了治理舉措。
(二)展望
目前對漂綠的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性。對漂綠的研究方法方面,當前多采用概念性思辨法和觀察法,對漂綠在宏觀層面的后果和多種治理措施的有效性還缺少實證檢驗。從研究樣本看,以披露了年度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的上市公司為主,而基于一般企業的調查較少;對發達國家的研究更豐富,而缺少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因此,針對漂綠的研究方法還可以更多樣化,范圍可以更廣,使漂綠研究更有理論效度和實踐說服力。
展望未來,筆者認為企業漂綠研究可向以下方向延伸。其一,增加漂綠理論研究多元性,從心理機制和情景機制角度為企業漂綠問題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利用心理機制研究個體選擇漂綠的動機,如激勵理論、ERG(生存—相互關系—成長)理論等;利用情景機制研究外在情景與漂綠行為的相互影響,如博弈理論、生態系統理論、ABC(態度—行為—情景)理論等。其二,擴展對漂綠行為的界定。隨著全球的氣候危機加劇,減少碳排放成為企業面臨的難題,企業依賴碳抵消路徑卻以綠色自居等低碳行為也應當歸屬于漂綠范疇。以科學的方法判定漂綠也就是以科學的方法判定綠色,只有厘清企業環境行為的本質,才能更有效地提出漂綠的治理方案。其三,強化漂綠動因研究系統性。未來在緊跟企業低碳轉型新動向探尋漂綠新動因的同時,更要加強對漂綠動因的內外系統性分析,提升漂綠動因研究的精準度和情境化水平。基于我國本土的制度環境,通過識別多種類型的漂綠行為,將它們與各個領域的誤導性行為和溝通聯系起來。其四,凸顯漂綠后果研究聯動性與深入性。相對而言,動因研究應優先于后果研究,后續研究要注重動因和后果的對應性關聯研究,漂綠后果在行業間、供應鏈、資金鏈、產業鏈的傳導風險值得深入探討。此外,關于漂綠對社會的影響,現有文獻大多在沒有強有力證據支持的情況下認為漂綠會損害社會福利,而針對漂綠對社會的有利作用以及多種形式的危害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理論與實踐研究。其五,重視漂綠治理研究協同性。協同治理的核心是構建更加開放、共同參與、共同治理的政治環境以實現公共秩序的持續穩定,后續研究需重點探究政府、市場、企業、消費者、媒體、社會中介、金融機構等多方力量協同參與,通過建立透明的管理體系與分享責任的機制來治理漂綠。
【 主要參考文獻】
黃世忠.ESG報告的“漂綠”與反“漂綠”[J].財會月刊,2022(1):3 ~11.
李大元,賈曉琳,辛琳娜.企業漂綠行為研究述評與展望[J].外國經濟與管理,2015(12):86 ~96.
姚瓊,胡慧穎,豐軼衠.企業漂綠行為的研究綜述與展望[J].生態經濟,2022(3):86 ~92+108.
Akturan U..How does greenwashing affect green branding equity and pur?chase intention?An empirical research[J].Marketing Intelligence & Planning,2018(7):809 ~824.
Baum L..It's not easy being green...Or is it?A content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claims in magazine advertisem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J].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2012(4):423 ~440.
Berrone P.,Fosfuri A.,Gelabert L..Does greenwashing pay off?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actions and environmental legitimacy[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7(2):363 ~379.
Blome C.,Foerstl K.,Schleper M..Antecedents of green supplier championing and greenwashing:An empirical study on leadership and ethical incentive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7(152):339 ~350.
Chen Y.F.,Wang G.,He Y.,et al..Greenwashing behavior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There is an elephant in the room![J].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2022(43):64597 ~64621.
Chen Y.,Chang C..Greenwash and green trust:The mediation effects of green consumer confusion and green perceived risk[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3(3):489 ~500.
De Freitas Netto S.,Sobral M.,Ribeiro A.,et al..Concepts and forms of greenwashing:A systematic review[J].Environmental Sciences Europe,2020(1):19.
De Jong M.,Harkink K.,Barth S..Making green stuff ?Effects of corporate greenwashing on consumers[J].Journal of Business and Technical Communica?tion,2018(1):77 ~112.
Delmas M.,Burbano V..The drivers of greenwashing[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11(1):64 ~87.
Du X..How the market values greenwashing?Evidence from China[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5(3):547 ~574.
Garrido D.,Espinola-Arredondo A.,Munoz-Garcia F..Can mandatory cer?tification promote greenwashing?A signaling approach[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2020(6):1801 ~1851.
Gatti L.,Pizzetti M.,Seele P..Green lies and their effect on intention to in?vest[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21(127):228 ~240.
He Q.,Wang Z.,Wang G.,et al..To be green or not to be:How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shape contractor greenwashing behaviors in construction projects[J].Sustainable Cities and Society,2020(63):102462.
Kim E.,Lyon T..Greenwash VS.brownwash:Exaggeration and undue modesty in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disclosure[J].Organization Science,2015(3):705 ~723.
Lee H.,Cruz J.,Shankar 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issues in supply chain competition:Should greenwashing be regulated?[J].Decision Sciences,2018(6):1088 ~1115.
Lemke F.,Luzio J..Exploring green consumers'mind-set toward green product design and life cycle assessment the case of skeptical brazilian and portuguese green consumers[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14(5):619 ~630.
Leonidou L.,Kvasova O.,Leonidou L.,et al..Business unethicality as an im?pediment to consumer trust:The moderating role of demographic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3(3):397 ~415.
Lyon T.,Montgomery A..The means and end of greenwash[J].Organization&Environment,2015(2):223 ~249.
Lyon T.,Maxwell J..Greenwash: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under threat of audit[J].Journal of Economics&Management Strategy,2011(1):3~41.
Marquis C.,Toffel M.,Zhou Y..Scrutiny,norms,and selective disclosure:A global study of greenwashing[J].Organization Science,2016(2):483 ~504.
Nyilasy G.,Gangadharbatla H.,Paladino A..Perceived greenwashing: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green advertising a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n consumer reac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4(4):693 ~707.
Parguel B.,Benoit-Moreau F.,Russell C..Can evoking nature in advertising mislead consumers?The power of 'executional greenwash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2015(1):107 ~134.
Parguel B.,Beno?t-Moreau F.,Larceneux F..How sustainability ratings might deter 'greenwashing':A closer look at ethical corporate communica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1(1):15 ~28.
Perez-Batres L.A.,Doh J.P.,Miller V.V.,Pisani M.J..Stakeholder pressures as determinants of CSR strategic choice:Why do firms choose symbolic versus substantive self-regulatory codes of conduct?[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2(2):157 ~172.
Pizzetti M.,Gatti L.,Seele P..Firms talk,suppliers walk:Analyzing the locus of greenwashing in the blame game and introducing 'vicarious greenwashi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21(1):21 ~38.
Polonsky M.,Grau S L.,Garma R..The new greenwash:Potential marketing problems with carbon offset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Studies,2010(1):49 ~54.
Ruiz-Blanco S.,Romero S.,Fernandez-Feijoo B..Green,blue or black,but washing-what company characteristics determine greenwashing?[J].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2022(3):4024 ~4045.
Seele P.,Gatti L..Greenwashing revisited:In search of a typology and accusa?tion-based definition incorporating legitimacy strategies[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17(2):239 ~252.
Siano A.,Vollero A.,Conte F.,et al.."More than words":Expanding the taxonomy of greenwashing after the Volkswagen scandal[J].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2017(71):27 ~37.
Sun Y.,Shi B..Impact of greenwashing perception on consumers' green pur?chasing intentions: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Sustainability,2022(19):12119.
Sun Z.,Zhang W..Do government regulations prevent greenwashing?An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of heterogeneous enterprises[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19(231):1489 ~1502.
Testa F.,Boiral O.,Iraldo F..Intern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and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Can stakeholders pressures encourage greenwashing?[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8a(2):287 ~307.
Testa F.,Miroshnychenko I.,Barontini R.,et al..Does it pay to be a green?washer or a brownwasher?[J].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2018b(7):1104 ~1116.
Walker K.,Wan F..The harm of symbolic actions and greenwashing:Corpo?rate a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o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their financial implications[J].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2012(2):227 ~242.
Wu M.,Shen C..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banking industry:Mo?tives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2013(9):3529 ~3547.
Xiao Z.,Wang Y.,Guo D..Will greenwashing result in brand avoidance?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J].Sustainability,2022(12):7204.
Zhang D..Are firms motivated to greenwash by financial constraints?Evi?dence from global firms' data[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Accounting,2022(3):459 ~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