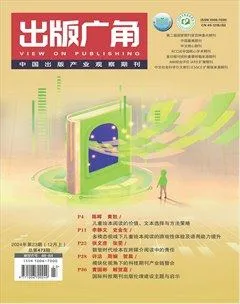數智時代繪本在跨媒介閱讀中的責任
【摘 要】數字技術帶來兒童閱讀環境的顯著變化,學習型媒介引發課內閱讀的結構變化、家長閱讀中介功能的減弱及課外閱讀時間的減少。引發兒童閱讀行為變化的主要因素有數字閱讀任務的增加、數字“百草園”的擴張與成年人閱讀媒介功能的消解、兒童課外閱讀與數字媒介使用的博弈。針對這些變化,應慎重甄別繪本的數字化方向,以繪本的創作規律出發,由技術工作者、兒童文學創作者、出版界聚合力量,為兒童閱讀建設具有共識的數字環境,從而延伸繪本在知識代際傳播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
【關" 鍵" 詞】繪本;跨媒介閱讀;兒童閱讀;知識代際傳播
【作者單位】張文彥,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張雯,青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中圖分類號】G24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4.23.004
人類依托不同的載體在不同的時代中為知識和藝術貢獻經典,經典的傳世并非簡單的時空位移,而是因更迭的媒介持續發生質變的結果,媒介在質變中發揮了破壞和創造的力量。一方面,新生媒介野蠻生長,會破壞傳統媒介與作品相互依存的穩定關系,新的信息生態會遮蔽甚至掩埋一些舊作品。另一方面,舊作品會因新的媒介表達方式而獲取再生的機會,如圖書成為電子書,小說改編成電影,電影轉變為電子游戲等,作品的形式發生了變化,在差異中產生了創新。在悠久的圖書發展史中,繪本也是一種“新媒介”,其將豐富的知識、深沉的思想、精美的藝術、絢麗的想象和充沛的情感以符合兒童身心需要、圖文并茂的方式進行精工細作,使之成為一種承載著愛、理想和祝福的藝術品,成為知識代際傳播中增進長幼互相理解的優秀載體。
在媒介環境巨變的今天,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數智時代兒童的閱讀環境正在發生哪些深刻變化,這些變化如何影響兒童閱讀,如何看待繪本跨媒介閱讀的出現及發展,繪本閱讀在新的媒介環境、知識代際傳播中扮演何種角色。
一、 兒童閱讀環境及行為的變化
20世紀80年代,電視機、錄音機在我國逐漸普及,各種文學名著被改編成電視、廣播節目,兒童就此進入跨媒介閱讀時代。40多年后的今天,數字媒介正在引發跨媒介閱讀格局的巨變。《失控:全人類的最終命運和結局》《24/7:晚期資本主義與睡眠的終結》等著作向我們揭示了數字媒介對成年人的強大控制力,在具有控制系統與開放網絡“二重性”的媒介平臺[1]面前,涉世未深的兒童顯然更沒有抵御力。尤其是近5年來,數字媒介已然延伸至兒童的課內閱讀與課外閱讀,基于對兒童的長期觀察以及對家長和教師的訪談,本文將兒童閱讀環境及行為的變化主要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1.數字閱讀任務的增加與課內閱讀結構的變化
班級作業微信群、“班級小管家”、“作業幫”,以及各類服務于幼兒、中小學學生的學習型數字媒介,其最初的功能是促進師生、家校溝通,彌補學生課堂學習的不足,在無法開展線下教學時提供線上教學服務,實現“停課不停學”。這些媒介在長達3年的疫情中發展壯大,開始深度介入教學,從家校交流、傳達通知的輔助方式變成主要方式,通過語音、拍照、視頻上傳打卡,以及提供答案、批閱等方式嵌入學習過程。于是,兒童課內閱讀(本文所指的課內閱讀,是兒童為了完成學業而開展的閱讀,與可以自主開展的課外閱讀相對應)以教材為主、教輔為輔的閱讀格局被瓦解了,形成教材、教輔、數字媒介混合的跨媒介閱讀方式,兒童的數字媒介接觸率和使用技能雖然得到了快速提升,但也加劇了兒童對數字閱讀的依賴。學習型數字媒介內容海量,下載打印便捷,能于無形間迅速膨脹兒童的學習總量,進而擠占線下閱讀的時間。從小學中年級到中學,這種態勢正愈演愈烈。
2.數字“百草園”的擴張與成年人閱讀媒介功能的消解
在家庭朗讀、親子閱讀、教師導讀等行動中,成年人扮演兒童閱讀的媒介角色。相對于成年人讀物,繪本尤其是面向低幼兒童的繪本,是功能“不完整”的讀物,它要以成年人共讀為配件,輔以音、圖、字混合的“多媒體”方式將內涵完整地傳遞給兒童。成年人在共讀繪本時往往充滿肢體、語言和情感的互動交流,從而成為一種意義豐富、愛意飽滿的知識代際傳播過程。如圖1所示,父母、教師等成年人與繪本共同架起了兒童向閱讀世界攀爬的階梯,這是一種以兒童閱讀規律為依據的三方游戲。在這種閱讀游戲中,成年人并不是冷冰冰的教養工具、閱讀中介,而是樂在其中的參與者。筆者在兒童閱讀推廣實踐中發現,青少年時期沒有養成良好閱讀習慣的家長在開展親子閱讀的過程中也能夠重新發現閱讀的樂趣,迎來人生遲來的閱讀發育期,進而可能轉變成一個閱讀愛好者。
數字媒介不需要搭建攀爬的階梯,它是“無縫”[2]的,也是可以讓兒童繞過成年人輕易進入的數字“百草園”,這就是鮑德里亞所批判的由擬像所主導的“超現實”世界。“超現實”世界阻隔了人與現實世界和自我的直接照面[3],如果不打破這種阻隔,我們就沒有辦法獲得完整的生活。只有意識到現實世界和“超現實”世界的不同,才有打破阻隔的欲望,而互聯網世界幼小的“原住民”是否能培養這種數字素養?可見,新的“童年的消逝”不再是簡單的閱讀問題。
3.兒童課外閱讀與數字媒介使用的博弈
數字任務的增加讓兒童處于一種“沒有時間的狀態”,數字“百草園”則讓孩子們放任“時間揮霍”,隨著年齡的增長,孩子們在二者之間往復折返,會喪失越來越多的閱讀時間、動力和能力。通過近幾年的觀察和調研發現,小學低年級的兒童經常以書中故事為談論對象,比如哈利·波特、米小圈、福爾摩斯等。小學高年級尤其是初中階段的兒童越來越多地談論起網上的熱點話題以及《原神》《第五人格》《光·遇》《蛋仔派對》等電子游戲,這些在繁重課業任務之余給兒童帶來強烈娛樂感的社交話題,大大擠壓了兒童的課外閱讀時間。因此,為低年齡段兒童提供的繪本承擔起更為重要的閱讀能力提升、閱讀素養培養與數字素養養成的責任。繪本與數字世界都有著共同的鮮明圖像屬性,繪本出版的數字化轉化似乎也更加容易,它能否在跨媒介閱讀中贏得一席之地,讓兒童在數字世界中依然擁有閱讀的熱情,是一個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二、 繪本的跨媒介內涵及跨媒介閱讀形式
繪本被認為是激發兒童閱讀興趣、培養兒童閱讀習慣的最佳媒介,但是在人類閱讀行為面臨數字化轉型的今天,我們也許不能樂觀地認為,在童年熱愛閱讀繪本的孩童,長大后一定能成為手不釋卷的讀書愛好者。那么,閱讀繪本意義何在呢?筆者曾在相關文章中論述了書籍與“媒介之海”的關系[4],以及重建閱讀自律的意義[5],筆者認為這些思考對兒童閱讀同樣適用——閱讀素養是數字素養的重要基礎,繪本閱讀既代表著書籍文明,亦具有獨特的跨媒介內涵,能在兒童走入數字時代的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1.繪本跨媒介內涵的三重含義
繪本作家和學者安·華福·保羅說過,繪本是給不會閱讀的人看的[6]。這正是由于繪本具有跨媒介閱讀的功能:跨越符號體系、文本版本、童年與成年,建立起內在的連接溝通。
一是跨越符號體系。繪本的每一頁(無字繪本除外)都在引導孩子從直觀、具象的圖畫世界通往加密、線性的文字世界,實現對二者的對照辨識、意義編織,建立對人類文明的兩類主要符號體系的認知。
二是跨越文本版本。大量繪本以人類知名文本為藍本,名著、詩歌、傳說、傳記、百科等原本是兒童難以理解的內容,經過繪本再造,轉譯為便于兒童理解、激發其閱讀興趣的內容和形式,讓文明俯下身軀與兒童相識。
三是跨越童年與成年。雖然成年人都擁有過童年,但往往會被歲月“磨滅”了童心,在哺育教養后代時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學習做家長、做教師。繪本具有喚醒童年記憶、溝通代際認知的媒介功能。對人類社會而言,“童年消逝”的趨勢正在數字海洋中加劇,繪本能提醒成年人認識到兒童這一群體的獨特存在,抵御信息對兒童的“催熟”[7],理解、尊重、保護兒童的童年。
這三種跨越媒介的豐富實踐建構起繪本獨特的語言系統和美學特征,那數字化再造的繪本是否依然擁有這些魅力?這需要對數字化進程中繪本跨媒介閱讀展開分析。
2.繪本跨媒介閱讀的多樣化展開
繪本的讀者群體以0—9歲低齡兒童為主,這個階段的兒童沒有或者只有少量學習任務,對數字產品的使用也相對容易被成年人監管。因此,繪本遭受的數字化沖擊比其他書籍輕一些。相對于文字圖書,繪本與以圖像為主導的屏幕有著更親近的親緣關系,正如松居直所說:“在一本圖畫書(即繪本)中,設計者也可以運用各種藝術語言,讓圖畫書像一部‘紙上電影’,通過圖畫視角的‘推拉搖移’,制造出豐富的效果。”[8]這在由他本人講述、中國繪本畫家蔡皋繪制的著名繪本《桃花源的故事》中得到了完美詮釋,畫面上簡單質樸的語言和一葉小舟共同將兒童引入“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的唯美神秘的古典世界。美國繪本作家莫里斯·桑達克所創作的《野獸國》從首頁開始,版心(畫面)在書頁上所占的比例逐頁加大,四周白邊逐頁縮減,直到版面出血,畫面完全占據書頁,而后白邊又逐頁變大,版心開始縮小——其視覺結構與戲劇、歌劇或電影等視覺藝術由序曲向高潮發展再回落到尾聲的設計有著共同的韻律節奏。這種藝術的互通性,讓繪本具備與文字圖書不同的數字化優勢,繪本的數字化正通過以下方式展開。
(1)衍生多元產品
繪本可以附加多種數字化衍生品。2024年度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青島出版集團出版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少兒繪本大系”在發行紙質圖書的同時,配套推出音頻小程序、互動繪本、動畫繪本、AI閱讀與表達評測、閱讀服務小程序等數字產品近200項[9],手機、平板、顯示屏都能成為繪本的數字延伸終端。當繪本的畫面呈現在屏幕上時,手指點擊滑過,原本靜態的人物、鳥獸、海浪等就會隨之而動,并響起相應的聲音,這是對書卷的創造性增值,為兒童帶來了跨媒介的多樣化體驗。
(2)引入多維體驗
文字作品被改編成影視等圖像作品的過程,往往是需要燃燒大量的時間、物資、智慧的集體再創造過程,這種跨界轉換充滿了“不忠實于原著”或“魔改”的風險。繪本在編輯制作乃至作者創作時就引入了數字繪制技術,方便動畫、音頻、虛擬現實(VR)等多種數字技術的接軌,靜態圖像可以高效實現從二維到三維、從靜態到動態的多方位轉變,為讀者提供多維度的閱讀體驗。
以比利時繪本作家G·V·西納頓的《我不想離開你》為例,其中有一個畫面是袋鼠媽媽和小袋鼠看著一群在平原上奔跑的長頸鹿。在此書的數字版本中,虛擬攝像機將獸群移動、放大,讀者可以更直觀地看到奔跑的長頸鹿對小袋鼠來說是多么的勢不可擋[10],這創造出一種全新的視角和體驗方式,讀者可以更加深入地參與作品,仿佛自己也成了畫面的一部分,與袋鼠母子一同見證這一壯觀的場景。
英國繪本作家畢翠克絲·波特在百年前創作的《彼得兔的故事》,在推出數字繪本版本時配上了嶄新的音樂:當彼得遇到鄰居麥格雷戈先生時,場景中出現了充滿戲劇性的奏樂;當彼得哭泣時,繪本播放輕柔而悲傷的音樂,然后音樂漸漸消失在抽泣聲中。數字繪本的聲音元素能夠強化讀者的沉浸感,使之身臨其境。
(3)實現數字交互
動畫和音頻的加入讓繪本閱讀從二維躍入三維,VR、AR等技術的運用讓繪本具有四維交互的功能,讀者仿佛置身于繪本描繪的世界之中,與角色面對面交流,甚至參與故事發展。在兒童移動電子書提供商iBigToy的動畫APP中,傳統寓言《狼來了》化身為一部互動兒童繪本,讀者翻動的每一頁畫面都能動起來,天空中的小鳥、可愛的小羊等都會隨著手指移動。讀者可以選擇扮演故事中的角色,如放羊娃、村民或狼,通過互動游戲了解角色的特點,推動故事情節發展。
(4)轉變讀者思路
繪本閱讀不同于學習型閱讀,它更符合兒童愛玩的天性,像游戲那樣調動兒童的興趣,為兒童帶來新鮮感和刺激感,讓其在游戲中自己捕捉意義。“繪游結合”是繪本數字化的一個重要方向,能將閱讀與電子游戲機制相結合,通過動態的視覺敘事增強閱讀性,加強閱讀體驗中的互動樂趣。比如,《別讓鴿子開巴士!》這部充滿趣味和幽默的繪本化身為游戲時,兒童就要從不斷猜想下一頁鴿子怎樣才能開上巴士的讀者,轉變為要思考如何拒絕鴿子請求的玩家,無論它撒謊還是威逼利誘,兒童都要完成“別讓鴿子開巴士”的任務[11]。兒童從故事的被動接受者轉變為情節的主動推動者,從而開展了不一樣的思維過程。
以上各種數字化創新拓寬了繪本閱讀的邊界,但也帶來了諸多疑問:數字技術與繪本閱讀的傳統價值如何平衡?如何避免兒童過度依賴屏幕閱讀導致的負面影響?哪些閱讀體驗是必要的,哪些又是數字泡沫?互動繪本會不會是介于繪本與電子游戲之間的雞肋?
三、以繪本之“靈暈”激活數字媒介之“童心”
繪本雖然與數字圖像有著親緣關系,但它的根本優勢不在于畫面多精美、體驗多豐富,而在于它是一個訓練閱讀素養、傳播代際知識的時間裝置:它容納上文所說的“三方游戲”,以閱讀游戲的方式喚醒成年人的童心,從而增進知識代際傳播中的情感交互,使親子閱讀成為養育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信息世界、現實世界分隔,鼓勵讀者從加速社會、繁忙勞動中脫身,在閱讀世界里長久逗留和積極凝思[12]。擁有親子閱讀經驗的人都知道,反復閱讀是兒童獨特的閱讀行為,他們往往連續數日要求家長反復朗讀同一部繪本,幾十遍甚至上百遍,這與網絡的圖像觀看機制不同,后者意味著快速滑動、永遠新鮮和過目即忘。二者就像游戲器材和海洋球,孩子們在玩耍木馬、滑梯、秋千等游戲器材時,會一遍遍反復掌握其技巧、了解其構造。
數字媒介可否也成為這種時間裝置?筆者認為,相對于各類長短視頻、智能問答,單機版的數字兒童游戲或許更具備繼承繪本基因的潛質,它可以容納上文所提及的各種數字技術手段,讓這些技術手段在游戲創造過程中優勝劣汰、有機組合,服務于故事的展開。當然,時間裝置離不開能對兒童閱讀達成共識的網絡環境,要從以下3個方面進行構建。
1.建立低齡兒童閱讀保護區
行業應通過法規研制、家長培育、宣傳普及等方式,為低齡兒童建立一個相對純凈的閱讀保護區。以優秀繪本閱讀為主的紙質閱讀更符合低齡兒童的視力、認知等身心發育規律,減少兒童的觸屏時間,尤其是盡可能地減少兒童對社交媒介和各類數字平臺的接觸,盡量將紙質圖書的閱讀時間拉長到小學三年級以后。其實,家長不用擔心兒童的數字素養會落伍,家長只需在還有能力控制兒童的數字媒介使用時間時,盡可能地打造其強韌的閱讀素養,在兒童終將躍入數字海洋的前夕,讓他們做好基礎的訓練和準備。
2.借鑒繪本創作的“靈暈”
被譽為“虛擬現實之父”的杰倫·拉尼爾認為,計算機科學理想豐富的多樣性并沒有在廣闊世界中獲得應有的關注。所謂多樣性,是指組織數字系統的底層邏輯不應只是信息或財富,更應該是人本身,去創造更能為人所用的人性化系統,對應到本文之中,就是去創造更能為兒童所用的兒童化系統。杰倫·拉尼爾多次在演講中呼吁,技術人員有責任提出那些美麗、有魅力和有深度的媒介技術[13]。兒童媒介技術應該符合兒童的身心發展規律,讓數字任務回歸教育本身,讓數字“百草園”成為真正的百草園。唯有如此,兒童才有可能比數字世界的“移民們”發展出更優越的數字素養,而不會困在“超現實”的童年中。
技術人員無法獨自完成這樣的任務,目前常見的以技術人員和童書作家、出版人團隊組合的方式也是不夠的,新時代需要新的專業人員,就像繪本創作那樣——除漫畫書創作者外,傳統書業少有能勝任圖文一體創作的人才。隨著繪本出版的發展,在過去幾十年中出現了為數甚眾的既能寫又能畫的卓越作家,比如美國繪本《大衛,不可以》的作者大衛·香農、德國繪本《森林里的小房子》的作者尤塔·鮑爾、日本繪本作家伊東寬和中國繪本作家周翔等,他們筆下的文字與圖像并非內容與插圖的主仆或平行關系,而是平等互補、有機一體的關系,繪本成為這兩類符號體系平衡共創的典范。繪本的親子共讀閱讀過程,也是一個聽與看、趣味獲取與知識習得平衡共生的過程。
從這個角度看,繪本是數字工作者及智能系統學習如何為兒童提供服務的優秀范本,以童心出發,融合數字技術、藝術、知識,以及其他各種有益兒童心靈成長的元素,運用多種媒介形式和信息解碼手段創造出新的平衡(如圖2所示)。只有如此,才能為兒童提供有益的多維度閱讀體驗,讓兒童以更開放的閱讀姿態追求生命的靈動,而非感官的刺激、時間的消磨。
3.在兒童跨媒介閱讀的實驗中行動
面對洶涌的數字化浪潮,我們需要的不是倡議書,而是行動方式。兒童閱讀危機的解決不能只靠閱讀推廣以及上文所說的建立閱讀保護區。兒童文學作家尤其是繪本作家應該抱著責任意識和開放的心態,成為在數字世界中營造兒童閱讀裝置的行動者,以數字技術為筆和紙。數字技術工作者也應該潛心理解、尊重兒童文學,讓自身成為數字人文的知音。要讓這種暢想由烏托邦成為現實,需使出版社和高校成為行動開展的平臺。比如:出版社可以通過舉行跨界創作工作坊的方式,廣泛招募對兒童文學有興趣的數字技術人才,與本社編創人員、兒童文學作家進行思想的碰撞啟迪,共同打造兒童閱讀的種子項目;高校的文學、藝術學、數字技術等專業可以開展交叉融合的科學研究和專業設置,為未來培養集技術制作、故事講述和藝術表達能力于一體的數字兒童閱讀創作引領者奠定基礎。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若能出現由曹文軒、梅子涵、朱自強、海飛、劉海棲、殷健靈、黑鶴等在兒童文學領域的卓越人物所監制的兒童數字游戲,使之成為繪本在數字世界的化身,就會在兒童數字閱讀行業信息海洋中建起引航燈塔。
|參考文獻|
[1]蔡潤芳. “圍墻花園”之困:論平臺媒介的“二重性”及其范式演進[J]. 新聞大學,2021(7):76-89.
[2]杰奧夫雷G. 帕克,馬歇爾W. 范·埃爾斯泰恩,桑基特·保羅·邱達利. 平臺革命:改變世界的商業模式[M]. 志鵬,譯. 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
[3]JEAN BAUF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Histories of Cultural Materialism[M]. East Lansing: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4]張文彥. 從“詩稿冊”到“極樂”世界:于書籍邊界探索出版性的可能[J]. 現代出版,2024(5):43-53.
[5]張文彥. 閱讀的靈暈與自律:紙上書、畫中書、鏡中書和人工智能[J]. 出版發行研究,2024(4):10-17.
[6]安·華福·保羅. 如何寫好一個故事:從繪本入手[M]. 王鵬帆,譯. 北京:新星出版社,2016.
[7]尼爾·波茲曼. 童年的消逝[M]. 吳燕莛,譯.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8]松居直. 我的圖畫書論[M]. 季穎,譯. 長沙: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7.
[9]張君成. 青島出版集團“繪本大系”以數字化構建全環境閱讀體驗場景體系: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換一種打開方式[N]. 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2024-08-19.
[10]X LI,AG BUS. Efficacy of digital picture book enhancements grounded in multimedia learning principles: Dependent on age?[J].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2023(6):1-9.
[11]張文儉. 游戲化在兒童繪本閱讀中的價值與應用[J]. 新閱讀,2023(10):53-55.
[12]韓炳哲. 時間的味道[M]. 包向飛,徐基太,譯. 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7.
[13]杰倫·拉尼爾. 虛擬現實:萬象的新開端[M]. 賽迪研究院專家組,譯. 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