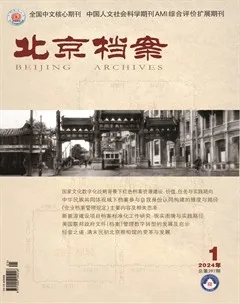居庸關云臺
張幼欣

居庸關云臺(又稱“過街塔”)為元代所建藏傳佛教造型的建筑,至元末時佛塔損毀,明初又在原塔基上修建佛寺。它矗立在群山之間,兩側盡是峰巒疊翠,明人驚嘆其景觀之壯麗,將之列為“居庸八景”之一,因其“遠望如在云端”[1],始有“云臺石閣”之稱。康熙四十一年(1702),因上方佛殿焚毀,僅剩塔基,故俗稱“云臺”。在云臺券門下方石壁上雕刻有四天王、佛像,以及八思巴文、漢文、藏文、回鶻文、梵文、西夏文六種文字的《造塔功德記》和《陀羅尼經咒》。其中,多元藝術元素的交相輝映、各民族文化的碰撞與融合,使得居庸關云臺成為北京地區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
居庸關為“天下九塞”之一,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細數從遼至元的王朝更迭,如金滅遼、金滅北宋、元滅金,居庸關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不僅見證了王朝政權的更迭,更見證了游牧民族向“漢地”進軍、游牧與農耕文明的互相沖擊與滲透。居庸關地處游牧與農耕文明交融帶的文化意義為元廷所重視,元順帝在居庸關建造佛塔,主要出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居庸關云臺的修建直接與元帝在大都與上都間的巡幸活動有關。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出于兼控中原漢地與蒙古的需要,以及對游牧風俗的繼承,實行兩京制(即元上都與元大都),每年巡幸于兩地。據《元史·地理志》記載,元帝兩京巡幸活動開始于中統五年(1264),“中統元年,為開平府。五年,以闕庭所在,加號上都,歲一幸焉”[2],即每年二月至八月(或三月至九月)在上都度過,并固定下來,這種巡幸活動被時人稱為“納缽”,居庸關作為巡幸兩京的必經之路,又有“納缽關”之稱。元至正年間,順帝提議在居庸關修建佛寺和佛塔,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為自己在巡幸兩京的途中建造一個休憩之所。據《析津志》記載,居庸關永明寺修建前,元帝巡幸至居庸關處往往連夜出關,無處休息,因此在居庸關修建永明寺作為落腳之處,居庸關云臺(即過街塔)則是永明寺整體建筑群的一部分。永明寺修建竣工后,元順帝巡幸兩京時常在此駐蹕休息,這里也就逐漸成為巡幸途中的一個固定休息地點。
其次,元代居庸關云臺的修建也受統治者宗教信仰的影響。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前便開始接觸藏傳佛教,元朝建立后,藏傳佛教的勢力在忽必烈的支持下繼續上升。忽必烈對藏傳佛教的支持和崇信,除自身宗教信仰原因外,還是為鞏固自身統治尋找一個精神支柱并借此宣揚其統治的正統地位。[3]此后,元朝歷代皇帝都信仰藏傳佛教。而元順帝在承襲信仰藏傳佛教的同時,也注重發揮藏傳佛教的教化功能,因此,他下令在居庸關建造藏傳佛教造型的佛塔,并在券門下方銘刻多種文字的佛經、佛像,使過往的各族人士經過塔下時如同禮佛,皆能“皈依佛乘,普授法施”。
第三,元代居庸關云臺的修建也與元大都風水格局存在一定關聯。張谷林從風水堪輿文化的角度探討居庸關與元大都建都形勝的關系時認為,以居庸徑北口即現今關溝八達嶺“北門鎖鑰”長城關城門為起點,“經長城居庸兩關城門、再經元大都西北城郭的健德門,至元大都的中心點(鐘鼓樓)為終點,可拉出一條筆直的堪輿‘天門線’”,而元代的居庸關嶺應該是元大都城的第一“天門”,這樣元大都城郭便有12座門,這樣的布局符合《周禮》禮制,[4]可見居庸關在元大都風水格局中占有重要位置。元人歐陽玄在《過街塔銘》中談到當時修建居庸關云臺的其中一個目的便是“令京城風氣完密……由是邦家大寧,宗廟安妥;本枝昌隆,福及億兆,咸利賴焉”[5],建過街塔是為了使“京城風氣完密”,可見云臺的修建也受到漢地風水堪輿文化的影響,這也反映出元朝統治者對傳統中原文化的吸收和應用。
元朝版圖之廣堪稱中國古代歷朝之最,在其統治的廣闊疆域內,各族文化背景不同,有著較大的文化差異。面對如此境況,元朝統治者實施開放的文化政策,國家內部文化類型呈現多元景象,推動了各族群間的文化交流。受此影響,統治者廣納賢才、選賢任能,招攬、吸納各族士人參與國家治理,如任用畏兀兒人、西夏人擔任官職并承擔一定的文字、語言的翻譯工作;在宗教方面倚重吐蕃人,并將藏傳佛教“喇嘛教”定為國教;軍事上任用驍勇善戰的西夏人和女真人,這種對各族精英的吸納與任用彰顯了元代文化的開放與多元并充分體現在居庸關云臺的建造中。
至正二年(1342),元順帝下令修建居庸關過街塔,命右丞相阿魯圖、左丞相別兒怯不花、平章政事鐵不兒達識及御史大夫太平總領建塔事宜。據八思巴文《造塔功德記》記載,御史大夫太平為建造此塔的實際總負責人,[6]阿魯圖、別兒怯不花等似為掛名;在具體施工中,負責官員主要是來自西夏故地的黨項人,如平章政事納麟及主持譯寫西夏文的智妙咩布和顯密二種巧猛沙門領占那征師等,此外,管理相關具體事務的還有藏人南加森;[7]在過街塔券門內各種浮雕紋樣的刻畫上,由僧眾亦恰朵兒、賽罕、金剛吉、普賢吉、八剌室利等人設計樣式并“授匠指畫,督治其工”[8],經謝繼盛考證,云臺券門內出現薩迦傳普明大日曼荼羅圖案應是受帝師喜幢吉祥賢的影響,[9]可見帝師喜幢吉祥賢亦參與或指導過街塔的設計。在過街塔建成之日,元順帝敕令漢人翰林學士歐陽玄撰文記述贊美其事并由學士張起巖篆刻匾額。
在過街塔修建過程中,各族人士廣泛參與其中,雖然限于史料部分族群屬性難以考證,但可以確認的是其中各族人士文化背景各異,如阿魯圖、別兒怯不花(燕只斤氏人)、鐵不兒達識(康里氏人)等承襲的傳統蒙古族草原文化;南里剌麻徒弟亦恰朵兒和南加森等代表的藏傳佛教文化;歐陽玄、張起巖等所代表的漢地傳統的儒家文化;納麟等來自西夏故地的黨項人所承襲的西夏文化等,各民族、地區的文化由此碰撞交融。

在元代開放多元的文化政策背景下,各族文化伴隨著社會流動,在各族人士的交往之中不斷影響、滲透乃至交融,居庸關云臺券門內的銘文與浮雕藝術造型也融合了當時蒙古、中原、西域等地各民族的文化元素。
文字是文化傳承的載體,居庸關云臺券門內東西兩面墻壁的銘文所記載的內容是蒙古族佛教儀軌文中的贊頌詩和祈愿詩聯壁的姊妹篇,其中有歌頌元帝信仰藏傳佛教、修建佛寺之舉功德無量,蔭及子孫萬世的,還有借“天意”論證元代統治的正統性和合法性,[10]由漢文、八思巴文、梵文、西夏文、藏文、回鶻六種文字銘刻《造塔功德記》和《陀羅尼經咒》,反映了元代各民族文化在北京地區交流交融的盛況。
元代文化政策的開放性,使得“此一時期的多民族物質文明更顯生機,其中融合了多民族文明元素的元代藝術具有強烈的氣勢與爆發力”[11],居庸關云臺券門之下精美的浮雕便是多民族文化元素融合的體現。居庸關云臺券門內的浮雕,按照所處位置及表現內容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部分:券門內頂的“五曼荼羅”,南北券門的“六拏具”,門內東西斜頂的“十方佛”和東西內壁的“四大天王”像。這四部分內容無論從內容題材還是藝術風格來看皆是藏傳佛教雕塑藝術,但也具有明顯的漢地文化色彩,如四大天王之一的東方持國天王,其形象特征據《般若守護十六善神王形體》記載,本是紫發,身著紅色甲青,膚色為青色,面帶憤怒之相,左手伸臂下垂持大刀,右手屈臂向前托一寶珠。由于受《封神演義》的影響,內地大多佛教寺廟中的東方持國天王被塑為手持琵琶的中國武將形象,居庸關云臺券門內的持國天王像則符合內地佛教寺廟的特征。在審美特征上,居庸云臺的佛像融入了許多漢地造像的特點,如券門“六拏具”中的龍子和騎瑞獸的童子與四大天王形象,已然具備了漢式造像面容飽滿的典型特征;另外在人物服飾、衣紋的刻畫上也更加注重立體感和穿插關系的表達,增強了線條的表現力,可見尼泊爾式、印度帕拉式注重簡潔的衣紋處理手法在漢地文化的影響下得到改良,漢地文化的色彩更加濃厚了。[12]
在元代多元共生的文化政策影響下,各族文化交流愈漸深入。在居庸關云臺修建過程中,文化背景不同的各族精英人士共同參與,各族文化交相輝映。云臺券門內多種語言文字書寫的佛教經文、多種文化元素共融的浮雕藝術作品,不僅是元代多元共生文化政策的結果,也是元代各族人士心血的結晶,更是北京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項目,《元、明“大一統”秩序變遷中的居庸關云臺佛寺》(項目號:BZKY2023038)研究成果。
注釋及參考文獻:
[1]周碩勛.延慶衛志略[M].中國方志叢書.塞北地方第32號.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49.
[2]宋濂.元史[M].北京:中華書局,1976:1350, 3374.
[3]陳高華,張帆,劉曉.元代文化史[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149.
[4]張谷林.論中華魂與根文化(第二卷)[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8:251.
[5][8]熊夢祥.析津志輯佚[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253,253.
[6]宿白.居庸關過街塔考稿[J].文物,1964(4): 18.
[7][9]謝繼勝.居庸關過街塔造像義蘊考——11至14世紀中國佛教藝術圖像配置的重構[J].故宮博物院院刊,2014(5):51,63.
[10]雙福.《居庸關東西壁銘文》研究[J].內蒙古社會科學,1992(2):117-118.
[11]謝繼勝.從多民族共創佛教藝術看中華民族文明史的建構[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10-26(A03).
[12]關于元代藏傳佛教雕塑藝術特色的研究,請參考2014年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學專業陳健的博士學位論文,第38-43頁。
作者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