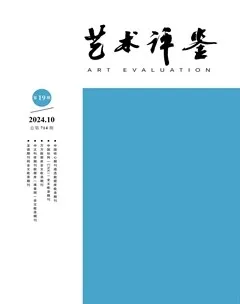老子審美境界中美與生命的統一
【摘 要】老子認為“道”是天地萬物的本體,也是美的本體。“道”之大美既是超越現象界的,又蘊含于現象萬物之中。對大美的觀照要通過懸擱“知”與“欲”的修道功夫復歸同于“道”的自然的、審美的人生境界,將人的在世生活融入“道”長養萬物的大化流行中。在這種審美人生境界中,美的本源、審美方法、審美體驗與人的生命渾然一體,自我存在的自然敞現和審美的生命體驗創造就是“道”之生化作用的展開和大美生成之源泉。
【關鍵詞】道" 老子" 審美境界" 生命
中圖分類號:J0-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24)19-0177-06
老子的美學是建立在他邏輯嚴密、結構完整的哲學體系之上的。道是老子哲學的中心范疇和最高范疇。道是有無相生的宇宙本體。“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道”是“有”與“無”的統一,是天地萬物之所從來、存在依據和天地萬物的整體和大全。在“道”的層面上,天地同根,萬物一體。無形無質之道分化而為“德”落向有形有質的萬物,“德”內在于萬物中,成為物之為物的根源。蒙培元提到:“‘德’雖然來源于‘道’,但不再是自然宇宙論的范疇,而是一個主體的實現原則,變成了人生修養問題,變成了境界問題。”老子之“道論”哲學之于人的意義就在于作為本源與本體的“道”能夠落實于個體生命之“德”,并提供一個突破個體局限向著“道”之永恒性和無限性的超越之途,這成為老子美學的思想基礎。
這一通過向“道”的復歸所達致的理想的人生境界實則就是一種懸擱了認識價值和功利價值的自由的審美境界。因此老子思想中審美問題實則是一個人的生存方式問題,向審美的人生境界的超越實則是老子哲學和美學的旨歸。在老子的理想中,“美”便不僅僅是個體生命活動歷程中轉瞬即逝的煙花,而是從“道”中敞現的照徹人之生命存在的永恒之光,因此《老子》中直接討論美的詞句雖不多,卻具有不可輕視的重要意義。
一、美在超越現象之境界
老子并未像莊子那般直言美,而是從美的對立面出發,以一種否定的方式切近美,最終通過對否定之否定揭示了真正的美是“道”之“大美”。“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美”這一概念的誕生便是“惡”與“丑”之概念的發源,分別之知是不美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注入智巧使話顯得動聽卻掩蓋了話語的真意,功于機巧是不美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求勝與殺人不能成為戰爭的目的,樂于爭抗是不美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音五色愉悅人的感官使人沉溺于感官享受無法自拔,耽于物欲是不美的。探其究竟,分別、機巧歸于向外求取的分別之“知”、爭抗、感官悅樂歸于昏蒙內心的妄想之“欲”。知識和欲望是老子認為的“美”之大敵。
老子之所以批判“知”和“欲”,是因為它們生出的分別對待之心是對人本真“玄德”的背反和對“道”的遮蔽。受到對待之心驅使,人愈發困頓于世俗層面的美與丑的對立,迷失于對世俗之假美的執著追求。徐復觀認為,人由“大道”之“德”而生,雖本根于“道”,但因為人在現象層面上有一定的形質,與沖虛的“道”必然有一定的距離。人心有“知”的作用,人的感官有“欲”的要求,“知”和“欲”易使人喪失,“道”在從無限性、恍惚性落實到現象萬物有限性之存在時,所賦予現象萬物的直通于道的虛無整一之“玄德”,是形制對德的背反。雖然在存在的根源處天地萬物本是“道”之一體,但在人試圖建立對世界的認識時,萬物直觀的形制和人在世界中的中心位置成了人構建知識的抓手。美丑、高下、長短等二元對立的認識是人從自身的主觀視角出發,經由現象界個體事物之間的對比產生的。正所謂“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人人皆知追求鮮艷華麗的顏色,皆欲欣賞悅耳動聽的音樂,卻忘記了雙目所見無不是顏色,雙耳所聽無不是聲音。世俗眼光中美的對象刺激人的感官,喚起愉悅的感受,與世俗眼光中丑的對象喚起人痛苦的感受在本質上并無差別,都是寶貴的生命體驗。但常人卻樂于將原本齊一的萬物劃分三六九等,并為自己的廣博知識沾沾自喜。經驗知識的逐漸積累使知識之網中相互分離的現象界個體將“道”的整體性存在形式遮蔽起來,使人只知“道”之“有”而不知“道”之“無”。當人試圖在單個的、分別的對象中尋找美和喜悅時就站到了現象界中具體對象的對面,將具體對象及人自身從“道”的本源中剝離出來,令萬物與人相互獨立存在,已經全然不見物我合一之“道”。
既然遮蔽了“道”的知識與欲望所確立的世俗之美是老子極力抨擊的對象,那么拂去知識和欲望帶來的“道”的敞現便是真正的美。憨山在對《道德經》的注釋中寫道:“謂世間眾美之名自外來者,皆是假名無實,故其名易去。惟此道體有實有名,故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閱,猶經歷。甫,美也。謂眾美皆具。”現象界中之萬物難免隨大道生化流行的節律生滅變化,因此現象事物的“美”終是“假名”。唯有大道不生不滅,是天地萬物的本體,也是美的本體。
一方面,“道”之大美超越現象,另一方面,現象界具體對象是“道”之大美向人敞現的窗口。“道”之大美存在于“有”與“無”的相互生成中。老子以“大音”與“大象”為中介說明超越現象之美與現象界具體對象的關系。“大”是道的性質,大音與大象實際上指的是“道之音”“道之象”。如同“道”是萬物的本體,萬物不離“道”外,大音、大象是現象界聲音和形象的本體,具有一切聲音和形象的性質,但不是任何一種具體的聲音和形象,同時也不存在大音、大象之外的聲音和形象。它們是圓具的“一”,所以在其中美與丑的對立消解了,既然其中不再存在丑的可能,大音與大象便是絕待的純美,也就是一種“無美”。憨山提出:“意謂全虛無之道體,既全成了有名之萬物,是則物物皆道之全體所在,正謂一物一太極。”“無”生出了“有”,“有”是“無”存在的明證,是“無”生化作用的顯現。同樣,人的感官所能捕捉的萬物之聲音和形象都是大音與大象落實在現象界的產物,是人在至實之中窺探至虛,在萬有背后體會萬無,在現象之中感悟大美的窗口。“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并作,吾以觀復”便彰顯了徜徉于現象萬物中的對大美的審美活動。
然而,現象界的聲音、形象能否在人的生命世界中呈現為大美取決于人的境界。馮友蘭指出:“人對于宇宙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底覺解,因此,宇宙人生對于人所有底某種不同底意義,即構成人所有底某種境界。”當人與現象萬物照面之時,萬物不會主動向人敞現大美,也不會主動遮蔽大美,它們在人生命世界中究竟呈現為虛名之美的載體還是大美敞現的窗口實則由人對“道”的不同覺解,即由人的境界決定。同樣面對萬物,出于“知”和“欲”的對待之心則“令人目盲”“令人耳聾”,出于“致虛”“守靜”的“玄德”之心,則可以“觀其復”。無怪乎老子既痛斥“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余”為“非道”,又以“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為同于“道”的“治之極”。這兩處看似矛盾的論斷恰恰點明大美審美的境界性。在追名逐利的世俗境界中,所謂美的事物刺激人向外求取,是對生命的損害,而在超越對立的同“道”境界中,萬物都能增添生命的情趣,是對生命的滋養。因此,老子并非完全不贊同感官性審美,也并非完全不承認現象對象的審美價值。在同于“道”的人生境界中,因為對大美的審美是超越現象界的,感官感受的懸擱是大美綻現的結果而非前提,要求人完全屏蔽感官活動,拒斥一切現象對象,只在一種現象世界的空無中追尋大美,這是對大美之美感產生過程的因果顛倒,無異于否認“有”在“道”之中的存在價值,否認“萬象”在“大象”中的存在價值。事實上,現象世界作為“有”同樣是“道”的一部分,同樣是大美棲身的居所。在人與萬物復歸唯一的虛靜境界中,包括人自身的萬物都是“道”的大音、大象的顯現,人的一切實踐活動中的目之所及、耳之所聞、身之所感都是大美周流萬匯,也只有在這一虛靜的、超越的“道”的境界中,大美才能敞現。
二、審美在自然靜觀之功夫
老子點破基于“知”和“欲”的現象界個體事物之美的虛名,既指出人易迷失于現象的局限性,又給出超越這一局限性達致審美的理想人生境界的方法。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道”的一個基本特性,即自然而然,是其所是。“道”的自然法則是一種純然的,沒有對立的自由無礙。“道”的自然特性落實于個體人生,人若能順其自然而不強作妄為正是“玄德”的顯現,是“道”賦予人的生命本真狀態,是“道”的境界,也就是大美的境界。超越充斥著“知”與“欲”的庸常俗心,回歸這一本真自然的“道”的境界是老子的審美方法論。
老子強調,從嬰兒啼哭的現象中指出人之天性本然與“道”相貫通。在人的原初狀態下,人與天地萬物是合一的,并無你我、主客的對立,在無意識中合乎道的自然法則。嬰兒能夠“終日號而不嗄”,是由于“和之至也”。蘇轍則據此直接指出“道”在這一現象中的顯現:“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嘎。終日號而不嘎,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嬰兒的狀態便是“道”在人的生命中完全呈現的自然狀態。嬰兒在未受到社會規訓的時候不因外物動其心,能夠在現象萬物中窺見“道”的本質,令“玄德”呈現以應對萬物,所以能夠哭號不止而不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損害。因此人生命的根本和初始之處本然是一種自由無礙的圓滿狀態,是一種大美充盈的純美狀態。
自然雖為人的本性,但人卻因為有心知偏見、易于強求妄作而極易失其本性。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從他人處學到的知識、在生活中總結的經驗因其在所難免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將人的視角收窄,使人“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乃至對人的生命產生損害。《莊子》中一則寓言揭示了這個道理。中央之帝渾沌無七竅便無視聽食息之欲,然儵與忽每日為其鑿一竅,七日后渾沌死,可見“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但人既然已有七竅,不可能重回初始的渾沌狀態。對于陷于世俗的泥淖中人來說,其“自然”的行動實際已經被種種欲念裹挾,反倒成了不自然。
怎么才能回歸自然狀態呢?莊子順應老子的思想,對人后天的自然狀態做了說明:“古之曰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常而自然。”馮友蘭在《新原道》中提出對這種自然狀態的精到見解。他認為人生有四種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中,自然境界與天地境界看似都是混沌,實則全然不同。在自然境界中,人不知對事物做分別,是一種無知。而在天地境界中,人有知但主動去知,忘卻了事物的分別。老莊理想中的后天的自然境界實質是馮友蘭先生所說的天地境界。在這種天地境界中,人自由地、敞開地包容一切,不再以我觀物,而是以物觀物、以“道”觀物,因而能順時應勢地言行,從而使一切事物乃至自身是其所是、恰如其分。
李澤厚深化了馮友蘭的這一觀點:“馮(友蘭)沒指出這‘天地境界’實際是一種對人生的審美境界。”自然既是“道”的性質和人的本性,也是復歸于“道”、體悟大美的途徑。要使“道”的大美重新澄澈地綻現在生命中,并不是要人回到混沌狀態,而是要從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實現超越達致天地境界。賈永平從“道”之大美的性質出發指出大美的審美方法:“在老子看來,道所表現出來的美不同于一般感官型審美的耳目視聽之樂,而是一種內在的、暫時舍去了耳目視聽的具有超驗性意義的大美,對于這種大美,我們無法通過外在的感官或者認知的手段來獲得,而只能靠直觀、靜照,靠內心的體悟來獲得。”大美是“道”之美,而“道”并不外在于人,因此體悟大美本質上是通過內省返照來解放自身的純粹、自然、圓具的本性。憨山指出“人人皆具此道,但日用不知,須待教而后能”。盡管自然是“道”賦予人的本性,但人仍需下修道的功夫來體認、發顯“道”之常德。
修道的過程便是一個復現生命之美的過程,也就是一種重新習得審美能力的過程。宗白華認為“美感的養成在于能空”“更重要的是心靈內部方面的空”。“空”正是同于“道”的審美人生境界的特征,是道家提倡的生命狀態。“為學日益,為道日損。”做學問的人,需不斷積累知識,但修道的人卻需要令智,故一天比一天減少。老子提出“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認為人的仁義巧智皆是紋飾,推崇仁義巧智使人逐于外物,忘卻樸素混全之道,并非自然。修道之人應當去華取實。待人破除了對外物的執著和欲求,做到了“忘物”,還需破除對己見的執念,即“忘我”。更重要的是,老子提醒道:“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對無名之“道”的向往仍然是一種欲求,對“道”的欲求則又將“道”置于“我”之外,“我”與“道”仍然是對立狀態,因此即便是對“道”的認知和向往亦須清除。拋去一切執著欲念后的空無虛靜的生命為“道”的敞現打開空間。在這種超越了世俗習性的境界中,人真正能夠做到無為,即不妄為,能夠突破狹隘的個人意志局限,使事物按照合乎各自所是的方式自行發展、自行成就。如此一方面不會施加外力干涉外物發展,另一方面也不會有意造作,矯控自己的表現,真正使萬物與自身都處于“道”的自然情態,從而達到一種無思無慮、沒有機巧之心的天地境界。順其自然,如其所是正是人本有的審美能力,只有回歸生命自然本真的狀態才能體驗到超越耳目視聽的超驗性的大美。
美學是感性學,在老子提出同于道的人生境界中,人的感性真正得到解放,此境界中的人生正是一種審美的人生。回歸到“道”的境界中,因為懸擱了知識和欲望的目的性和功利性,人的感官感受便不會被扭曲,能夠為感覺而感覺,所見所感的便不是知或不知、欲或不欲、美或不美之物,而是物之所是,也就是隱藏在現象背后的大象,氤氳于大象之中的大美和并包眾美的“大道”。此處,對萬物的感覺便不是停留于感官中,而是藉由這“大道”直貫人的本真生命的存在。
三、價值在自我生成之生命
老子美學的本質是通過向“道”的超越與回歸,將現實人生融入大道流行,實現生命活動與審美活動的統一。
老子提出修道者應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知無欲無為的“道”的境界,過一種無思無慮的虛靜生活。這一理念并非倡導將人慣常理解的一切活潑的生活活動都剝除棄置,通過削減感官活動而屏蔽現象界,否定人的形而下的現實生活而僅提倡沉浸于形而上的精神生活。老子將“道”與現實人生相貫通反而是希望人能過一種“生”的生活,是令人的存在真正地敞現,令個體生命自由地發展,過時刻新奇、時刻自由、時刻創造的審美生活。在“道”的境界中令大美呈現的意義和價值不僅超越悅耳悅目,從而實現悅神悅志,更在于這一審美的人生境界使人的一切所知、所做、所感都籠罩于大美的光輝中,使人在大美的審美觀照和審美創造中展開自己的生命。
“道”雖是一種現成的存在,但具有生成性。彭富春認為:“無自身不是死之無,而是生之無,這樣它才是道的本性。”“道”的“無”并非純粹的虛無,而是一種生成的力量,是萬物之始,也是萬物之終。“道”之“無”在顯現的過程中,與萬物以及作為萬物之一的無相區分,它的顯現正是對萬物的否定,同時也在自身中遮蔽自己。這種“道”的顯現并不是外在的、分離的,而是內在的、密切的,“道”與天地萬物同為一體。有與無的生成和轉化就是所謂的“生生不息”。
人與“道”的一體不二意味著人的本性層面上也具有這種“生”之德,同于“道”的審美人生境界,因此也是一種蘊含著生成性的境界。誠如陳鼓應所言:“‘虛靜’的生活,蘊含著心靈保持凝聚含藏的狀態。唯有這種心靈才能培養出高遠的心志與真樸的氣質,也唯有這種心靈,才能導引出深厚的創造力量。”在“道”的境界中,人能自由地創造和生成自己。在常人的生活中有著各種需要遵守的規則和規范,被欲望和意志裹挾而不自由,被沖突和對立擾動而生痛苦。但在這種超越的境界中,人安住在虛靜的心性本體上“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與“道”合一因而能夠實現本性的自然流露。此時人不是被個人的習慣所迫使也不是被異化了的社會規訓所蒙蔽而亦步亦趨地仿照仁義道德的范本而生活,而是能解放“道”先天賦予的創造的自由,隨心所欲地游戲于天地間,在至樂中向著未來展開自己的生命。
人在“大道”流行中展開自己的生活,反過來,人在生活中與萬物的交叉生成也一起編織成了“大道”的造化不息。人若能復現其赤子之心,則“蜂蠆虺蛇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在“道”的境界中,人與萬物并無物我主客之分,一切現實生活中人與萬物的交互變成在“道”孕育一切的大搖籃之中手與足的嬉戲,因此蛇蝎猛獸亦與人無妨無害。在“大道”流行之處,萬物不是被作為主體的人凝視和控制的客體,而是與人推杯送盞共享生命之宴的賓客。人生命的展開,人生命世界中萬物的顯現和人與萬物的交互既是出自“道”的造化作用,也是“道”實現自身的過程,人與萬物主體間性的活動正是“道”生化之作用的顯現。
在“道”的天地境界中,過一種大美的生活是老子為人生現實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顯示出老子對人生命的關懷。老子以內在于人的“道”的境界啟發人以“道”為依據確證個體生命的存在之無理由的必然價值,將人投射向外的目光反射向內照徹自我、在洞見萬物存在的本質中體悟自身生命存在的至美極樂。王建疆認為:“在道的德能運行和人的修養過程中,道德境界從形而上玄想進入了具有審美意蘊的深層心理感受,屬于第一類脫離了外在感性對象和外在感官的精神性內審美境界,實現了人生境界與審美境界之間的轉換。”此處“道德境界”對應的是馮友蘭先生提出的“天地境界”。老子將人生命的意義錨定到了將平凡的生活轉化為超驗的審美體驗,從中超越自己、創造自己,生成自己,并在生命的生成性活動中成全和成就萬物存在,以當下為奇點自由地奔向無限可能的未來,融入“道”之大化流行而與萬物同游。在這種審美的天地境界中,美的本源、審美方法、審美體驗與人的生命渾然一體,因此大美并不需要外求而自然自發地人的生命中迸發噴涌而出。老子雖以“道”為本源,最終卻將自我存在的自然敞現這一最根本、穩定、無可辯駁的基點證成了個體生命的安身立命之所。向“道”的境界的超越在引領人向外追逐的現象界生活之后又使人熱情地、堅定地復歸于基于現象的向內的、自由的、澄澈的生活,使人的整個生命體驗變成一種掌握在自我手中的創造美和體驗美融在一起的大美體驗。這便是無形無名的“道”對于現實人生的意義。
四、結語
葉朗認為:“在當今世界存在的眾多問題中,有三個問題十分突出,一個是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失衡,一個是人的內心生活的失衡,一個是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老子以“道”為燈塔呼喚迷航人生復歸的途徑在當今時代仍然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在向大美的天地境界超越的過程中,人通過懸擱經驗知識所帶來的現象上的價值判斷,消解“汲汲于富貴、戚戚于貧賤”的潛在動力,破除倫常道德劃定的強制的、外在的矯飾人之天真性情的話語框架,從而專注于本真生命的自然發展。同時,道家以“道”作為世間天地萬物和人共同的本體和法則,而為萬物與人確立了齊一的地位,將人自由發展的需要與萬物自由發展的需要之間的緊張關系化解于人生命價值的內在轉向過程中。萬物從人的價值體系之網中解脫出來,不會再作為人的附庸被評判、掠奪和囤積,而能作為具有與人同樣具有存在意義的個體獲得其各自生命本真存在的敞現。通過“道”對人之個體生命存在價值的確證和對萬物的復魅,人與萬物能夠共同在主體間的交互性活動中自然無爭地創造、生成自己,在“天、地、神、人四方游戲”中融入自然的生命循環洪流而各得其所,共美共生。
參考文獻:
[1]蒙培元.“道”的境界:老子哲學的深層意蘊[J].中國社會科學,1996(01):115-124.
[2]憨山,著.梅愚,點校.老子道德經解[M].武漢:崇文書局,2015.
[3]馮友蘭.新原人[M].北京:三聯書店,2007.
[4]蘇轍,著.黃曙輝,點校.道德真經注[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5]馮友蘭.新原道:種中國哲學之精神[M].北京:三聯書店,2007.
[6]李澤厚.華夏美學[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7]賈永平.論《道德經》中大美的生成及其內涵[J].甘肅社會科學,2016(01):183-186.
[8]宗白華.宗白華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9]彭富春.論老子的道[J].湖北社會科學,2011(08):112-118.
[10]陳鼓應.老子今注今譯[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11]王建疆.老莊人生境界的審美生成[D].上海:復旦大學,2004年.
[12]葉朗.胸中之竹—走向現代之中國美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