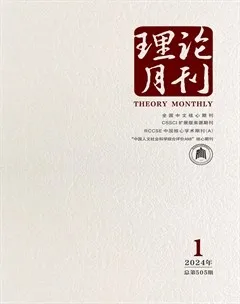建構(gòu)“紅色中國”:海外親歷者的中共革命史書寫
張德明
[摘 要] 改革開放以來,國內(nèi)翻譯出版了一批海外親歷者所寫的中共革命史著作。這些著作觀察細致、視角新穎,既有宏觀論述,又有微觀考證,注重運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及變化發(fā)展的眼光考察相關(guān)問題,對1921—1949年間中國共產(chǎn)黨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文化等領(lǐng)域的作為都有論述,從他者角度構(gòu)建了豐富的“紅色中國”面相,具有重要學術(shù)價值。
[關(guān)鍵詞] 海外;中國共產(chǎn)黨;革命史;譯著
[DOI編號] 10.14180/j.cnki.1004-0544.2024.01.003
[中圖分類號] D25? ? ? ? ? ? ? ? ? ?[文獻標識碼] A? ? ? ? ? [文章編號] 1004-0544(2024)01-0021-10
1921—1949年,曾有許多來華海外人士親歷了中共革命,并寫作出版了大量詳細記述革命史細節(jié)的著作,其中不少著作已譯介到國內(nèi)。學界對海外親歷者視野中的中共革命史已有一定關(guān)注①,但對他們的相關(guān)著作卻缺乏綜合研究。本文以改革開放以來在國內(nèi)翻譯出版的海外親歷者的中共革命史著作為研究對象,力圖闡釋其觀察中共革命史的視角,分析其黨史書寫的內(nèi)容及特點,總結(jié)其在構(gòu)建“紅色中國”過程中的貢獻。
一、海外親歷者書寫的中共革命史著作譯介概況
1921—1949年,不少來華的記者、外交官、軍事顧問等曾與中國共產(chǎn)黨人有過密切接觸,他們未輕信國民黨或日軍的反共宣傳,注重開展實地考察,并依據(jù)在中共根據(jù)地的參觀、采訪資料寫成了一批紀實性著作。這些著作敘述了大量中共黨史的細節(jié),其中不少已被陸續(xù)譯介到國內(nèi)。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一批蘇聯(lián)軍事顧問參與了北伐戰(zhàn)爭并寫有回憶錄。如切列潘諾夫的《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布柳赫爾的《黃埔軍校首席顧問布柳赫爾元帥》(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勃拉戈達托夫的《中國革命紀事(1925—1927)》①(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2年)等書,都對第一次國共合作及北伐戰(zhàn)爭有所敘述,但由于當時共產(chǎn)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了國民黨,對中共活動的描述相對較少。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薄復禮、斯諾、貝特蘭等來華海外人士親歷了長征及中共在西北革命根據(jù)地的活動,這些事件在他們的著作中也有諸多記載。瑞士人薄復禮的《一個外國傳教士眼中的長征》(昆侖出版社,2006年)記錄了紅軍的長征(該書也有史實性錯誤,需要讀者辨析利用)。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名著《西行漫記》②(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依據(jù)其1936年6—10月前往西北革命根據(jù)地實地采訪的見聞,向世界介紹了中共領(lǐng)袖及工農(nóng)紅軍的情況。斯諾等著《前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6年)為1937年秘密出版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的再版,主體內(nèi)容為斯諾同毛澤東的談話及其對陜甘寧邊區(qū)的報道,部分內(nèi)容與后來出版的《西行漫記》相同,另收錄史沫特萊同毛澤東的談話記錄、美國人韓蔚爾有關(guān)四川紅軍的三篇報道等。新西蘭記者貝特蘭的《中國的新生》③(新華出版社,1986年),記述了1936年作者親歷的西安事變以及1937年初訪問徐海東所率紅軍的經(jīng)歷。美國人畢森的《抗日戰(zhàn)爭前夜的延安之行》④(東北工學院出版社,1990年),介紹了其1937年6月期間在延安訪問的情況。
抗日戰(zhàn)爭時期,諸多來華海外人士曾到延安及八路軍、新四軍根據(jù)地采訪,他們寫有大量記述中國共產(chǎn)黨抗戰(zhàn)的文字,其中美國記者最為活躍。斯諾及其夫人、史沫特萊、斯特朗在全面抗戰(zhàn)期間曾寫有大量描述中共抗戰(zhàn)的作品,其中不少作品在西方流傳甚廣。斯諾的《為亞洲而戰(zhàn)》(新華出版社,1984年),記述了他1939年重訪延安解放區(qū)的見聞;《紅色中國雜記 1936—1945》⑤(群眾出版社,1983年),介紹了毛澤東、周恩來、博古、蕭勁光、林彪、陳賡等人物,土地革命等革命活動,以及共青團等革命組織。斯諾夫人海倫·斯諾(其筆名為尼姆·韋爾斯)也曾出版多部有關(guān)中共的著作,如《紅都延安秘錄:西行訪問記》(中國青年出版社,1994年),專章介紹了朱德、徐向前、蕭克、賀龍、羅炳輝、項英、蔡樹蕃、董必武、王震等人物;《紅都延安采訪實錄》(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 年)則是她1937年春赴延安采訪各界知名人士(包括廖承志、董必武、徐特立、賀龍、王震、林彪、蕭克等20余人)的記錄;《延安采訪錄》⑥(貴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記述了斯諾夫人1937年延安之行的具體經(jīng)過(在歷時4個多月的實地考察中,她采訪了埃德加·斯諾未能訪問的中共領(lǐng)導人和一些紅軍指戰(zhàn)員,廣泛接觸了邊區(qū)的各個社會群體),并收錄了20多封她與斯諾的書簡通信;《續(xù)西行漫記》⑦(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1年)同樣記錄了其1937年的延安之行,但較前書增加了婦女與革命、蘇維埃走向民主及中日戰(zhàn)爭三部分內(nèi)容;《一個女記者的傳奇》①(新華出版社,1986年)專章記述了其在延安的活動及見聞。史沫特萊的《中國的戰(zhàn)歌》②(作家出版社,1986年)記錄了作者1937—1941年在中國的經(jīng)歷,其中有對華中的新四軍以及在延安、華北的八路軍的描寫;《中國在反擊:一個美國女人和八路軍在一起》③(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則以日記形式記載了她于1937年8月19日從延安出發(fā)至1938年1月9日到達漢口的全過程,其中有大量對八路軍的描寫。斯特朗的《人類的五分之一》(新華出版社,1988年)為作者采訪中國抗戰(zhàn)的紀實,有專門章節(jié)講述其在山西同八路軍在一起時的所見所聞。1944年,作為中外記者團成員訪問延安的美國人福爾曼著有《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④(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一書,記錄了其在延安、晉綏根據(jù)地等地訪問的見聞,反映了根據(jù)地軍事、經(jīng)濟、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情況,在國外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
除了上述著名記者外,還有一些美國記者也來華報道了中共抗戰(zhàn)。霍爾多·漢森的《中國抗戰(zhàn)紀事》(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7年)記錄了他1938年深入晉察冀邊區(qū)和延安,并在延安采訪多位中共領(lǐng)導人的情況。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從北平到延安:1938年美聯(lián)社記者鏡頭下的中國》則主要通過照片呈現(xiàn)了漢森視野中的中共抗戰(zhàn),同時配有漢森日記中有關(guān)其在晉察冀邊區(qū)及延安活動的珍貴記載。喬伊·荷馬的《在中國看見曙光》(北京出版社,2016年)對中共的抗戰(zhàn)有詳細介紹,并記載了其1939年赴延安采訪毛澤東和其他中共領(lǐng)導人的經(jīng)歷。白修德、賈安娜所著《中國的驚雷》⑤(新華出版社,1988年)的第十三章專門介紹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十五章介紹了延安的政治情況。白修德的《中國抗戰(zhàn)秘聞:白修德回憶錄》(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的第五章介紹了其1944年訪問延安的見聞。上述著作肯定了中共抗戰(zhàn),向世界傳播了積極正面的中國共產(chǎn)黨形象。
抗戰(zhàn)時期頻繁來華的美國軍官、外交官也寫有大量記述中共抗戰(zhàn)的著作。美國軍官卡爾遜的《中國的雙星》(新華出版社,1987年)及《太陽正在升起——卡爾遜親歷的中國抗戰(zhàn)》(北京出版社,2016年)展現(xiàn)了其親歷的中共敵后抗戰(zhàn)實況,后者還收錄了作者關(guān)于八路軍、新四軍活動的報告。1944年,美軍觀察組分批訪問延安,他們寫下了大量作品,如高林的《延安精神——戰(zhàn)時中美友好篇章》(華藝出版社,1992年)、戴維斯的《抓住龍尾——戴維斯在華回憶錄》(商務印書館,1996年)、包瑞德的《美軍觀察組在延安》(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彼得金的《深入中國1943—1945: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見聞》(北京出版社,2019年),都記錄了他們在延安的所見、所聞、所感及其與中共領(lǐng)導人的交往情況。西奧多·H.懷特在《巨人的對峙(抗日戰(zhàn)爭回憶錄)》(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中記錄了其在延安的見聞。埃謝里克編著的《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的報告》(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89年)的第二部分根據(jù)美國外交官謝偉思1944年訪問延安的經(jīng)歷,專門介紹了邊區(qū)生活和中共對國民黨及美國的政策等內(nèi)容。
抗戰(zhàn)時期還有一些加拿大人士來華參與抗戰(zhàn)。瓊·尤恩的《在中國當護士的年月(1933—1939)》①(時事出版社,1984年)記錄了中共在根據(jù)地的生存實況,包括毛澤東、八路軍的近景特寫以及白求恩在根據(jù)地的救護事跡。于維國等編譯的《諾爾曼·白求恩文選》(金盾出版社,2015年)收錄了白求恩發(fā)表的一些記錄八路軍抗戰(zhàn)的日記、書信與文章。
來華歐洲及大洋洲人士介紹抗戰(zhàn)的作品相對較少,多記錄了中共在華北的活動。英國記者斯坦因曾于1944年到訪延安,他的《紅色中國的挑戰(zhàn)》②(新華出版社,1987年)記敘了延安社會的方方面面,較為全面、客觀地分析了中國共產(chǎn)黨在抗戰(zhàn)中的作用。英國教師班威廉、克蘭爾的《新西行漫記》(新華出版社,1988年)則是1943年兩人在延安和晉察冀抗日根據(jù)地的生活記錄,描繪了根據(jù)地政治、經(jīng)濟及文化活動的許多細節(jié)。英國教師林邁可的《八路軍抗日根據(jù)地見聞錄——一個英國人不平凡經(jīng)歷的記述》③(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記錄了身為燕京大學教師的作者在冀中、晉察冀抗日根據(jù)地的經(jīng)歷及見聞。德國記者希伯的《希伯文集》(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收錄了他報道新四軍、八路軍的文章。德國人王安娜的《中國:我的第二故鄉(xiāng)》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80年)記錄了延安及華北抗日根據(jù)地的情況。奧地利人格·卡明斯基主編的《中國的大時代:羅生特在華手記(1941—194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記錄了奧地利醫(yī)生羅生特1941—1943年在江蘇新四軍根據(jù)地及1943—1945在山東抗日根據(jù)地的服務經(jīng)歷。波蘭裔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寫有多部有關(guān)中共革命的著作:《見證中國:愛潑斯坦回憶錄》(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涉及大量中共抗戰(zhàn)的相關(guān)史實,該書部分內(nèi)容又被節(jié)選為《歷史不應忘記》(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一書,記錄了其在延安及新四軍中采訪中共領(lǐng)導人的情況;《人民之戰(zhàn)》⑤(新華出版社,1991年)報道了晉察冀邊區(qū)和新四軍的情況;《中國未完成的革命》⑥(新華出版社,1987年)則介紹了其親歷的敵后戰(zhàn)場,及根據(jù)地的新民主主義經(jīng)濟;《我訪問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家書》(新星出版社,2015年)記錄了其1944年訪問延安的見聞。貝特蘭的《華北前線》⑦(新華出版社,1986年),詳細介紹了作者1937年在延安、晉南八路軍總部和120師采訪,并隨小分隊遍訪華北前線的經(jīng)歷;《在中國的歲月:貝特蘭回憶錄》⑧(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3年)則同樣有專門章節(jié)介紹其在延安及華北前線的活動。
蘇聯(lián)對中國抗戰(zhàn)給予了大力支持,也有來華人士撰有回憶錄。名將崔可夫曾在抗戰(zhàn)期間擔任國民政府軍事顧問,其著作《在中國的使命:一個軍事顧問的筆記1940—1942》(解放軍出版社,2012年)記錄了皖南事變及其所認知的中國共產(chǎn)黨。羅曼·卡爾曼的《在華一年:蘇聯(lián)電影記者筆記(1938—1939)》(人民出版社,2020年)則被譽為蘇聯(lián)人寫的《西行漫記》,該書作者是新聞電影攝影師和導演,1939年親赴陜甘寧邊區(qū)采訪了中共領(lǐng)袖,并通過該筆記向全世界真實展現(xiàn)了邊區(qū)人民的生活。
當時還有很多日本的反戰(zhàn)人士參加中共軍隊并寫有回憶錄,記錄了他們的反戰(zhàn)經(jīng)歷及八路軍的作戰(zhàn)情況。小林清的《在中國的土地上:一個“日本八路”的自述》①(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香川孝志、前田光繁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延安日本工農(nóng)學校紀實》(長征出版社,1985年)②,水野靖夫的《反戰(zhàn)士兵手記》(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2015年再版),野坂參三的《為和平而戰(zhàn)》(解放軍出版社,2015年)及鈴木傳三郎等的《一個老八路和日本俘虜?shù)幕貞洝罚▽W苑出版社,2000年)等書,記錄了他們參與的八路軍對日反戰(zhàn)宣傳工作,對研究抗戰(zhàn)時期的日本反戰(zhàn)運動頗有參考價值。
還有一些來華海外人士親歷了解放戰(zhàn)爭并著有相關(guān)作品。美國記者杰克·貝爾登的《中國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主要記錄了華北解放區(qū)的土地革命、婦女生活、軍隊情況等。美國人韓丁的《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北京出版社,1980年)根據(jù)親身體驗記錄了1948年山西長治張莊的土改情況。英國人伊莎白·柯魯克、大衛(wèi)·柯魯克的《十里店(一):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及《十里店(二):中國一個村莊的群眾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兩書,是柯魯克夫婦于1948年春作為觀察員采訪河北十里店村土改復查和整黨運動的紀實性作品,對當時分地后的農(nóng)民反應,整黨后黨員干部和群眾的面貌有生動描寫。美國人葛蘭恒等的《解放區(qū)見聞》(新華出版社,1993年)主要為葛蘭恒、羅爾波等于1946—1948年在山東解放區(qū)的觀察報道。美國人斯特朗的《中國人征服中國》(北京出版社,1984年)則為作者1946—1947年在延安、陜甘寧、晉察冀的采訪紀實,報道了中共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情況及軍事政策。日本人橫川次郎曾參加東北民主聯(lián)軍,他在《我走過的崎嶇小路——橫川次郎回憶錄》(新世界出版社,1991年)中記錄了1946—1948年其在東北參與解放戰(zhàn)爭的情況。日本人古川萬太郎的《冰凍大地之歌》(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釘崎衛(wèi)的《黎明前的洗禮》(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川畑一子的《大江東流:川畑一子與解放軍一起走過的青春道路》(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年)等著作也回憶了他們跟隨解放軍參加解放戰(zhàn)爭的經(jīng)歷。美國記者西默·托平的《在新舊中國間穿行》(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則記述了作者親歷的淮海戰(zhàn)役及南京解放的細節(jié)。
此外,亦有來華海外人士所寫的中共領(lǐng)袖的個人傳記譯介至國內(nèi)。如埃德加·斯諾筆錄的《毛澤東自傳》③(青島出版社,2003年)記錄了毛澤東前半生的經(jīng)歷;史沫特萊的《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79年)則詳細介紹了朱德的生平事跡。
二、海外親歷者書寫的中共革命史內(nèi)容
海外親歷者所寫的中共革命史著作內(nèi)容廣泛,涉及中國共產(chǎn)黨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社會生活等領(lǐng)域的情況。這些著作特別重視在社會文化史視野下書寫革命史,注重深入挖掘和分析人物的生平事跡,不僅關(guān)注精英人物,還關(guān)注根據(jù)地的普通知識分子、戰(zhàn)士、婦女等基層民眾,展示了中共革命的方方面面及根據(jù)地的眾生相。
中國共產(chǎn)黨軍隊的作戰(zhàn)是來華海外人士的關(guān)注重點。高林在晉察冀邊區(qū)親歷了中共開展的抗日敵后游擊戰(zhàn),他敘述稱:“為了要同優(yōu)勢敵軍的作戰(zhàn)中取得生存,民兵避免和日軍打正規(guī)戰(zhàn),因為他們沒有攻城掠地的軍事手段。同時,由于他們的火力太弱,也不能打硬仗。因而,共產(chǎn)黨人集中力量打襲擾戰(zhàn),依靠速度、突擊、勇氣和完善的機動性來取勝——這一切均依靠周密的計劃。”[1](p107)班威廉等則分析了八路軍敵后游擊戰(zhàn)取得成功的原因:“八路軍以山區(qū)的主要抗日根據(jù)地為中心,時時向敵人襲擊,這項策略之所以能夠發(fā)生效果,乃是基于一個事實,那就是:敵人因擴展封鎖區(qū)域的結(jié)果,兵力分散得厲害,每一據(jù)點往往只有少量的護衛(wèi)部隊,因此中國軍隊可以隨心所欲地越過整個的鐵路地帶而不致遇到優(yōu)勢的敵軍。”[2](p118)當時他們親自到前線見證了中共的軍事作戰(zhàn),故對中共靈活戰(zhàn)術(shù)的敘述較為可信。
軍民關(guān)系是當時來華海外人士關(guān)注的熱點,他們肯定了中共贏得民眾廣泛支持的做法。鈴木傳三郎描述了民眾對八路軍的支持:“世界上未必有像八路軍和農(nóng)民那樣的鐵一般的團結(jié)。八路軍不論將軍和士兵,一概都十分愛護老百姓,而老百姓也把八路軍視作親人。八路軍部隊移動時,沿途所住的兵站,一般都是借用民房,和老百姓住在一起,親密無間。”[3](p219)葛蘭恒生動記述了百姓對半夜行軍的解放軍的支持:“即使是最緊張的強行軍,也充滿勝利前進的氣氛。沿途的每個村莊都喜氣洋洋。每一家的門前都有一盞把油盛在淺碟里點燃的油燈,從土墻的—些缺損處發(fā)出微弱的亮光。所有村民都站在那兒迎接隊伍,用口號、歌聲、香煙和茶水鼓勵他們快速前進。”[4](p30)貝爾登評述了中共軍隊的征兵工作:“八路軍采取宣傳、說服和利用地方上社會壓力的辦法,動員人參軍。軍屬受到優(yōu)待。村里給戰(zhàn)士代耕土地,并照顧其親屬。在蔣管區(qū),農(nóng)民認為當兵是件丟人和悲慘的事情;而在解放區(qū),共產(chǎn)黨使參軍成為件光榮的事情。”[5](p424)戴維斯則闡述了共產(chǎn)黨贏得農(nóng)民支持的原因:“共產(chǎn)黨來到他們身邊,告訴他們不要絕望,他們要依靠共產(chǎn)黨組織強大起來,抵抗敵人并最終獲得勝利。共產(chǎn)黨干部和軍隊尊重每個農(nóng)民,激發(fā)他們的思考,促使他們參與決策,然后獲得他們的信任。而在此過程中,共產(chǎn)黨對他們強調(diào)的是民族主義和如何抵抗侵略者。”[6](p272)這些生動記述展現(xiàn)了共產(chǎn)黨軍隊與人民群眾的密切關(guān)系,與國民黨軍隊形成鮮明對比,這也是中共取得勝利的重要保證。
政治教育、官兵平等等中共部隊中較有特色的工作,也為來華海外人士所關(guān)注。卡爾遜觀察到中共部隊普遍設有政委,在他看來:“政治工作是八路軍軍事行動獲勝的最重要因素。通過對個體的勸服,士兵覺得自覺執(zhí)行上級指示是他們的職責,意志力成為八路軍的立軍之本。部隊里極少有強迫行為,只是讓每個人愿意做他們認為正確的事情。履行職責是同樣的道理,士兵很樂意執(zhí)行上司所委派的任務。”[7](p109)在延安參加反戰(zhàn)的日軍士兵水野靖夫也注意到八路軍的政治工作:“在八路軍中政治要絕對領(lǐng)導軍事,上自一個團,下至一個連,至少都派有一名政治指導員。這些指導員,平日擔任著士兵的文化指導甚至代寫家信。一旦開始戰(zhàn)斗,便對這場戰(zhàn)斗的政治意義和認識承擔起指導的責任。”[8](p110)漢森則注意到中共軍隊的政治信仰與民主精神:“這支軍隊之所以具有如此強的戰(zhàn)斗力的另一原因,也許是主要原因,在于其政治信仰。從總司令到紅小鬼和趕騾子的人,似乎所有人都相信中國最終會取得勝利。他們因農(nóng)民獲得的新的政治權(quán)利而感到自豪。整個軍隊都擁有一種民主精神。軍官們除了‘同志以外再無其他稱呼,軍官和士兵吃一樣的食物,接受同樣嚴格的紀律約束,尤其在對待農(nóng)民方面。”[9](p226)高林還注意到在延安的平等同志關(guān)系:“士兵和軍官在輕松的同志式友愛氣氛中,相互談天和開玩笑。在集會上不安排座次。在討論中,毛和所有其他人都簡單地被稱作‘同志。在制服上沒有軍銜標志、單位編號或其他番號。” [1](p33)
來華海外人士還描述了中共根據(jù)地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狀況,高度贊揚中共在抗戰(zhàn)時期采取的“三三制”、普選制等民主模式。白修德肯定了延安的民主作風:“在行政方面,批評和討論的自由的確是毫無限制的,對于一個方針的執(zhí)行不當,對于無論文武當局的失錯,任何人都可以予以批評。……在各地,這種行政上的批評自由形成了中國農(nóng)民所從未有過的最民主的政治制度。地方上的會議可以接受他們的控訴和滿足他們的需求,可以說有史以來第一次他們成了這個社會里的平等公民。”[10](p260-261)王安娜介紹了抗戰(zhàn)時期延安大生產(chǎn)運動的成效:“生產(chǎn)運動的重要性并不亞于前線的軍事行動。這個運動的重點是開墾已經(jīng)荒蕪了的農(nóng)田,配給良種,減輕稅收,實行信用貸款。此外,軍隊和行政機構(gòu)實行自給自足,以自己的力量,利用荒地種糧食、蔬菜、棉花等。進入40年代,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敵后各根據(jù)地的人民生活水平盡管仍然受到日軍的破壞,但已比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要高。”[11](p336)中共在根據(jù)地開展的土地改革贏得了廣大農(nóng)民的支持,貝爾登分析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的土地改革,客觀評價了土改的作用:“共產(chǎn)黨的土地政策,在中國奪取政權(quán)的斗爭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因為它動員了多少年來受壓抑的廣大群眾奮起推翻舊社會。土地革命從兩個方面打破了中國農(nóng)民似乎是千古不變的蟄伏狀態(tài)……在精神方面,土地改革喚起了農(nóng)民的希望。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產(chǎn)生的激情。在物質(zhì)方面,土地改革給農(nóng)民提供了與地主進行斗爭的手段。”[5](p189)這些記載都為來華海外人士的實地觀察,為從“新革命史”視角觀察中共革命提供了絕佳資料。
來華海外人士非常注重觀察與采訪中共領(lǐng)導人,特別是毛澤東,他們對人物的刻畫涉及生活、學習、工作經(jīng)歷等方方面面,且特別重視從階級出身及社會背景角度開展分析。貝特蘭評價毛澤東:“我可以說,毛澤東具有超群出眾的,足以代表中國式的最好的精神特征的精明和韌性。就是這種原因使他在這一向充滿了機靈的政治投機家的中國成為一個成功的政治戰(zhàn)略家。因為他這種才能是在一種有訓練的,合乎人道的意志的支配和控制之下的(這種情形在中國是少有的)。”[12](p120)班維廉夫婦印象中的中共軍隊領(lǐng)袖“是一群奇特的被遺棄了的人物。他們過的是一種艱苦奮斗的生活。……他們大都曾在高山峻嶺,深林大川中過生活,而他們又都是英勇農(nóng)民階級的兒子。他們都有一種干脆的性格,這種性格在大都市的居民之中是很難找到的;他們那種豪爽的脾氣與人口稠密之區(qū)的奸商們相較之下,令人覺得頗有點象西方人”[2](p141)。謝偉思對中共領(lǐng)導人的素質(zhì)有過總體評價:“他們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講求實效的人們組成的一個統(tǒng)一的集體,這些人忘我地獻身于崇高的原則,并且有杰出才干和堅毅的領(lǐng)導素質(zhì)。這一印象——和使我聯(lián)想起的他們的經(jīng)歷——把他們排列在現(xiàn)代中國任何一個團體之上。”[13](p202)鈴木傳三郎則肯定了中共領(lǐng)導人的能力:“中國共產(chǎn)黨活動的輝煌成就,原因有一半是由于領(lǐng)導層的卓越的領(lǐng)導能力而來,而另一半我想是由于有一批為了實現(xiàn)他們的理想,不謀求名譽、地位,只顧埋頭于政治工作的干部。他們的事業(yè)心、責任感、見識、希望,都令我不勝欽佩。”[3](p213)
海外親歷者對中共革命具體實踐的整體印象頗佳,對其未來充滿希望。喬伊·荷馬指出:“我看到共產(chǎn)黨作為一個政黨,上到黨的領(lǐng)導人,下到年紀輕輕的戰(zhàn)士,比起那些非共產(chǎn)黨人,他們對于日軍有著更加堅定、絕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和那份誓死贏得戰(zhàn)爭的決心。認為這個組織(這是一個有智慧的組織)會因為個人的得失而顛覆了自己道路的想法幾乎是荒謬可笑的。”[14](p217)卡爾遜則認為共產(chǎn)黨“處世率直、生活樸素,在轄區(qū)的管理誠信,所產(chǎn)生的感召力使得中國青年匯集于共產(chǎn)主義的大旗之下”[7](p95)。不少來華海外人士展望了中國革命的美好前途,如1944年10月9日謝偉思預測:“共產(chǎn)黨已建立了既廣且深的群眾支持,因而使他們之被消滅成為不可能,從這基本的事實,我們必須得出結(jié)論,未來的中國,共產(chǎn)黨將占有確定的和重要的地位。”[15](p527)之后的歷史走向,也充分印證了其預言。
三、海外親歷者的中國革命史書寫特點
與后世研究者的書寫不同,海外親歷者對中共革命史的書寫自有特點,如這些書寫建立在他們實地調(diào)查的基礎上,重視將宏觀敘述與微觀考察相結(jié)合,注重在中共內(nèi)部及中共與國民黨之間進行比較研究,多從大歷史觀的視角來敘述中共革命史等。
其一,來華海外親歷者的革命史著作的顯著特點是他們的書寫依據(jù)是實地調(diào)查所得的一手資料,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無論是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蘇聯(lián)顧問,還是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的斯諾、薄復禮等人,抑或是抗戰(zhàn)時期來根據(jù)地采訪的大批外國記者,都見證了中共革命史的細節(jié)。他們的著作駁斥了國民黨對中共的種種污蔑,如國民黨攻擊紅軍為“土匪”,薄復禮接觸了長征中的紅軍后指出:“這些人實際上是堅信共產(chǎn)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并實踐著其原理,是另一種形式的蘇維埃。”[16](作者自序p3)貝特蘭1937年初訪問了西北紅軍后,對外界廣泛宣揚的所謂“赤色恐怖”的說法予以了駁斥:“真正碰到過紅軍的難民卻說紅軍是全中國最有紀律最有秩序的軍隊。”[17](p233)“不管中國農(nóng)民的性命多么便宜,共產(chǎn)黨人決不是‘匪,正式的紅軍恐怕比任何其他軍隊都更有資格獲得‘國民革命軍的名稱。”[17](p256)再如愛潑斯坦1944年訪問陜甘寧邊區(qū)時,駁斥了國民黨宣傳的中共在邊區(qū)種植鴉片的謠言,指出:“本記者愿以本人的職業(yè)聲譽作為擔保,明白無誤地聲明:所有一切最近在中國和國外談論的關(guān)于中國共產(chǎn)黨正在種鴉片的罪狀都是無稽之談。”[18](p71)
當然,由于文化差異、語言障礙、政見分歧等各種因素影響,一些來華海外人士記述的相關(guān)史實存在明顯錯誤或故意歪曲。在一些親歷者的著作中,也有錯誤記敘根據(jù)地的地名、人名、時間、事件等的情況。
其二,來華海外親歷者多從大歷史的全局,用變化發(fā)展的眼光考察問題。卡爾遜實地考察山西八路軍的狀況后提出:“必須考慮中國問題的更加廣闊的方面。山西只是這個國家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中國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經(jīng)證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式推廣到共和國的所有地方,這顯然是困難的,因為許多國民黨官員同共產(chǎn)黨人尖銳地對立,他們不肯采納后者設計的任何計劃。所以,第二個大問題是要消除對立。”[19](p110)他們還重視探討中共的形象變化,如班威廉等分析指出,他們開頭的時候大都是以破壞半封建軍閥政府統(tǒng)治下的社會秩序為職志的所謂“匪”,可是他們高超的目光使他們不滿于只止于“暴動”,他們轉(zhuǎn)變了中國社會最惡劣的一面,經(jīng)共產(chǎn)黨發(fā)動了文化戰(zhàn)爭之后,向來被視為“寄生匪徒”的兵在華北已轉(zhuǎn)變?yōu)樯鐣髲团d的領(lǐng)導者[2](p141-142)。韓丁則運用普遍性與特殊性原理,通過張莊的個案研究分析了中共革命的深遠影響:“當中國革命的進程全面展開時,它包括前進與后退,右傾與左傾,每日、每時、每分鐘的量變到突然的質(zhì)變。總之,革命的進程深入了,它不僅改變了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也改變了人們的思想意識。而正是后一方面組成了革命的特殊力量,是使革命所導致的變化深刻而持久的保證。”[20](序言p4)由于來華海外人士不熟悉中國國情,慣用西方思維模式考察中國問題,其分析反而有獨特細致之處。
其三,來華海外親歷者喜歡通過與外國事物比照來敘述中共的相關(guān)情況,以便使對中國感到陌生的國外讀者了解中國革命的實況。斯諾夫人1937年訪問延安時曾說:“延安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那里的人們生活純樸,思想高尚——類似于英國的新村,只是多了幾分危險。”[21](增訂版前言p3)再如林邁可為說明延安和陜甘寧邊區(qū)在抗戰(zhàn)時期的重要性,曾將其和美國的哥倫比亞特區(qū)及澳大利亞的堪培拉相比擬[22](p3)。卡爾遜對朱德印象深刻,認為他具有羅伯特·E·李的仁慈、阿伯拉罕·林肯的謙恭和U·S·格蘭特的堅強[19](p59)。林邁可還比較了中共革命與東南亞革命的所處環(huán)境:“與東南亞共產(chǎn)黨的革命相比,中共在華北所處的地理和氣候條件都不利于游擊戰(zhàn)爭。除山西西北部分地區(qū)外,這里的山區(qū)確實是荒涼的,而且沒有道路,山是光禿禿的,根本不像越南和馬來亞的游擊區(qū)那樣,覆蓋著茂密的叢林。更有甚者,冀中是一馬平川。”[22](p22)
其四,來華海外親歷者重視進行比較分析,以向國外介紹真實的中共情況。如由于外國讀者分辨不清中共抗戰(zhàn)軍隊的區(qū)別,愛潑斯坦便根據(jù)親身經(jīng)歷,比較了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情況:“八路軍擁有數(shù)十萬兵力,主要是在它從日軍手中收復的地盤活動。新四軍則不同,它的活動被限制在一定的地盤內(nèi),要受在它來之前早已建立的軍政當局的管轄。在華北的許多地區(qū),八路軍和自己組織起來的游擊隊是單獨作戰(zhàn)的。新四軍則是東戰(zhàn)區(qū)諸種軍事力量中的一種。它必須接受戰(zhàn)區(qū)司令部的命令,仰賴它的財政和給養(yǎng)。在兵源的補充方面,它沒有華北游擊隊那種自由。”[23](p235)林邁可比較了延安與晉察冀抗日根據(jù)地的區(qū)別并分析了原因:“延安的物質(zhì)條件和前方相比要好得多,但這里的組織機構(gòu)和晉察冀前方相比,其工作效率和節(jié)奏卻顯得緩慢。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種差別,我考慮一個原因是,前方是游擊戰(zhàn)斗區(qū),在缺乏外部供給給養(yǎng)的條件下,一切全靠自己想辦法,靠和人民配合來打擊敵人,所以迅速決策和行動是第一要務。我想另一原因可能是,在延安的黨的中樞組織必須精心地按部就班地把行政工作做到盡善盡美。”[22](p189)王安娜親歷了抗戰(zhàn)時期根據(jù)地和國統(tǒng)區(qū)的不同生活,頗有感觸地比較了國共雙方:“與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相比,共產(chǎn)黨控制的地區(qū)的施政要民主得多,這是我親眼目睹所得出的結(jié)論。在我之前和在我之后來自各國的非親共的觀察家,也持有同樣的看法。后來被毛澤東稱為‘新民主主義的實施,對愛國者、理想主義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對青年一代,有著很大的吸引力。對此,蔣介石只知以武力進行封鎖,別無他法。”[11](p343-344)羅生特亦比較了國共統(tǒng)治區(qū)生活:“解放區(qū)的生活和國民黨社會的生活,就像人體的健康組織和腐爛組織一樣,涇渭分明。在組織發(fā)生學上,健康器官和膿灶之間有一條清楚的界線。解放區(qū)是純潔的,人們愉快地勞動,而中國其他地區(qū)是腐敗的,已經(jīng)被國民黨污染,兩者之間橫亙著一條同樣的界線。”[24](p162)總體而言,來華海外親歷者的切身體驗,使他們總體對中共持同情支持態(tài)度。
四、研究反思
(一)學界利用情況
1921—1949年期間來華海外親歷者的中共革命史書寫,提供了珍貴且豐富的細節(jié)資料,有其獨特價值。他們從宏觀與微觀的不同角度審視中共革命史,從第三者的視角觀察與研究“紅色中國”形象,呈現(xiàn)出中共革命的多元與復雜面相,從深度與廣度上都推進了中共革命史的研究。這些作品基本上對中共歷史進行了客觀評價,打破了外界對中共的種種謠言,向國外宣傳了積極正面的中共形象,為中共贏得國際社會同情與支持提供了便利。在親歷者的敘述中,中國共產(chǎn)黨的形象也隨著局勢的變化而不斷改變,經(jīng)歷了從普通政黨到抗戰(zhàn)中流砥柱,再到奪取全國勝利政黨的形象轉(zhuǎn)變。這些海外親歷者身份多元,有記者、作家、外交官、軍人、政治顧問、醫(yī)生等,既有持政治立場中立的人士,也有以斯諾、斯特朗、史沫特萊為代表的對共產(chǎn)黨同情支持的左翼人士,還有支持國民黨政府的美國軍官、外交人員,他們的身份也決定了其觀察中共革命史的視角與立場,因而不可避免地摻雜了個人感情因素、主觀意見于其黨史書寫中,需要研究者客觀分析。
隨著中共黨史研究的日漸繁榮,學界對這些黨史譯著已有較多利用,特別是在有關(guān)中共抗戰(zhàn)的研究中運用最多。如金紫光等主編的《外國人筆下的中國紅軍》(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jù)地研究會主編的《國際友人筆下的新四軍》(解放軍出版社,2016年)等著作,收錄匯編了大量上述譯著中關(guān)于紅軍和新四軍的記載。在一些綜合性研究中,如朱紀華主編的《外國記者眼中的中國共產(chǎn)黨人》(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2015年)及方明的《抵抗的中國:外國記者親歷的中國抗戰(zhàn)》(團結(jié)出版社,2017年)等著作,都大量使用了前述譯著資料;黃靜的《美國左翼作家筆下的“紅色中國”形象(1925—1949)》(九州出版社,2021年)則利用了史沫特萊、斯諾、斯特朗等人所寫的著作。總體來看,學界對來華記者的黨史譯著利用較多,對來華外國軍官、外交官等其他群體的譯著的利用相對薄弱,尚需對相關(guān)資料繼續(xù)挖掘,豐富中共革命史的研究內(nèi)容。
(二)未來研究利用路徑前瞻
雖然目前國內(nèi)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已取得長足進步,但從全球史視角考察中共黨史的國際性的研究仍有極大的深化拓展空間。筆者認為,前述譯著呈現(xiàn)了不同國籍、不同群體的來華海外人士觀察中共黨史的視角,展現(xiàn)了來華海外人士的獨特認知,對于將中共革命史置于全球史的大背景下,從他者視角分析革命史中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探討事件背后的國際因素的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同時,國內(nèi)學界正大力推進“新革命史”研究,注重觀察革命史的微觀細節(jié)及日常生活,前述譯著恰對這些內(nèi)容有大量記載,正可供學者充分利用。此外,前述譯著在中共革命史中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治工作、軍民關(guān)系、根據(jù)地建設等重要問題的研究中亦可發(fā)揮重要作用。
當然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國內(nèi)已出版的海外中共革命史譯著質(zhì)量參差不齊,甚至存在錯譯問題,學者開展相關(guān)研究時需要參考外文原著,并充分利用英國外交部檔案、美國對外關(guān)系文件等外文原始檔案。另外,受多重因素影響,尚有許多海外親歷者所寫的英語、日語、俄語、德語、法語等語種的中共革命史著作未能翻譯,亟待出版社與學者共同努力,將這些著作譯介至國內(nèi),為深化中共革命史研究貢獻資料。
參考文獻:
[1][美]高林.延安精神:戰(zhàn)時中美友好篇章[M].孫振皋,譯. 北京:華藝出版社,1992.
[2][英]班威廉,[英]克蘭爾.新西行漫記[M].斐然,何文介,吳楚,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3]劉國霖,[日]鈴木傳三郎.一個老八路和日本俘虜?shù)幕貞沎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
[4][美]葛蘭恒,等.解放區(qū)見聞[M].麥少楣,葉至美,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
[5][美]杰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M].邱應覺,楊海平,胡代崗,等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6][美]約翰·帕頓·戴維斯.未了中國緣:一部自傳[M].張翔,陳楓,李敏,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
[7]舒暲,趙岳.太陽正在升起:卡爾遜親歷的中國抗戰(zhàn)[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
[8][日]水野靖夫.反戰(zhàn)士兵手記[M].鞏長今,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
[9][美]霍爾多·漢森.中國抗戰(zhàn)紀事[M].韓瑞國,譯.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7.
[10][美]白修德,[美]賈安娜.中國的驚雷[M].端納,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8.
[11][德]王安娜.嫁給革命的中國[M].李良健,李希賢,校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9.
[12][新西蘭]詹姆斯·貝特蘭.華北前線[M].林淡秋,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
[13][美]約瑟夫·W.埃謝里克.在中國失掉的機會:美國前駐華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期的報告[M].羅清,趙仲強,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14][美]喬伊·荷馬.在中國看見曙光[M].吉文凱,譯.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
[15]中共陜西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在延安[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5.
[16][瑞士]薄復禮.一個西方傳教士的長征親歷記[M].嚴強,席偉,譯.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8.
[17][新西蘭]詹姆斯·貝特蘭.中國的新生[M].林淡秋,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
[18]伊斯雷爾·愛潑斯坦.我訪問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家書[M].張揚,張永澄,沈蘇儒,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19][美]埃文斯·福代斯·卡爾遜.中國的雙星[M].祁國明,汪杉,譯.汪溪,校.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
[20][美]韓丁.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M].韓倞,等譯.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21][美]海倫·福斯特·斯諾.紅都延安采訪實錄[M].張士義,張香存,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4.
[22][英]林邁可.抗戰(zhàn)中的中共:圖文見證八路軍抗戰(zhàn)史[M].楊重光,郝平,譯.李效黎,校.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13.
[23]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人民之戰(zhàn)[M].賈宗誼,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5.
[24][奧]格·卡明斯基.中國的大時代:羅生特在華手記(1941—1949)[M].杜文堂,李傳松,柳葉,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