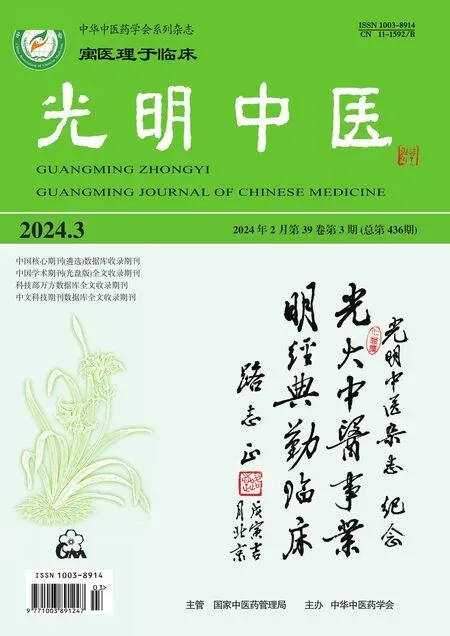電針聯合穴位敷貼在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患者中的應用
胡 艷 萬德仁 黃麗紅
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屬于臨床上治療難度較大的一種精神疾病,臨床上常表現為神情淡漠、思維貧乏、缺乏主動性等癥狀,患者的精神活動能力、社會功能等逐漸趨于衰退,對患者的日常生活有嚴重影響,且對患者的身心健康不利。臨床上常給予常規的西藥聯合穴位敷貼進行對癥治療,安全性較高,但其對于患者腦部神經受損的修復作用甚微,患者于治療后易反復,故而不利于患者的預后恢復[1,2]。中醫認為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屬于“癲證”范疇,常因七情受傷,使陰陽失衡、氣血不通,致神情淡漠、消沉懶散之癥,應以活血化瘀、開竅醒腦、調理情志之法進行治療,采用穴位電針對特定的穴位進行刺激,起到通經活絡、化瘀活血、提神醒腦的功效,此外采用中藥進行穴位敷貼可調理情志、益腎健脾、開竅醒腦,且操作較為簡便,兩者聯合使用可改善患者的臨床癥狀,促進恢復,更有利于患者的預后恢復[3]。故本研究主要探討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患者采用穴位電針聯合穴位敷貼對患者認知功能、自我效能等改善效果,現根據此次研究的內容及結果進行以下闡述。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19年10月—2021年10月九江市第五人民醫院收治的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患者86例,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試驗組43例、對照組43例。試驗組中女性20例,男性23例;年齡26~59歲,平均(40.05±5.45)歲;病程1~9年,平均(3.25±1.05)年;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5例,高中24例,大專及以上4例。對照組中男性25例,女性18例;年齡25~61歲,平均(40.02±5.43)歲;病程2~7年,平均(3.27±1.02)年;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3例,高中27例,大專及以上3例。2組患者一般資料對比,P>0.05,可進行后續研究。九江市第五人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準許此項研究的實施,所有研究對象家屬均知悉此研究并在相關文件上簽字確認。
1.2 診斷標準西醫依據《CCMD-3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4]中關于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的診斷標準;中醫參照《中醫神志病臨床診療指南》[5]中關于癲證的相關描述。
1.3 納入標準符合上述中西醫診斷標準者;入院經臨床癥狀、實驗室指標等檢查確診者;近3個月病情較為穩定者;經陽性與陰性癥狀量表(PANSS)檢測[6],陰性癥狀評分高于20分且高于陽性癥狀評分者;中醫主癥為煩躁不安、神情淡漠等,次癥為舌苔發白、脈象細弦等。
1.4 排除標準合并有軀體功能障礙或殘疾者;有針刺不耐受、暈針、電針禁忌證等情況者;無法配合指標檢測后續隨訪者;精神活性物質等導致精神障礙者;妊娠哺乳期婦女等。
1.5 方法
1.5.1 治療方法對照組給予常規的藥物進行對癥治療,即富馬酸喹硫平片(規格:100 mg/片,湖南洞庭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 H20010117)。初始劑量100 mg/d,根據患者病情逐漸增加劑量,控制劑量為500~700 mg/d;此外給予穴位敷貼,即將中藥赤芍、當歸、地龍、山萸肉、桃仁、黃精等研成粉末后用醋調制成糊狀敷貼,每次6 g貼敷于患者的雙側腎俞,4 h/次,1次/d。試驗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給予穴位電針療法,即讓患者行仰臥位,使用一次性針灸針(吳江市神龍醫療保健品有限公司,蘇械注準:20172270270,規格:直徑0.16~0.45 mm,長度13~100 mm)常規消毒后對患者的印堂、百會緩慢進行13~20 mm的平刺,儀器使用由南京濟生醫療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HANS100A韓氏穴位神經刺激儀,頻率設定為2 Hz/15 Hz疏密交替波,印堂、百會電極連接分別為負、正極,電流強度依據患者的耐受情況,即患者皮膚輕微抖動為最佳,30 min/次,隔天1次,3次/周。2組均治療3個月,并于治療后隨訪3個月。
1.5.2 觀察指標①中醫證候量表評分[7]:于治療前、治療3個月后、治療后3個月對2組患者的中醫證候進行評價并比較,量表主要包括4個維度,各維度均為3分,總分為12分,患者的臨床癥狀改善越好則總分越低。②認知功能[8]:于治療前及治療3個月后參照威斯康星卡片分類測驗(WCST)對2組患者的認知功能進行評價并比較,主要包括總正確數、總錯誤數、持續反應數、持續錯誤數、完成分類數,各項分值根據計算機生成結果進行統計。③大體評定量表(GAS)[9]評分、陰性癥狀分量表評分、住院慢性精神分裂癥社會功能評定量表(SSSI)[10]評分:于治療前及治療3個月后對2組患者的GAS、陰性癥狀分量表、SSSI評分進行評價并比較,其中GAS總分為100分,患者病情越嚴重則分值越低;陰性癥狀分量表總分為49分,患者的陰性癥狀越嚴重則分值越高;SSSI總分為20分,患者的社會功能越差則分值越高。④ 睡眠情況:于治療前及治療3個月后對2組患者包括覺醒次數、入睡時間、總睡眠時間在內的睡眠情況進行統計并比較。⑤ 自我效能:于治療前、治療3個月后、治療后3個月參照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11]對2組患者的自我效能進行評價并比較,總分為40分,患者的自我效能感越好則患者的此項評分越高。

2 結果
2.1 中醫證候量表評分與治療前比,治療3個月后、治療后3個月2組患者中醫證候量表評分呈逐漸降低趨勢,其中試驗組相比于對照組更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中醫證候量表評分比較 (分,
2.2 認知功能與治療前比較,治療3個月后2組患者總正確數、完成分類數升高,且試驗組比對照組高;2組患者總錯誤數、持續反應數、持續錯誤數降低,且試驗組比對照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患者認知功能比較 (分,
2.3 GAS評分 陰性癥狀分量表評分 SSSI評分與治療前比較,治療3個月后2組患者GAS評分均升高,其中試驗組比對照組高;2組患者陰性癥狀分量表評分、SSSI評分降低,且試驗組比對照組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2組患者GAS評分 陰性癥狀分量表評分 SSSI評分比較 (分,
2.4 睡眠情況與治療前比較,治療3個月后,2組患者覺醒次數、入睡時間減少,且試驗組比對照組少(P<0.05);2組患者總睡眠時間延長,其中試驗組比對照組長,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2組患者睡眠情況比較 (例,
2.5 自我效能與治療前比,治療3個月后、治療后3個月2組患者自我效能評分呈逐漸升高趨勢,其中試驗組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2組患者自我效能比較 (分,
3 討論
臨床上對于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患者常采取常規的西藥聯合穴位敷貼進行治療,于治療后患者的臨床癥狀雖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易導致患者的自我效能和治療依從性降低,進而不利于患者的預后恢復,對患者的機體功能造成不利影響。
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屬于“癲證”等范疇,其病因病機為脾腎虧虛、邪氣侵入、血運受阻,使意志減退、腦神不調、情感冷漠、思想匱乏,終致言行異常、喜靜少動、徹夜難眠之癥[12]。穴位電針的主要穴位為印堂和百會,印堂為督脈必經之處,刺激可通神醒腦、安神定驚、助眠清神;百會為督脈、三陽經、足厥陰肝經匯聚之處,刺激可調節血氣、通經活絡、寧神安心,兩穴組合,共奏提神醒腦、解郁安心、通經活絡之效。此外,采用穴位敷貼,通過使用赤芍、當歸等藥物,可起化瘀活血、滋肝補腎、調理情志、補腦清神之效,兩者合用,效用更佳[13]。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3個月后、治療后3個月,試驗組相較于對照組的中醫證候量表評分較低、自我效能評分較高;治療3個月后,對照組相較于試驗組,總睡眠時間較短,覺醒次數、入睡時間較多,提示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患者采用穴位電針聯合穴位敷貼治療,可以促進患者臨床癥狀的恢復,提升自我效能感,改善中醫癥狀和睡眠情況,進而促進恢復,改善預后。
國內一項研究中發現[14],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常會導致患者的認知功能出現一定程度的障礙,提升臨床上對其治療的難度,此外,還會致使患者的社會功能異常,出現致殘的風險,故臨床上需采取有效措施改變這一現狀。范勇等[15]在研究中發現,使用電針對百會、印堂進行刺激可作用于腦部的神經元,促進神經功能的恢復,進而改善機體的認知功能,其機制在于,電針刺激可通過微量的電流調節大腦皮層的功能,改變患者的慣性思維模式,抑制陰性癥狀的持續進展,使得患者日常生活中可主動地進行自我管理,進而提升社會功能,最終促進患者的恢復。此項研究表明,治療3個月后,試驗組總正確數、完成分類數、GAS評分高于對照組,總錯誤數、持續反應數、持續錯誤數、陰性癥狀分量表評分、SSSI評分低于對照組,提示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患者采用穴位電針聯合穴位敷貼治療,可以改善患者的認知功能和整體精神病情,抑制陰性癥狀,提升社會功能改善臨床癥狀,促進患者的恢復。
綜上,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患者采用穴位電針聯合穴位敷貼治療,可以改善患者的臨床中醫癥狀和認知功能,抑制陰性癥狀,促進社會功能的提升,提升患者的自我效能和生活狀況,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納入研究樣本量較少且缺乏對于血清神經功能相關指標、炎性因子等研究,對于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的機制探討較為片面,故后續研究需納入更多的研究樣本量,進行更為深入地研究,對疾病的發病機制進行更為全面地探討,為后續臨床上中醫治療精神分裂癥殘留陰性癥狀提供更為客觀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