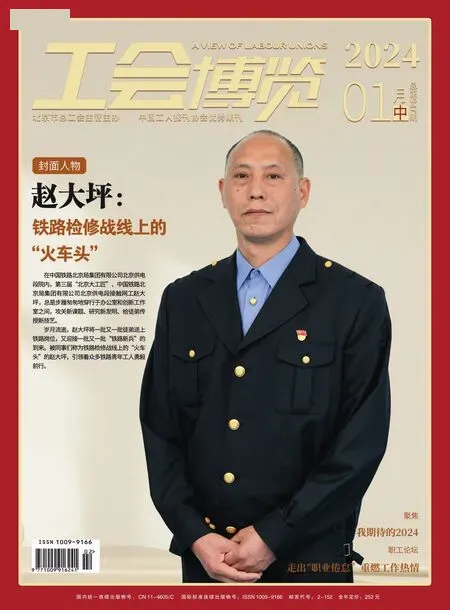記憶中的“老味道”
□本刊編輯部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記憶中的 “老味道” 仿佛是一扇通往過去的時光之門。“老味道”,仿佛曾經的記憶,懷舊而熟悉,它會是兒時的一道菜,也會是一段戀戀不舍的美食記憶。在回味“老味道” 的同時,我們更時常想起自己記憶中那座城市的老文化、老鄉土情。

張湘林 北京市順義區木林小學教師
忘不掉的粘豆包
粘豆包是老北京的傳統小吃之一,它承載著濃厚的歷史文化以及“60 后”“70 后”對過往時光的懷念。在小時候,每當路過街頭的小攤販或老字號店鋪,那香氣四溢的粘豆包總是令人心馳神往。那個時候,粘豆包是稀有的美食,需要排隊才能買到,但每一次品嘗都能帶來滿滿的幸福感和滿足感。
小時候有一次我和父親一起逛街,在一個擁擠的胡同口,我們遇到了一家小小的粘豆包攤位。人們排隊等候著,生意看起來很火爆,對美味的渴望驅使我向父親請求購買一份粘豆包嘗嘗。父親笑著點了點頭,他知道這是我期待已久的美味。
終于輪到我們,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個熱騰騰、散發著誘人香氣的粘豆包。它外皮晶瑩剔透,里面包裹著紅豆餡料。我小心翼翼地咬下一口,那糯軟的口感和濃郁的紅豆味道瞬間彌漫開來,幸福感油然而生,仿佛這就是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
從那以后,粘豆包成為我和父親最愛一起分享的美食。只要有空閑時間,他就會親自給我做粘豆包。每次,粘豆包還沒出鍋我就會焦急地站在旁邊等候,父親揭開鍋蓋的那一刻,我都會被它外皮的柔軟與彈性所吸引,然后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細嫩的紅豆餡料與口感細膩的面團相互融合,發出誘人的香氣,營造出一種獨特的口感和風味。端著粘豆包,我和父親會坐在胡同口的石凳上,邊品嘗邊聊天。那些時刻充滿了親情和溫馨,也成為我人生中最珍貴的回憶之一。
隨著歲月的流逝,我長大了,離開了父母的身邊,但是父親還是經常做好粘豆包后給我送來。每當吃著粘豆包,我都會回憶起童年時光里與父親一起品嘗粘豆包的幸福時刻。
粘豆包不僅是老北京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代表著老北京人對傳統面點制作工藝的珍視,更是聯結我與家鄉、與童年記憶的紐帶。它讓我感受到親情的溫暖和家鄉的味道,使我無論身在何處,都能感受到家的溫馨。

洪力鈞 諾基亞通信系統技術(北京)有限公司云和網絡服務部運營經理
耐人尋味的臺北味道
第一次到臺北出差,日程滿滿的三天會議結束,終于可以放松緊繃的神經,漫步臺北的大街小巷。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味道,聽到的話、走過的景、遇到的人都耐人尋味。初見臺北,我想細細品味一下這里的味道……
一位酒店里的工作人員聽到我講北京話,揚起眉毛說:“好喜歡你們的北京話‘兒’。”他很刻意地加入兒化音在句尾,順帶出憨憨的笑意。我聽得好笑又親切,誠懇地告訴他,其實臺灣腔咬字更周正,不像北京話說得輕快隨意,習慣性吞字跳字,有時聽得含混不清。臺灣的國文還保留著民國遺風,雖然有些詞匯與普通話略有差異,但絲毫不會影響彼此溝通并艷羨對方的口音,同一種語言兩種腔調隨即輕松愉快地攀談起來。
無論是老人還是年輕人,臺灣當地人對人對物都有知性的涵養,不嬌柔不浮夸,質樸中讓人感到舒適和溫暖。他們不緊不慢地講話,字字清透不肯省去恭敬謙和,就像沿用至今的繁體字,一筆一劃容不得一點怠慢和懶散。每每看到豎版印刷的繁體字,字里行間就會透出舊時光里的暖意,讓生長在大陸的我感覺熟悉又陌生。
漫步臺北街頭,會不自覺地回想起那些80 年代的經典老歌,忠孝東路、澎湖灣、西門町、鹿港小鎮。如今身臨其境在那些熟悉的旋律之中,街邊上藤蔓低垂的大榕樹,淡水河邊從容悠閑的人群,緊湊干凈的商鋪和小鎮。恍惚間幾十年的光景,依然能感受到歌中恬淡儒雅的氣息。
酒店不遠處,有一家牛肉面小館,從酒店房間就能看到那里每天顧客盈門。一天傍晚我走進這家面館,店主人和妻子兒子三人打理店內店外,小小的店面干凈整潔,只有6 套半舊的桌椅。客人們進到店里安靜地就坐,店家精簡的問候讓人感覺自在又舒適。店鋪里只提供牛肉面配免費小菜一盤,沒有菜單。食客絡繹不絕,明顯看出老熟客占了大多數,上了年紀的阿公阿婆、打扮精致的上班族、嬉鬧的學生進進出出。我坐在一角跟老板娘閑談,父子二人在里面忙著煮面。殊不知這一碗人間煙火經營了四代人,湯鍋里的熱氣從未間斷,濃濃的牛肉湯汁沉淀著幾十年風霜,散發著時光的醇香。我掩不住唇齒留香的喜悅,稱贊這是我吃到最好吃的牛肉面。老板娘開心又謙遜地說:“愛吃就好啦,每家牛肉面都有自己的味道嘛,愛吃哪家就吃哪家,反正下次來吃還是一樣的湯、一樣的面哦。”
臨近打烊,老板一家人熱誠地送我出門揮手告別。一家溫暖的牛肉面館,安靜地守候在街邊一隅。一鍋一灶,小火慢熬烹出持久而豐富的味道,彌漫在街巷里,也沁潤到我的記憶深處,這是臺北的味道——堅守著傳統,任光陰流轉,自有品味卻不張不揚。

劉銘洋 北京建工博海公司黨群工作部宣傳專員
一碗老面茶 一段舊時光
我雖出生在北京,但很小就被送到了天津的姥爺家。姥爺是個老“天津衛”,每天早晨都會一手牽著我、一手拎著鳥去海河邊遛早兒,然后去常光顧的那家早點鋪買早點。我常常隔著馬路就能聞到老味兒天津面茶那濃郁的芝麻香氣,買上兩大碗熱氣騰騰的面茶,再來幾個現炸的炸糕或果子,回到家大快朵頤一番。
“糜子面的熱面茶,伏天清晨喝最佳。健脾養胃食欲振,閑靜度夏享清睱。”這是天津民眾口口相傳的一首打油詩,寫的就是傳統清真小吃“面茶”。面茶選料為純糜子面,制作十分考究,先把糜子面半泡脹,磨成漿糊,用大鍋大火燒沸,加入適當的鹽堿礬姜粉熬,然后將糜子面調稀往翻花的地方澆,邊澆邊攪,再用細火熬,待糜子面成粥狀定型后封火保溫。另外,芝麻用開水燙后,再炒成金黃色后撒鹽,攪拌均勻后炒干水分再搟為粉末,制成芝麻鹽。麻醬用小磨香油調稀備用。盛的時候先盛半碗,撒上一層芝麻鹽、淋上麻醬,然后再盛上一層面茶,再撒上一層芝麻鹽、淋上麻醬,直到溢出為止。
關于吃面茶,周簡段曾這樣回憶:“兩手捧住碗,把嘴唇攏起,貼著碗邊,吸著,由右往左,熱乎乎地一口。而且還像鄭板橋說的,縮頸而吸之,沒有幾口,便凜意全消,暖流遍布,遍體生津矣。真是又熟又香的絕味,夢中我都思念著它啊——此味豈可再得乎?”吃面茶的時候講究不動筷子不動勺,左手五指拖碗送至嘴邊,轉著圈用嘴沿碗邊吸溜著趁熱喝,右手持棒槌果子,待面茶吃到中途可用棒槌果子輕輕推頂面茶,不使面茶掛碗。喝完之后用果子把碗里殘留的小料一抹,做到碗光、嘴光、手光,倍兒干凈。
去年清明,在回天津老家上墳的路上,正好路過姥爺常帶我去的那家早點鋪,沒吃早飯的我毫不猶豫地買了碗面茶。老板端上了熱騰騰的面茶。啊!就是這個味道,十幾年了一點沒變。我喝著面茶,又想起了小時候與姥爺一起喝面茶時的情景。如今姥爺早已駕鶴西去,睹物思人,我不禁潸然淚下。還記得我上高一的時候姥爺得了重病,最后的那段時光里幾乎都是在醫院病床上度過的,每隔兩周學校放假我都會去醫院探望姥爺。在一個寒冷的清晨,我去看姥爺的途中發現醫院附近一家鋪子門前排起了一長隊,我好奇地湊上前去,濃濃的咸香氣息便撲鼻而來,原來新開了一家面茶鋪。我排了不知道多久才買到了一份面茶,然后飛奔到姥爺床前,一勺一勺地喂姥爺吃著香滑可口的面茶。姥爺臉上浮現出久違的、一如童年的笑容,我想姥爺一定是吃到了愛的味道。
一碗面茶,吃的是味道,也是美好的回憶,賣面茶的窗口更是無數擁有同樣記憶的人通往舊時光的大門。
老味道是一種底蘊
在我的心頭,有一道菜叫做“回憶”,它的名字雖平凡,卻蘊含著百態人生的味道。這道菜,或許你聽過,或許你嘗過,又或許你曾親手烹制過。“回憶”這道菜,千人千面,千味千情。它并非拘泥于某一種烹飪技法,而是靈活變通,可以繁復精致,也可以樸素純粹。它是一份懷舊情懷的呈現,是時光隧道中的一幅幅閃回畫面。在我的“回憶”中,總有一道“老味道”獨占鰲頭,如同一幅古老的畫卷,緩緩展開。
小時候,家中的蔥爆羊肉是我最愛的“老味道”,說起來算是炙子烤肉的家庭版。每當爸爸在廚房中忙碌起來,那股濃烈的香氣便滲透到整個屋子。羊肉的鮮美與大蔥的爽口交織在一起,在王致和紅腐乳的調和之下更顯濃厚醇香,仿佛是時光的定格。那個時候,家是溫暖的港灣,味蕾是懵懂的探險家,而“老味道”是最美妙的旋律。在這獨特的香氛中,小時候的我成為了家庭美食的忠實品味者。這種美好的味覺記憶,成為了我成長路上最珍貴的一部分,每一次回味,都是一次溫馨的時光旅行。
長大后,漫步在這座城市的夜市,我發現了一種令人陶醉的美味——酸菜白肉蘸紅腐乳汁。那撲鼻而來的香醇氣息仿佛能喚醒心靈深處的每一片味蕾,讓人回味無窮。在夜幕降臨的霓虹燈下,與朋友們圍坐在小攤前,一盤熱氣騰騰的酸菜白肉,搭配著王致和紅腐乳醬汁,成了城市夜晚最美妙的一抹風景。
每一種“老味道”都是一座城市的記憶,是歷史的沉淀,是文化的傳承。在這些美食背后,是無數普通人的辛勤努力和心血付出。品味這些“老味道”,仿佛在穿越時光隧道,與歷史對話,與文化共鳴。城市的老文化,如同一本沉甸甸的古籍,讓人百讀不厭。古老的建筑、傳統的手藝、悠久的歷史,構成了這座城市獨有的底蘊。而在這些老文化中,那些細膩的味道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茶館里的香茗、古書店中的紙香、老街巷弄里的炊煙,都是城市的靈魂,也是“老味道”的一種表達。
“回憶”這道菜,不僅僅是味覺的享受,更是心靈的慰藉。在品味“老味道”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漸漸明了生活的真諦。時間在流逝,城市在演變,但那些深深刻在心底的“老味道”卻是永恒的。或許,“回憶”這道菜,每個人口中的味道都不盡相同,但它都是我們共同的情感紐帶。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讓我們抽時間,回味一下那些屬于自己的“老味道”,讓心靈在這一抹懷舊的滋味中得到寧靜與慰藉。因為,“回憶”這道菜,永遠都是最美好的味道。
飄滿花香的老槐樹
每當遇到路旁的槐樹,聞著淡淡的槐花香,我的記憶就會被定格到那個叫“童年”的地方,不是自己太懷舊,而是它在心中的分量實在太重。
我的童年中總會有三個快樂的身影以及校園和老槐樹。校園里的老槐樹真的會唱歌,只要它枝丫上的喇叭響出動人的音樂,我們就快樂得像一只只燕子在操場上飛來飛去。玩累了,我們就在老槐樹下躺下來,望著雪白色的槐花說著悄悄話。風一吹,槐花恰好落在身旁,把它放入口中,甜絲絲的味道伴著花香鐫刻在了心里。
后來學校搬遷,離我們很遠很遠,我們真的像是離巢的小鳥沒有了家。我們還是會一起上學,一起回家,只是再也沒有了那種歸屬感和依賴感。在不上學的時候,我們還是會回到老槐樹身邊,三個人把它抱住,跟它說:“想在這待一輩子,不想離開它,這才是我們的家。”就這樣跟它說許多話。或許老槐樹真的老了,聽了我們的悄悄話,回答不動了。那時,黃昏微細的光總會透過稀疏的葉子斜斜地照進來,把我們的影子照得好長好長。三個執呦而又不可理喻的影子排列在老槐樹下,先是一片,再是一條線,最后一點,慢慢和老槐樹一起消失不見。是,消失不見了,連同三個快樂的小身影,學校和老槐樹。
再后來,學校也拆了,老槐樹也在我們放學的某個黃昏倒下了。等我們再來看他的時候,只剩下一個好大的樹樁,沒有我們的保護,它沒落得像個受傷的父親。我們摸著它的紋路,看著曾經的家,沒有哭,就是一直蹲在它的旁邊,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只是我們連同老槐樹的影子再也不會拉得很長很長了……
最后我們一直很默契地都沒有提過那個黃昏,三個人慢慢長大,離開家鄉,有了各自的生活,老槐樹成為了我們記憶中最柔軟的存在。我會給孩子講我的“純真年代”和老槐樹的故事,直到7 歲的孩子在我生日那天,畫了一幅畫,畫面中的老槐樹和我印象中的樣子漸漸重合。我忽然釋然了,老槐樹一直都在,從未離開,它一直在默默守護著它所愛的人們。
老屋的甜葡萄
葡萄是最常見的水果之一,一顆顆飽滿的紫色珍珠入口,留給唇齒間滿是酸甜,不禁讓我回想起兒時老屋院子里種的那棵葡萄樹,雖然它的顆粒相對較小,但這并不影響它給我留下美好的記憶。
葡萄樹應該是哥哥種的,那時候初中的課程中有一門是果樹栽培,聽母親說哥哥不知道從哪里弄來的葡萄枝埋在了地上,具體過程已經模糊不清楚了,只記得過了一個冬天以后,幾顆小樹發起了綠芽,大家都很興奮。
前兩年葡萄樹基本沒結果子,一味地在長枝蔓。漸漸地,一人多高的木架已經滿足不了葡萄樹的需求,只得將木架搭到廂房的屋檐上,滿架的葉子郁郁蔥蔥。不知道是哪一年的夏天,架子下的葡萄樹,開始結出一串串的葡萄了,從小小的青豆大小,一直盯著它長到成熟,每一顆都認識得那么清楚。我和鄰居家的孩子每天饞饞地盯著,紅一顆吃一顆,到最后甚至稍有點紅色,就開始摘下來吃了,酸酸的,甜甜的,完全不顧樹下隨時爬出來的青蟲。以至于真正到了葡萄成熟的季節,長在低處的葡萄早就被我們吃光了。
每每看到饞嘴的我們,母親總會說上一句,“等到熟了再吃呀,一個一個的小饞貓。”我和鄰居小朋友笑嘻嘻地,把手中的幾粒葡萄,塞到母親嘴里說,“已經熟啦,很甜呦”。母親就會開心地和我們一起笑。
葡萄樹雖然是哥哥種的,經營打理的事基本都是由母親來做。待到秋天葡萄樹的果實摘盡,落葉入泥后,如果不埋到地下,是熬不過冬天的。每次掩埋葡萄樹,母親總是把全家人動員起來。父親負責拆葡萄架,姐姐和我負責打下手,挖土坑的重活交給了哥哥,而母親則負責最精細的部分,修剪葡萄樹。葡萄架和土坑隨著葡萄樹的日漸長大,也逐漸變大起來,爸爸和哥哥也越來越辛苦。當然最辛苦的,還是母親。母親每次先把小枝杈剪掉,再把雜亂無章的樹枝用草繩捋順綁好后彎成一個弧形,到后來粗壯的樹杈母親一個人已經按不住了,這時候我們幾個孩子就一起按住樹枝,待母親用草繩綁好后,大家齊心協力將葡萄樹塞到土坑內,父親和哥哥就開始埋土。一切完成后,母親總會叮囑我們說輕輕踩幾下,不要太實,來年還是要長葡萄的。
母親的溫柔體貼滋潤了我整個童年。隨著年紀的不斷增長,老屋葡萄樹上那一串串葡萄的甜味留在了記憶中。我懷念盛夏暖陽里的紅綠相間,更懷念在老屋等候葡萄熟透的日子。葡萄酸酸甜甜,一顆挨著一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