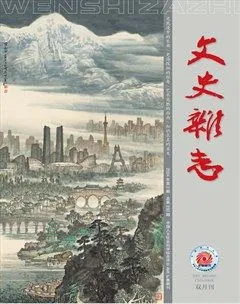魯迅小說《藥》中的“康大叔”與“黑的人”
唐雨
摘 要:魯迅小說《藥》中“康大叔”與“黑的人”并非同一人。前者屬于魯迅所說“愚弱的國民”“示眾的材料和看客”;后者是殺害革命者的職業劊子手。比較后者,以康大叔為代表的社會普通人對生命的冷漠、對革命的漠不關心,更令人寒心與不安。而這,正是魯迅要喚醒民眾,一起為革命理想共同奮斗的原因。
關鍵詞:人血饅頭;抽象與具象;改造國民精神
魯迅小說《藥》中的“康大叔”到底是誰?他與劊子手“黑的人”是否是同一人?這些疑問自上世紀60年代就有學者開始提出,并逐漸引起學界的關注和討論。最初學術界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大約從80年代開始,認為“黑的人”就是“康大叔”,“康大叔”就是“黑的人”的觀點逐漸占據主流地位,此后的部分教科書和教師用書甚至直接將二人等同混用,以劊子手的名號來代指“康大叔”,似乎這一問題已經解決、已下定論。筆者重新思考“康大叔”與“黑的人”二者間的關系,以確定“康大叔”與“黑的人”不是同一人為起點,來探究魯迅《藥》的寫作方法和思想深度,以及小說的多重主題和社會意義。
一、“康大叔”是不是“黑的人”
(一)認為二者是同一人
許多學者曾就“康大叔”是不是“黑的人”這一問題展開討論,并在上世紀80年代愈演愈烈,但是似乎“康大叔”就是“黑的人”這一研究觀點最后占據上風。例如學者陳德滋1985年在《語文教學與研究》中發表的《〈藥〉中“黑的人”就是“康大叔”》,葉閏桐于1991年在《上海魯迅研究》中發表的《我認為康大叔就是劊子手》等等文章,都一致認為“康大叔”就是“黑的人”,就是殺害夏瑜的劊子手。
后來的部分教科書與教師用書也承襲了這一觀點。人教社《語文第四冊教師教學用書》2001年版說,在肖像描寫部分,對康大叔的肖像描寫最為精彩:“渾身黑色的人”“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滿臉橫肉”“披一件玄色衣衫散著紐扣,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捆在腰間”。這本教參書講,只這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一個兇殘、蠻橫的劊子手形象。[1]人教社《語文》第四冊(2001年版)《藥》的課后“練習”第三題第2小題例舉:“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拴還躊躇著,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拴,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嘴里哼著說,“這老東西……”(練習題就此發問:上面兩段文字表現了康大叔什么樣的性格特征?)[2]顯然,2001年版的人教社教材與教參均認為“黑的人”與康大叔就是同一人。
(二)二者不是同一人的證據
那么“康大叔”究竟是不是“黑的人”呢?筆者認為小說中并沒有足夠證據表明康大叔和“黑的人”是一個人。恰恰相反,小說中卻有許多材料足以證明康大叔絕不是“黑的人”。“一個渾身黑色的人”是夏瑜被執行死刑時直接參與行刑的劊子手;而康大叔則是負責牽線搭橋,為“客戶”提供信息的中間介紹人。
一是從華老栓“買藥”、劊子手“賣藥”時的具體情景分析。原文中寫道:
“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一個渾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攤著;一只手卻撮著一個鮮紅的饅頭,那紅的還是一點一點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卻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那人便焦急起來,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還躊躇著;黑的人便搶過燈籠,一把扯下紙罩,裹了饅頭,塞與老栓,一手抓過洋錢,捏一捏,轉身去了。嘴里哼著說,“這老東西……。”[3]
從描寫的交易現場可以看出華老栓完全不認識劊子手。若真見到的是茶館里的常客康大叔,華老栓就不會表現出那么慌亂緊張的模樣——“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兩把刀,刺得老栓縮小了一半”,老栓“慌忙摸出洋錢,抖抖的想交給他,卻又不敢去接他的東西”。此時,老栓害怕的不是還在滴著溫熱的血的人血饅頭,而是害怕面前站著的“眼光正像兩把刀”的“渾身黑色的人”,害怕直視剛行刑完畢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老栓若是怕人血饅頭,就不會在回家路上像揣稀世珍寶似的揣著人血饅頭,“仿佛抱著一個十世單傳的嬰兒”。人血饅頭此刻于他而言,是救兒子性命的靈丹妙藥,是花費家中大半積蓄,且好不容易有門路“運氣好”才有機會買來的,此刻珍惜還來不及,又怎么會害怕呢?因此,華老栓唯一害怕的只會是面前這個“渾身黑色的人”。同時,還可以從劊子手稱呼老栓是“老東西”看出劊子手不認識老栓。如果兩人相互認識,并像在后文茶館中那樣熟識、常見,那么劊子手斷不會使用“老東西”這樣籠統且帶有侮辱性的稱呼,而應當順口稱呼他為“老栓”,也不會非常謹慎防備地“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二是從康大叔在茶館中的言語來分析。在第三節中,康大叔終于緩緩在茶館出場,現身第一句話便是“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首先,在這里康大叔直呼華老栓為“老栓”,說明二人相熟且關系不錯,因此前文中直呼華老栓“喂”“老東西”的劊子手不會是康大叔。其次,這句“老栓,就是運氣了你!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這里的“信息靈”是指康大叔知道犯人會在何時何地被處決。一名劊子手能夠輕易知道在何時何地殺人,這是職業分內之事,而只有行業外部人員通過特殊渠道層層打聽后,了解到尋常人無法知曉的信息,才能稱之為“信息靈”。所以,康大叔自稱的“信息靈”就不能說明他就是劊子手,而是指他有渠道打聽消息。在買賣“藥”的交易中,康大叔實際上是起到了牽線搭橋的中介作用——介紹買賣雙方,即老栓與劊子手建立起生意關系。因為康大叔提前知道夏瑜在后半夜就會被處決,華老栓不出意外現在肯定已順利拿到人血饅頭,所以才會一進門就高聲問“吃了么?好了么?”
并且,當花白胡子低聲下氣地向康大叔打聽夏瑜時,康大叔回應道:“……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連剝下來的衣服,都給管牢的紅眼睛阿義拿去了。——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康大叔如果就是殺害夏瑜的劊子手,那么他才在天亮前賺取了華老栓滿滿當當的一包洋錢,又怎能當著老栓的面高聲抱怨說自己“一點沒有得到好處”呢?唯一的解釋就是“康大叔”不是那個劊子手,沒有利用夏瑜的血賺錢,所以他才會認為夏瑜的可用價值全被華老栓、夏三爺和紅眼睛阿義占去了。
三是從康大叔與劊子手的外在形象分析。康大叔身著“玄色布衫”,而劊子手也是身穿黑色衣服。這身“黑色衣服”也就常常成為人們把康大叔認同為劊子手的“鐵證據”。但只要對劊子手的“黑衣”服飾加以分析,就能發現僅從衣帽看是不對的。
劊子手在大清是官方職業,其衣著打扮有著嚴格要求。影視劇中,古代劊子手也大都身著黑衣,可以說“黑衣”是劊子手們的職業制服。同時,《藥》也描寫了行刑前為防止夏瑜的“同黨”劫法場而執行警戒的“兵”的裝束:“又見幾個兵,在那邊走動;衣服前后的一個大白圓圈,遠地里也看得清楚,走過面前的,并且看出號衣上暗紅色的鑲邊。”可見清朝的官方人員在工作時著裝都是統一規整的。由此可以表明,《藥》中劊子手身著“黑衣”是其身份的代表、職業的裝束。而康大叔出場的外貌形象,則更像是社會上成天無所事事的地痞流氓、小混混。其隨意不講究的穿著打扮(雖也著玄色布衫),說明康大叔不是行刑者,不是“黑的人”。
二、區分二人的意義
(一)豐富看客的身份類型
確定康大叔不是劊子手“黑的人”之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康大叔是誰?他的身份信息、社會地位如何?
“包好,包好!這樣的趁熱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么癆病都包好!”[4]康大叔一點不在乎直說華小栓得“癆病”會讓華大媽心生不滿,更是加大了音量高聲大叫地“嚷”,“嚷得里面睡著的小栓也合伙咳嗽起來”,說明他并不是因為關心病人真心地想要為其治病而積極詢問病情和藥效。他大聲嚷嚷只是在向茶館大眾炫耀自己能耐通天,炫耀自己“信息靈”。“康大叔見眾人都聳起耳朵聽他,便格外高興,橫肉塊塊綻放,越發大聲……”在眾人崇拜渴望的眼神中,康大叔的虛榮心獲得了極大的滿足。
“我可是這一回一點沒有得到好處”,康大叔此話是在旁敲側擊向華老栓一家邀功要賞。從他標榜“要不是我信息靈”的話來看,他認為自己在買賣藥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華老栓一家應該將自己當做救命恩人一般地重金酬謝自己。這突顯出他的貪得無厭、欲壑難填。
花白胡子向康大叔問話時低聲下氣,并且“康大叔顯出看不上他的樣子”;華老栓面對康大叔時臉上堆著笑,恭恭敬敬,華大媽也“很感激的謝他”;牢頭阿義被駝背五少爺敬稱為“義哥”,但康大叔要么直呼其名,要么叫綽號“紅眼睛”。從茶館眾人對康大叔的言語和態度,可見其地位遠在牢頭之上。他在茶館中的話語、神態和聲調,無不顯露出他的高人一等、目中無人、蠻橫粗野。
不同于為給兒子治病耗盡家財的華家,也不同于駝背、花白胡子、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等閑談的顧客,康大叔是主動向這些底層看客散播消息的上一級,無論是華家的人血饅頭,還是夏瑜被殺的事跡,都是通過康大叔一人所言才滿座皆知。所以康大叔在這些底層看客的心中是身份尊貴的權勢者,是掌握話語權的核心人物。
小小的茶館將人群分為了三六九等。這些不同階級、不同立場的人物,映射出整個社會的普遍狀態或心態,大大豐富了魯迅小說中的看客形象,讓這些旁觀者不再是一群無名無姓,沒有清晰五官的模糊背景。通過多階層的展示,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集合,讓讀者得知整個社會從上到下,都已經病入膏肓、無藥可救。看客們面對國之同胞受難,不會想著同仇敵愾;面對身旁鄰居受苦,不會想著共渡難關。他們表現出來的只有對生命的毫無敬畏和對弱者的毫無悲憫。
(二)“抽象”與“具象”完美結合
“要讓接受者從小說的具體敘述中感受到超越性的意味,要讓接受者從人物形象的言行舉止中領會到普遍性的旨趣,是一件難度極大的事。作品具有超越性的意味,具有普遍性的意旨,是小說家共同的夢想。”[5]但要實現這一點,卻極其不易,這關乎許多方面的因素。諸多因素中,特別重要的一點就是在一字一句的敘述中,把“抽象”與“具象”完美地結合在一起。
魯迅首次提出“看客”這一概念,可追溯到《吶喊》的自序部分。在文中,他指出“無論國民體格如何健全茁壯,然而一旦精神愚弱,便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由是,“看客”一詞正式登上現代文學的歷史舞臺。毫無疑問,“看客”就是魯迅小說中能夠把“抽象”與“具象”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能夠同時囊括普遍性和超越性的一個群體。
在對看客群體的塑造上,魯迅給予讀者的信息少之又少:或無名無姓,或沒有身份信息,更有甚者模糊得只剩下若隱若現的輪廓。然而,筆者以為正是他有意地模糊淡化甚至抹去了每一個具體、確切的看客個體,從而更能使讀者聚焦于看客的整體形象,進而從他們身上提煉出一個時代的縮影,集中反映出他們性格的弊病與弱點,以達到剖析因果、謀求出路之效。
若是清楚設定了康大叔就是“黑的人”,其職業就是劊子手,那么他所代表的社會群體范圍將會大幅縮減。魯迅為了最大限度地讓康大叔這個看客的精神具有普遍性,便盡量控制對他的描繪。魯迅刻意不賦予康大叔任何明確的社會身份;即使名字,也只給他一個明確的姓氏,卻又是沒有意義的。假若康大叔有過多的連貫性動作,讓康大叔與具體的買藥故事情節糾纏太多,那么這個人物形象的內涵便一開始就“具體化”了,他的精神便會具體化,便會讓人感到只在特定情境中才具有意義。
但是,僅有抽象化的敘述,容易使作品枯燥乏味,容易讓人物概念化、公式化、刻板化,從而讓人難以卒讀。而魯迅十分自然巧妙地把抽象與具象結合在一起,以一個又一個鮮活、靈動的具體細節來裝點、填充著抽象的人物符號。
在這篇《藥》中,魯迅以十分精細的筆法,把那些往往為常人所忽略的地方加以精雕細琢的敘述:“突然闖進了一個滿臉橫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著紐扣,用很寬的玄色腰帶,胡亂捆在腰間。剛進門,便對華老栓嚷道:……。”短短幾句就將康大叔的衣著、神情、性格等向讀者交代清楚,讓讀者在腦海中能粗粗勾勒出一個五大三粗、不修邊幅、趾高氣揚、蠻橫粗鄙的混混形象,于細微處讀出諸多信息。這些生動的神情、言行大大增強了人物的立體性,從而讓讀者對事件的真實性深信不疑,不再認為這是一個被虛構出的脫離社會實際的公式化符號。唯有身份信息模糊不明,但又兼具真實生動的看客形象,才能讓讀者自然地聯想和代入到彼時社會上的諸多人物群體上,從而達到以小見大、嘗鼎一臠的良好效果。
(三)深化和拓展小說主題
1.改造國民精神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明自己為何棄醫從文:“因為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務,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6]從魯迅的原話我們可以看出,這位肉體健壯的康大叔,卻是精神的靡弱者,從而顯出強烈的諷刺和批判意義。康大叔正是魯迅筆下的那種“看客”。
如果康大叔只是朝廷的爪牙、行刑的劊子手,是一種傳統意義上本就冷酷無情殘暴的代名詞,那就無法符合魯迅所提出的“愚弱的國民”“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的定義。只有讓康大叔作為普通群眾的“領頭羊”,作為行刑者的幫兇,才能更好展現出“示眾”的含義。這樣的“看客”代表也才能更好地揭示《藥》的深刻主題——“描寫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或者因群眾的愚昧而帶來的革命者的悲哀;更直截說,革命者為愚昧的群眾奮斗而犧牲了,愚昧的群眾并不知道這犧牲為的是誰,卻還要因了愚昧的見解,以為這犧牲可以享用,增加群眾中的某一私人的福利。”[7]這一特殊看客形象的存在,進一步深化了“群眾的愚昧和革命者的悲哀”的主題,使這部小說呈現出復雜的象征意義和強烈的諷刺意義,進而鮮明地表達了魯迅對于改造國民精神的愿望。
2.強調生命價值
過去對于《藥》這部小說主題的解讀主要集中在“反思說”和“啟蒙說”,即要么認為它批判了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反映出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和脫離群眾等缺點;要么認為《藥》批判了精神腐朽、愚昧麻木、不理解革命先鋒的落后國民。但說到底,這兩種解讀思路的出發點和著眼點還是落在“革命”上面,是從“革命”的角度體驗魯迅小說的,是從外部分析、研究魯迅小說的客觀意義,而忽視了作為創作主體的魯迅自身對人類生命存在的感受。
康大叔作為全篇小說的重點人物,直到第三節才緩緩出場,但他一出現便顯示出身份地位的不一般。不同于茶館里的其他客人,康大叔身居高位,是在“包好,包好”的喊叫中出場的。他的喊叫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藥,二是藥源。關于藥,康大叔明顯帶有炫耀的色彩。“包好,包好!……什么癆病都包好!”“你運氣,要不是我信息靈……”“這是包好!這是與眾不同的。”從始至終康大叔都在通過夸大藥的功效來顯示自己的非凡本事;至于這藥能否真的能治好華小栓的病以及華小栓病情如何,他則全然不顧、漠不關心。
在茶館中占據主體地位的華老栓和康大叔構成了病人華小栓生命環境中的兩極——極度關心與極度冷漠。沉默忙碌的華老栓與聒噪喧嘩的康大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華老栓為兒子病情擔憂得“兩個眼眶,都圍著一圈黑線”;而康大叔只專注于吹噓藥的功效。這是一個極具反諷意義的敘事結構。在這個反諷結構中,病人的生死退居于末席,而“藥”這個主體意象被推至首位。人們關心的是藥,而不是吃藥的人;關心的是藥的來源,而不是吃藥的結果。
但人們對于藥的來源,即夏瑜被砍頭的關注仍然只是聽個熱鬧。花白胡子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事”,卻在聽到夏瑜被親人出賣,被牢頭欺辱后卻說“打了這種東西,有什么可憐哩”“瘋話,簡直是發了瘋了”。在他們無聊空虛的生活里,在這樣冷漠又虛無的生存環境中,生命是無關大體的,生命在人們的生活中的重量占比不過是茶余飯后的一點調味劑,是可有可無的,是被漠視甚至被蔑視嘲笑的。生存的冷漠與生命的重量構成極具張力的反諷結構,其中的荒誕和可悲由此而生。
作者如果安排康大叔的職業就是劊子手,那么他每天殺人已經司空見慣,則無所謂什么麻木或冷漠了。比較劊子手與尋常普通人,顯然是普通人對生命漫不經心、視如草芥的態度更加令人膽戰心驚、毛骨悚然,更能激發讀者的憤慨和反思。作者只有將康大叔歸入單純的百姓群體中,與華老栓、花白胡子、駝背五少爺等無異,才會更加顯出這些麻木冷漠的、殘忍冷血的人群實為社會大多數這一時代的悲哀。這樣的大多數只關心各自眼前的利益:華老栓只關心自己兒子的命,不關心人血饅頭的血是哪來的;康大叔只關心自己沒有撈到好處,不關心人血饅頭是否有效;大眾只關心今日“新聞”,不關心革命者為何而死。正是在這樣的集體無意識狀態下,“大清是我們大家的”——夏瑜拼死留下的遺言才不會在大眾心目中泛起哪怕是極微小的波瀾。社會的整體愚昧、麻木比之朝廷的瘋狂、劊子手的兇惡,顯然更令人感到可怕、寒心與不安,更能構成生命的反諷結構,產生巨大的時代的反諷張力。
3.擴大群眾范圍
作者在描寫康大叔時盡管極力刻畫其邋里邋遢、目空一切、高高在上、夸夸其談的混混形象,卻并沒有粗暴莽撞地將他直接劃分在革命的對立面,確立為社會的敵人,而仍然只在于揭示他作為群眾一方所受到的精神荼毒之深之重,說明他既是封建等級制度的受害者,又是助紂為虐的封建統治的維護者的情況。作者筆下的康大叔的致命缺點是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眼界狹隘,缺乏階級觀念和階級感情,但本質上并不是反革命分子。
歸根結底,康大叔與華老栓夫婦、夏四奶奶等人一樣,都是封建專制社會下被壓榨的底層民眾,只是被壓抑的境況和展現出的奴性程度不同罷了。魯迅從啟蒙主義角度出發,有意識擴大被啟蒙群眾的范圍,奉行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的原則,盡力團結和爭取一切底層民眾,其目的是使整個民族覺醒。唯有喚醒更多民眾,才能推翻清政權,完成民族革命的神圣使命。
推翻清朝暴虐統治是當時民族革命的直接目標。革命者向群眾呼號不要替清朝統治者賣命,要有民族骨氣、民族尊嚴、民族感情、民族自尊心。在夏瑜的心目中,民族革命大業是排在自己的生命之前的,是第一位的。他堅信“這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關在牢里還念念不忘民族的利益,將牢頭阿義當作爭取對象。在民族國家觀念尚未深入人心的時候,革命家走在時代前列的先進思想支撐著他們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完成革命偉業。這正是夏瑜成為革命家最為寶貴的個性,是革命家與一般國民最本質的區別。
阿義、康大叔、夏三爺等人由于他們自己“中毒”太深,故對革命家一味地痛罵和攻擊。誠如《阿Q正傳》里阿Q對革命“向來深惡而痛絕之”,他進了一次城,回到未莊,便向未莊人吹噓“咳,好看。殺革命黨。唉,好看好看,……”我們絕不能簡單憑據阿Q對革命“深惡痛絕”的態度和他說“殺革命黨好看好看”的麻木語言,就篤定他是漢民族的敵人。魯迅寫阿Q,寫康大叔,都是將他們視為群眾,從啟蒙主義角度出發,有意識擴大被啟蒙的群眾范圍,雖挖掘出國民的劣根性——鼠目寸光、見利忘義,喪失民族氣節和道德良心,但其根本目的還是落在啟蒙與救亡上,想要叫醒更多的人,從而一同啟蒙、一同拯救。
結語
康大叔是否是“黑的人”,是否是殺害夏瑜的行刑者,這并非是一個可以模糊和忽略的小問題。當我們將二人區分開來后,便能從這篇短小精悍的小說中,發現魯迅更多精細的寫作筆法和深邃的社會思考,從而對其文本和文學觀有進一步深入準確的認識和理解。
注釋:
[1]《語文第四冊教師教學用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50頁。
[2]《語文第四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第49頁。
[3][4][6]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頁,第468頁,第463—472頁。
[5]王彬彬:《趙太爺用哪只手打了阿Q一嘴巴——〈阿Q正傳〉片論》,《文藝爭鳴》2022年第2期。
[7]孫伏園:《魯迅先生二三事》,中國文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28頁。
作者:西華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