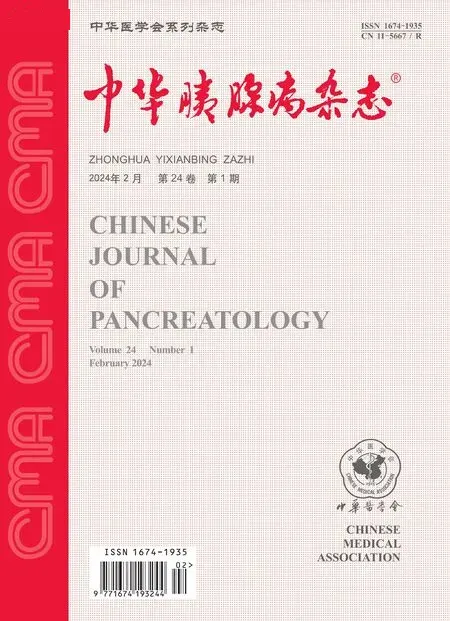急性胰腺炎有創(chuàng)治療相關(guān)腸瘺的臨床分析
閆夏曉 周婧雅 曹劍 徐強(qiáng) 韓顯林 張晟瑜 吳東
1中國醫(yī)學(xué)科學(xué)院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消化內(nèi)科,北京 100730;2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疑難重癥及罕見病國家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730;3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病案科,北京 100730;4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放射科,北京 100730;5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基本外科,北京 100730
AP發(fā)病率約為34/10萬,是世界范圍內(nèi)急診入院的首位消化疾病,且有逐年遞增的趨勢[1]。約20% AP患者會出現(xiàn)胰腺和(或)胰周壞死,可繼發(fā)感染及其他全身并發(fā)癥,是病程后期出現(xiàn)第二個死亡高峰的重要原因,也是有創(chuàng)干預(yù)的主要指征[2]。消化道瘺是AP病程后期的嚴(yán)重并發(fā)癥之一,可能繼發(fā)腹腔內(nèi)出血、腹腔感染等,進(jìn)一步導(dǎo)致病情惡化,延長患者住院時間并增加治療費用,增加疾病后期死亡風(fēng)險[3-4]。AP相關(guān)的消化道瘺可累及胃、腸道、膽囊等空腔臟器,發(fā)生率為12%~18%[5-9]。其中腸瘺的發(fā)生與AP的自然病程發(fā)展相關(guān),也與手術(shù)中過度清創(chuàng)和引流管放置等有創(chuàng)操作密切相關(guān)[4,10-15]。目前,AP的有創(chuàng)干預(yù)策略包括多種引流和清創(chuàng)方式的序貫或聯(lián)合使用,其中延期的升階梯(step-up)多元化微創(chuàng)治療已成為主流模式,并逐漸取代手術(shù)清創(chuàng)[16-19]。有創(chuàng)干預(yù)尤其是經(jīng)皮穿刺引流和內(nèi)鏡透壁引流對AP并發(fā)腸瘺影響的研究較少,亦尚未形成管理共識。因此,本研究回顧性分析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行有創(chuàng)干預(yù)的AP患者,旨在分析有創(chuàng)干預(yù)相關(guān)腸瘺患者的臨床特征。
資料和方法
一、研究對象和分組
收集2003年1月至2022年12月間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177例行有創(chuàng)干預(yù)的MSAP和SAP患者的臨床資料。根據(jù)有創(chuàng)干預(yù)術(shù)中或術(shù)后有無相關(guān)性腸瘺發(fā)生,將患者分為腸瘺組和無腸瘺組。納入標(biāo)準(zhǔn):(1)MSAP或SAP診斷符合修訂版亞特蘭大分級標(biāo)準(zhǔn)[20];(2)均行針對胰周并發(fā)癥的有創(chuàng)干預(yù),包括經(jīng)皮穿刺引流、內(nèi)鏡下透壁引流或清創(chuàng)、外科手術(shù)清創(chuàng)等。排除無胰腺及胰周病變的腹部影像學(xué)資料者。有創(chuàng)干預(yù)指征:臨床懷疑或證實的感染、持續(xù)存在的癥狀、胰管中斷綜合征伴相關(guān)癥狀、腹腔間隔室綜合征、持續(xù)的急性出血、腸壞死、胰胸瘺、胰性腹水等。本研究經(jīng)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zhǔn)(批準(zhǔn)號I-22PJ553)。
二、腸瘺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和治療
腸瘺的診斷符合以下5項之一:(1)經(jīng)皮引流管引流出或清創(chuàng)手術(shù)切口溢出消化液、食糜或糞便等胃腸內(nèi)容物;(2)經(jīng)竇道造影顯示竇道與消化道相通;(3)口服或經(jīng)胃管注入亞甲藍(lán),可見亞甲藍(lán)自創(chuàng)口或竇道溢出;(4)胃腸道造影或經(jīng)胃腸鏡等內(nèi)鏡檢查明確可見瘺口部位;(5)手術(shù)中明確有胃腸壁全層穿孔。不包括用于治療的內(nèi)鏡下透壁引流或假性囊腫消化道吻合術(shù)后產(chǎn)生的內(nèi)引流。根據(jù)臨床實際,不對腸瘺和穿孔進(jìn)行嚴(yán)格區(qū)分。
腸瘺的治療包括保守治療、微創(chuàng)治療和手術(shù)等方式的單獨或序貫使用。保守治療包括繼續(xù)并加強(qiáng)已有的沖洗引流、抗感染、腸內(nèi)外營養(yǎng)支持等,微創(chuàng)治療包括經(jīng)皮引流和內(nèi)鏡下治療等,手術(shù)治療包括瘺口修補術(shù)或近端造瘺術(shù)等。
三、觀察指標(biāo)
記錄患者的年齡、性別、病因、SIRS、器官功能衰竭、修訂版亞特蘭大分級、BISAP評分、Balthazar CT分級、局部并發(fā)癥胰外受累情況、局部并發(fā)癥繼發(fā)感染情況、干預(yù)指征、干預(yù)時機(jī)、干預(yù)策略、住院時長、重癥監(jiān)護(hù)時長和結(jié)局。其中局部并發(fā)癥繼發(fā)感染定義為有引流物病原學(xué)培養(yǎng)陽性結(jié)果。腸瘺組患者記錄腸瘺的發(fā)現(xiàn)時間、臨床表現(xiàn)、診斷方式、治療和結(jié)局。
四、統(tǒng)計學(xué)處理
采用SPSS 23.0軟件進(jìn)行數(shù)據(jù)分析。符合正態(tài)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非正態(tài)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shù)(范圍)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或Mann-Whitney檢驗;計數(shù)資料以例(%)表示,組間比較采用Fisher確切概率法或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
結(jié) 果
一、兩組患者臨床特征比較
177例患者中MSAP患者83例,SAP患者94例。其中男性112例,女性65例,中位年齡43歲。有創(chuàng)干預(yù)指征中90例(50.8%)為局部并發(fā)癥合并可疑感染征象,58例(32.8%)為持續(xù)存在的癥狀,19例(10.7%)為難以自行緩解的腹腔積液及腹內(nèi)壓升高。共21例(11.9%)于有創(chuàng)干預(yù)術(shù)中或術(shù)后發(fā)現(xiàn)腸瘺,其中8例于經(jīng)皮穿刺術(shù)中或術(shù)后,13例于外科手術(shù)術(shù)中或術(shù)后。51例行內(nèi)鏡下引流或內(nèi)鏡下清創(chuàng),無內(nèi)鏡操作后腸瘺發(fā)生。72例患者在有創(chuàng)干預(yù)后引流物病原培養(yǎng)陽性,明確存在繼發(fā)感染,其中15例(20.8%)發(fā)生腸瘺;105例引流物病原培養(yǎng)陰性患者中,6例(5.7%)發(fā)生腸瘺,腸瘺發(fā)生率差異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χ2=9.34,P=0.002)。
與無腸瘺組比較,腸瘺組患者的性別、病因、器官功能衰竭情況、亞特蘭大分級、CT分級、干預(yù)時機(jī)等方面差異均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表1)。腸瘺組患者的中位年齡較小(36歲比45歲,P=0.014),發(fā)生SIRS(95.2%比59.6%,P=0.001)、局部并發(fā)癥胰外受累(100.0%比67.3%,P=0.002)和繼發(fā)感染(71.4%比36.5%,P=0.002)的比例更高。所有腸瘺患者均存在影像學(xué)或術(shù)中所見的胰周及腹腔、腹膜后受累(圖1)。自起病至發(fā)現(xiàn)腸瘺的中位時間為84 d,平均91 d;首次及末次有創(chuàng)干預(yù)至發(fā)現(xiàn)腸瘺的中位時間分別為65 d和10 d。腸瘺組中位住院時間(71 d比40 d,P=0.002)和重癥監(jiān)護(hù)時間(8 d比0,P=0.016)更長,而住院病死率差異無統(tǒng)計學(xué)意義。腸瘺組1例患者在腸瘺控制穩(wěn)定后轉(zhuǎn)院,3例放棄治療出院,1例因降結(jié)腸瘺繼發(fā)的腹腔感染和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

圖1 1例急性胰腺炎合并腸瘺的影像學(xué)表現(xiàn)。起病第77天,十二指腸水平段周圍及腸系膜區(qū)、右側(cè)腹膜后、右側(cè)結(jié)腸旁溝多發(fā)滲出及包裹性積液,向下延伸至右側(cè)盆腔(1A),升結(jié)腸多發(fā)腸壁增厚水腫(1B)。起病第83天,經(jīng)引流管造影升結(jié)腸顯影(1C)

表1 腸瘺組和無腸瘺組患者的臨床特征比較
二、腸瘺患者的診斷及治療
腸瘺發(fā)生部位主要為結(jié)腸(13例,61.9%)和十二指腸(6例,28.6%),具體包括十二指腸降部6例、空腸1例、升結(jié)腸4例、橫結(jié)腸1例、降結(jié)腸3例,1例同時出現(xiàn)升結(jié)腸和降結(jié)腸腸瘺,5例未明確具體部位,根據(jù)臨床表現(xiàn)推斷為小腸瘺1例和結(jié)腸瘺4例。
5例次為造影或清創(chuàng)術(shù)中偶然發(fā)現(xiàn),7例次表現(xiàn)為體溫升高,11例次出現(xiàn)引流物性質(zhì)改變,包括引流量增多和(或)引流物中可疑腸內(nèi)容物,4例次合并腹腔內(nèi)或消化道出血。所有患者均存在影像學(xué)或術(shù)中所見的胰周及腹腔、腹膜后受累,腸瘺確診主要通過經(jīng)引流管造影(11例)或消化道造影(5例)。
5例患者在發(fā)現(xiàn)腸瘺后直接行瘺口修補術(shù)或空腸造口術(shù);16例(76.2%)首選非手術(shù)治療,因治療效果不佳,其中4例放置新的經(jīng)皮穿刺引流管引流,5例升級為手術(shù)治療。13例結(jié)腸瘺患者中,9例首選非手術(shù)治療,4例首選瘺口修補或近端造口術(shù);8例非結(jié)腸瘺患者中,7例首選非手術(shù)治療,僅1例在術(shù)中發(fā)現(xiàn)腸瘺時即進(jìn)行修補。16例患者接受腸內(nèi)營養(yǎng),其中5例未因腸瘺停用腸內(nèi)營養(yǎng),11例發(fā)生腸瘺后曾停用腸內(nèi)營養(yǎng)(中位時長24 d)而后恢復(fù),均好轉(zhuǎn)出院。
討 論
AP的嚴(yán)重程度在早期階段主要取決于全身炎癥反應(yīng)和器官功能衰竭;在晚期階段,胰周并發(fā)癥的發(fā)展及可能繼發(fā)的感染,使病程復(fù)雜化,此時通常需要多學(xué)科綜合管理,尤其是經(jīng)皮介入引流、內(nèi)鏡透壁引流或清創(chuàng)和外科清創(chuàng)等不同策略的合理應(yīng)用。局部并發(fā)癥的形成及有創(chuàng)干預(yù)本身帶來的醫(yī)源性損傷系A(chǔ)P患者并發(fā)腸瘺的危險因素,引流物性質(zhì)的改變常可提示腸瘺的存在,通過臨床表現(xiàn)和后續(xù)造影檢查可明確診斷。治療方面,多首選保守治療,但超過半數(shù)結(jié)腸瘺患者最終需要修補或近端造瘺。合并腸瘺患者所需的住院和重癥監(jiān)護(hù)時間更長。
本組有創(chuàng)干預(yù)的AP患者中,腸瘺的發(fā)生率為11.9%。既往關(guān)于消化道瘺的研究多選取壞死性胰腺炎或接受外科清創(chuàng)術(shù)的患者為研究人群,報道的發(fā)病率因研究人群和研究中心不同而異。在荷蘭胰腺研究組的觀察性研究中,消化道穿孔或瘺的發(fā)生率為16.0%[9]。國內(nèi)單中心研究報道的SAP患者中消化道瘺發(fā)生率為2.5%,壞死性胰腺炎患者中十二指腸瘺發(fā)生率為9.0%[20-21]。本研究納入的是病程中接受有創(chuàng)治療的AP患者,以“升階梯”的綜合微創(chuàng)治療為主,均為MSAP或SAP且合并有局部并發(fā)癥,其中40.7%(72/177)有病原學(xué)證實的局部感染。本研究結(jié)果顯示,腸瘺組較非腸瘺組的SIRS、胰周侵犯和繼發(fā)感染的發(fā)生率顯著增高。AP早期的全身炎癥反應(yīng)和晚期的局部炎癥反應(yīng)可能通過影響腸道血供導(dǎo)致腸道屏障的破壞[11];胰周積聚的液體或壞死物也可能直接壓迫腸壁組織和腸系膜血管或促進(jìn)血管內(nèi)血栓形成,加重腸壁的缺血、水腫和壞死,最終導(dǎo)致穿孔和瘺的發(fā)生[4,10,12]。此外,腸瘺相關(guān)危險因素還包括高CRP、低蛋白血癥、早期器官功能衰竭、腹腔間隔室綜合征、CT氣泡征、高CT嚴(yán)重程度評分等[6,9,22-25]。
本研究21例AP合并腸瘺患者中,胰周并發(fā)癥均累及甚廣,范圍可至腸系膜區(qū)、經(jīng)結(jié)腸旁溝至盆腔或經(jīng)腹膜后至腰大肌間隙,多為感染性壞死或壞死物積聚。與既往研究報道類似,本組腸瘺好發(fā)部位為結(jié)腸和十二指腸,空腸瘺僅1例。解剖上,胰腺與十二指腸降部、水平部、橫結(jié)腸和結(jié)腸脾曲等部位毗鄰,胰周滲出或壞死亦可通過結(jié)腸旁溝向盆腔蔓延轉(zhuǎn)移;且小腸的血供豐富,而結(jié)腸的血供側(cè)支循環(huán)有限,更易受到AP病程中休克相關(guān)低灌注的影響。以上原因,可能解釋了腸瘺的好發(fā)部位。
由于解剖學(xué)因素和病理生理學(xué)特點,存在有創(chuàng)干預(yù)指征的AP患者與合并腸瘺的潛在風(fēng)險人群高度重合。局部并發(fā)癥的處理對腸瘺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既可改善腸壁周圍炎癥環(huán)境從而降低腸瘺的發(fā)生,又可因有創(chuàng)干預(yù)帶來醫(yī)源性損傷直接導(dǎo)致腸瘺的發(fā)生。van Santvoort等[14]和Boxhoorn等[15]研究將消化道穿孔或瘺作為干預(yù)后并發(fā)癥,發(fā)生率分別為18.2%和8.7%。充分徹底的清創(chuàng)和引流管的放置可能對腸壁薄弱處及其血供產(chǎn)生影響,并加速瘺的發(fā)生。本研究單純經(jīng)皮引流相關(guān)腸瘺中,62.5%為非結(jié)腸瘺;而接受手術(shù)清創(chuàng)的腸瘺中,結(jié)腸瘺占比更高(76.9%),這一差異可能與AP的嚴(yán)重程度相關(guān)。局限在胰頭周圍的病灶首先累及同為腹膜后器官的十二指腸,往往可通過引流控制;而嚴(yán)重廣泛的胰腺外壞死更易累及結(jié)腸,單純引流效果欠佳,多需升級為手術(shù)治療;此外,術(shù)中大范圍的清創(chuàng)對腸壁血供影響程度更大,可能造成感染播散,更易累及血供薄弱的結(jié)腸。因此,進(jìn)行有創(chuàng)干預(yù)過程中應(yīng)當(dāng)力求對腸壁鄰近壞死組織的充分處理,同時避免對腸壁的刺激,注意清創(chuàng)時對腸道血供的保護(hù)和引流管放置位置、角度和時長等。本研究未發(fā)現(xiàn)內(nèi)鏡治療后腸瘺的發(fā)生,與既往研究結(jié)果一致,支持內(nèi)鏡引流作為創(chuàng)傷更小、并發(fā)癥更少的治療方式,是AP有創(chuàng)治療的一線選擇這一觀點[18]。
本研究對AP并發(fā)腸瘺的處理也遵循“升階梯”原則。8例非結(jié)腸瘺患者,除1例術(shù)中發(fā)現(xiàn)十二指腸瘺進(jìn)行同期修補,其余均在接受保守治療后愈合。13例結(jié)腸瘺患者也多先接受保守治療(局部引流),因局部感染嚴(yán)重或合并有腹腔內(nèi)出血等情況,最終9例(69.2%)需要手術(shù)。因此,針對AP合并腸瘺的處理原則,均以局部引流、抗感染和腸內(nèi)或外營養(yǎng)支持等保守治療為主,必要時加強(qiáng)穿刺引流或外科手術(shù)。但本研究為單中心回顧性病例研究、樣本量相對有限,缺少長期隨訪信息,因此AP合并腸瘺的管理推薦仍需更大規(guī)模、前瞻性研究證據(jù)支持。
綜上所述,有創(chuàng)干預(yù)與AP合并腸瘺的發(fā)生、診斷和處理均密切關(guān)聯(lián)。從降低腸瘺風(fēng)險角度,有創(chuàng)干預(yù)應(yīng)盡量避免對腸壁的刺激;干預(yù)后應(yīng)關(guān)注引流情況,及時發(fā)現(xiàn)、處理潛在腸瘺,避免病程復(fù)雜化。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聲明無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xiàn)聲明閆夏曉:數(shù)據(jù)整理、統(tǒng)計學(xué)分析、論文撰寫;周婧雅、曹劍、徐強(qiáng)、韓顯林:數(shù)據(jù)整理、統(tǒng)計學(xué)分析、論文修改;張晟瑜、吳東:研究設(shè)計、論文修改、經(jīng)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