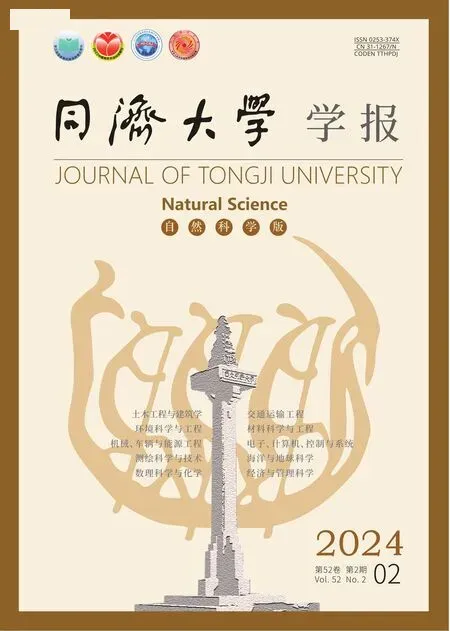基于位置服務數據的社區生活圈測度方法及影響因素分析
楊 辰, 辛 蕾, 馬東波, 賈姍姍, 陳 晨
(1. 同濟大學 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上海 200092;2. 上海同濟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 200092;3.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風景園林藝術學院,陜西 咸陽 712100;4. 上海社會科學院,上海 200020)
社區是居民日常活動的空間載體,也是國家治理和地方自治的實踐場所。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單位制向社區制轉型,城鄉社會的流動性和多元化程度不斷加強,以“居住區、居住小區”為邊界、以“千人指標” 為公共資源配置原則的規劃方法逐漸受到挑戰。源于日本的“社區生活圈”概念近年來受到中國學術界和規劃實踐領域的廣泛關注——自上海城市總體規劃(2017—2035)提出“15 min社區生活圈”以來,北京、廣州、杭州、成都、武漢、長沙、濟南、廈門、海口等城市也陸續啟動了本地的社區生活圈規劃。2018 年12 月,新版《城市居住區規劃設計標準(GB50180—2018)》正式生效,標志著我國的社區規劃開始由居住區模式轉變為生活圈模式。
然而,當前大部分城市的社區生活圈研究和建設重點仍然是“在步行范圍內,完善社區居民的公共服務設施配套”[1],對于社區生活圈理論的關鍵問題——生活圈的邊界劃分及其影響因素缺乏深入研究。現有的社區生活圈邊界劃分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種:行政或控規單元邊界、依據設施服務半徑及可達性、居民的活動行為。
規劃管理者認為,當前我國的社區建設仍處于培育階段,政府自上而下的引導應發揮主要作用,社區生活圈的劃定也應采用街道轄區等行政邊界為宜[2]。這一看法也得到了學者的呼應,比如袁家冬等[3]認為,社區生活圈是一種功能性的城市地域系統,以最小區劃單位(街道)為界統計上更為方便;柴彥威[4]則指出了另一種行政單元的變體——中國的單位大院,實際上也是一種典型的社區生活圈,“其工作單位和附屬的居住、生活福利設施空間就是基礎生活圈的邊界”。雖然從建設和管理的角度,把行政轄區或控規單元作為社區生活圈邊界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這個邊界與居民實際日常活動范圍之間的誤差相當大[5-6],這種誤差會在公服設施配套和社區治理方面造成嚴重的錯配[7]。
利用“服務半徑”“可達性”的概念來劃定社區生活圈邊界是城市規劃常用的手段。除了圍繞公服設施劃定300 m或500 m服務半徑的方法,規劃師也嘗試從居民的角度,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等時出行對居民活動的可達范圍進行測度[8];以及利用GIS 路徑分析工具,將小區外800 m路網距離(而不是歐式距離)范圍作為社區生活圈邊界,并對其中的公服設施數量和種類進行評價[9]。近年來由于多源數據的開放,規劃師們又開始構建基于興趣點(point of interest,POI)數據的生活圈服務半徑,如采用“小區到各類設施最近距離的最大值”作為社區生活圈的服務半徑[10]。
基于居民行為的社區生活圈邊界劃定更加受到學者的關注,因為從科學的角度,這是唯一真正接近生活圈本意的方法。這類研究大多依賴對特定社區居民出行的全球定位系統(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GPS)調查,例如采用標準置信橢圓方法計算GPS 數據邊界,得出居民日常活動空間范圍[11];結合GPS 數據與活動日志數據,采用alpha-shape 方法測度社區生活圈邊界[5];采用最小凸多邊形(convex Hull)方法發現社區居民日常活躍多集中在距離居住地400 m 半徑的扇形空間[12];采用結晶生長模型與核密度分析相結合,深入刻畫居民15 min生活圈及其內部結構[13]。還有學者關注特殊群體的社區生活圈邊界,如基于GPS 數據測算兒童在社區周邊的活動范圍[14];利用GPS 數據結合問卷調查,對老年人的社區生活圈進行空間識別,發現生活圈邊界具有不規則甚至飛地特征[6]。這些研究雖然對居民活動的真實軌跡進行了大量分析,也關注到了居民個體差異(比如老年人、兒童),但存在三個明顯不足:①GPS 調研成本高,樣本有限,難以描述社區大多數居民的活動規律,更缺乏對全市不同類型社區生活圈的全貌認識;②GPS 軌跡已經顯示居民的日常活動不受街道邊界限制,但大多數調研仍預先設定了一個研究單元(一般以“街道轄區”為界),通過觀察本單元居民的活動軌跡來劃定生活圈。實際上,不同精度的分析單元(街道、居委會、小區、單元樓)對生活圈邊界劃分有很大影響[15];③行為研究過于關注“行為”,對居民日常生活使用的、構成社區生活圈的大量地點之間的聯系未給予充分重視,這限制了對社區生活圈概念的深入理解。
實際上,社區邊界劃分是自20 世紀70 年代始,城市地理學和城市社會學共同關注的重要議題,前者稱之為“社區發現”(community detection),后者稱之為“鄰里識別”(neighborhood recognition)。兩者的研究目的非常接近:就是要在區域中找出那些“在功能或聯系方面更為緊密”的次級地區[16]。在具體方法上,地理學關注社區內部的功能聯系,多采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識別出具有共性的社區[17];而社會學則更為關注社區內部基于地點間的社會互動,認為“內部互動強于外部互動的區域”即可定義為社區——這種互動可以是通勤交通[18],可以是電話通訊[19],可以是人口流動[20],甚至可以是報紙訂閱信息[21]。近年來由于手機、社交媒體等帶有地理信息的大數據出現,基于地點互動的“鄰里識別”方法得到了快速發展,其中尤以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中的復雜網絡算法發展最快,為大范圍的鄰里識別提供了可能,也為社區生活圈的邊界劃分提供了有力的分析工具。
本文以成都市中心城區(549 km2)為例,通過大樣本的手機位置服務數據(location based services,LBS),嘗試采用復雜網絡分析技術對社區生活圈進行測度,并探討區位、路網密度和POI密度等空間要素對社區生活圈規模的影響。
1 案例、數據和方法
1.1 案例選擇
選擇成都作為研究對象出于三個考慮:首先、作為中國的超大城市,成都市域面積大(14 335 km2)人口多(約1 400萬)、城鄉社區類型多樣(成都下轄22個區/縣,374個街道/鎮,4 357個居委/村委,各區(縣)和街道(鎮)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水平方面差異明顯,不同社區在資源稟賦、城市化水平、產業結構、空間特色、文化認同、生活方式等方面呈現出極大的豐富性),社區生活圈的規劃難度很大,本研究以成都中心城區為對象(含錦江區、青羊區、成華區、金牛區、武侯區、高新區行政范圍,下轄81個街道辦和556個居委單元,總面積549 km2);其次,近年來成都在社區規劃與治理方面十分活躍,編制并實施了包括《成都市中心城十五分鐘基本公共服務圈規劃(2014—2020)》[22]、《成都市城鄉社區發展規劃 (2018—2035)》[23]在內的多種類型的社區規劃,成都經驗對全國其他城市具有重要的借鑒;最后,成都市民文化豐富,社區生活有特色,生活圈研究有一定的代表性。
1.2 數據來源
本研究收集了成都市社區層面的三類數據:居民日常活動、公共服務設施POI、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居民日常活動數據是由某數據服務商提供的成都市2017年5月13—20日為期一周的手機LBS數據(已脫敏并清洗),是手機用戶通過使用各類與地理位置相關的APP而主動定位的數據,具有精度高,不受信號基站密度影響的優點。公共服務設施數據是2017年底通過高德POI抓取的7大類和26小類公服設施信息(包含商業、教育、醫療、休閑、文體、交通、養老,共119 723有效信息),以及按照2017年《成都市中心城區十五分鐘基本公共服務圈規劃》在建的184處社區綜合體信息等。社區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數據包括2017年底全市街道(鎮)與居委(村)的行政邊界、常住人口、路網邊界、網格化管理單元數等信息。課題組借助2017—2019年間的多次實地調研已獲得了上述數據,初步建成了GIS數據庫(圖1)。

圖1 成都市域和中心城區行政劃分圖(自繪)Fig. 1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map of Chengdu and its central urban area
1.3 分析方法
社區生活圈測度與特征識別是本課題的基礎和重點。從居民個體視角看,社區生活圈可以理解為“以家為中心,日常活動所及的空間范圍”。但個體數量眾多,日常活動的邊界也是動態變化的。一座城市到底有多少社區生活圈以及如何劃定邊界(而不是街道行政邊界或控規單元),目前在技術上仍有難度[24]——這對于社區生活圈規劃和公服設施配置來說又是必須要解決的問題。其實,從生成機制看,生活圈也可以理解為“一定范圍的空間,由于居民日常性的‘使用’而產生了某種內在聯系”,是居民“用腳投票”而不是行政區劃或技術分區的結果。將全市居民(本文為手機用戶)的日常活動軌跡進行疊加,就能得到一張聯系著城市各類場所的巨大網絡,其中必然有一些節點由于居民的頻繁使用而產生了更為緊密的聯系,從而形成集合(網絡分析中稱之為“簇”或“社區”)。借助復雜網絡的計算方法,可以根據聯系的強弱把整個城市劃分為若干不同規模的社區生活圈(圖2),圖中連線的粗細代表聯系強度,不同色塊代表發現社區生活圈的邊界。在這些生活圈中,“節點”是居民自住地以及周邊的商店、菜場、餐廳、學校、醫院、運動場館、公交車站等設施,“聯系”則是居民在不同節點之間的活動軌跡,可以通過手機LBS、出租車、甚至是微博簽到等帶有位置信息的動態數據獲取。復雜網絡的視角能讓我們更加接近社區生活圈的本質——即把居民的日常活動作為測量不同地點之間聯系強度的一種方法,這就是復雜網絡方法測度社區生活圈的基本原理。這種地點之間的“內在聯系”是由大量的居民活動和城市功能交互過程中形成的相對穩定的關系。也可以說,社區生活圈是城市空間結構的一種基本體現。

圖2 基于手機LBS數據(2017.05.17)和路網單元(d=0.5km),采用Infomap算法生成的135個社區生活圈(自繪)Fig. 2 135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generated by Infomap algorithm based on mobile phone LBS data(2017.05.17) and road network unit(d=0.5 km)
基于如上理論,課題將對成都的社區生活圈進行測度。先整理成都中心城區道路中心線及居委會行政邊界,以路網單元(LWDY,共計3 691個,平均規模0.15 km2)和居委單元(JWDY,共計556個,平均1 km2)分別作為分析單元;選取1個工作日(2017.5.17)的手機LBS軌跡數據(1 231 433位用戶,7 785 826條記錄)計入路網單元和居委單元;采用復雜網絡分析中的Infomap算法計算聯系強度,聚類生成社區生活圈。
在“鄰里識別”方面,社會網絡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已經發展出了許多算法,大體可以分為拓撲分析和流分析兩大類。“拓撲分析”是把內部聯系多于外部聯系的點的集合劃為一個社區,該方法不考慮節點權重和聯系方向,即無權無向,如Q Modularity,Fast Greedy 等算法。而“流分析”則是基于網絡節點之間存在的某種流動(物質、能量或信息),流動越強次數越多就越有可能劃為一個社區,該方法考慮節點權重和聯系方向,即有權有向,如Walk Trap,Infomap 算法等。顯然,基于居民日常活動的社區生活圈發現更適合用“流分析”方法,而且Infomap 算法在小型社區發現方面更為穩定。Infomap 的計算原理如下:假設有同一小區a 的兩位居民甲和乙,他們在同一天分別出現在周邊b,c,d 和b,e等場所活動,那么因為甲的活動所形成的社區聯系為[a,b,c,d]兩兩相連,乙為[a,b,e]兩兩相連。以此類推就可以得到全市所有居民日常活動的聯系矩陣,從而根據各節點之間的聯系強度發現復雜網絡中的“社區”(生活圈)結構。
此外,考慮到全市的手機用戶活動距離差異很大,為了避免無效的“過境出行”,通過在Infomap 中設定距離約束(d)來篩選出“有效聯系”(即兩個單元之間距離小于d值的聯系才認為是有效的)。通過測試不同的d值,可以得到不同數量和規模的“社區生活圈”(表1)。

表1 不同d值下發現社區生活圈的數量及規模(自制)Tab. 1 Number and scale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discovered at different d values
2 分析結果
2.1 單元精度與d值選取
初步測算發現,分析單元的精度(resolution)對生活圈的聚類有重要影響,居委單元(JWDY)由于自身尺度較大,無法測量居民日常大量的短距離活動,聚類得出的最小生活圈也有13.8 km2。相比之下,路網單元(LWDY)精度高,對短距離活動敏感,聚類效果更好(圖3)。

圖3 不同精度的分析單元聚類生成的社區生活圈數量比較(自繪)Fig. 3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generated by clustering analysis units at different accuracies
把d值從0.5 km 逐步增加到20 km,再到全鏈接(無距離約束),中心城區(549 km2)的生活圈聚類數量從135 個減少到44 個,生活圈的平均規模從4 km2增加到12 km2。其中,d值在0.5~3 km時,生活圈的聚類數量變化最顯著——這說明3 km 以內的活動是決定生活圈規模的主要聯系,超過3 km的活動對生活圈的形成作用不顯著,從手機LBS 聯系數量上也能發現同樣的規律:小于0.5 km的聯系量(4 683 625)占全鏈接聯系總量(11 915 470)的39.3 %,小于3 km 的聯系量(7 799 346)則高達65.5 %。當d值為0.5 km所形成的生活圈(平均規模為4 km,平均半徑為1.1 km)與大家熟知的“15 min 社區生活圈”最為接近。以下將選取這一模型(選取路網單元LWDY,普通工作日,d值0.5 km)展開進一步分析。
2.2 社區生活圈的空間特征
目前國內城市在社區生活圈規劃和實施中大多會建議一個生活圈的標準模式,如上海“15 min社區生活圈”的面積為3~5 km2,常住人口5~10萬,人口密度1~3 萬·km-2。但實際上,每個社區生活圈受到區位、社會經濟發展條件的影響,并不存在一個標準模式,這就需要對其規模、邊界等特征做進一步分析。從成都中心城區來看,社區生活圈的面積差異較大,大但多數的規模處于1~5 km2之間,其中2 km2占比最大(接近15 %)(圖4)。

圖4 135個社區生活圈的面積規模分布(自繪)Fig. 4 Size distribution of 135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此外,將135個社區生活圈邊界與《成都市中心城十五分鐘基本公共服務圈規劃(2014—2020)》邊界(由于行政區劃調整,該規劃并未覆蓋整個中心城區)進行比較可以看出:①在城市環路、河道、放射狀主干道附近,社區邊界與公服圈邊界重合度較高。初步統計,135個社區生活圈中,約有60 %的邊界與現有街道/鎮行政邊界重合,這些重合的邊界大多是城市快速路、河道等物理阻隔——而行政邊界和物理邊界正是當前成都“十五分鐘基本公共服務圈”劃分的主要依據。②基于LBS數據發現的社區生活圈的平均規模要大于公服圈的平均規模(前者有時數倍于后者),這說明成都中心城區居民的日常活動已經超出了“基本公共服務圈”的規劃范圍。利用LBS數據發現的生活圈可能更為接近社區居民的實際活動與需求(圖5)。

圖5 135個社區生活圈與“成都市中心城十五分鐘基本公共服務圈規劃”邊界比較(自繪)Fig. 5 Boundary comparison between 135 community living circles and the “Fifteen-Minute Basic Public Service Circle Plan for Central Urban Area of Chengdu”
2.3 影響社區生活圈規模特征的空間要素
社區生活圈的形成是一個動態過程,其規模、邊界和構成要素會隨著人口結構、城市化水平、交通區位條件的變化而發生改變。為了理解這一動態機制,還需要進一步分析“哪些空間要素對生活圈的規模特征產生了影響”?已有研究表明,人口規模和密度、商業和住宅開發強度、路網密度、與地鐵站距離等要素都對社區生活圈的邊界有不同程度的影響[25]。根據數據收集情況,本研究提出了“三類空間要素與社區生活圈規模相關”的初步假設,包括:①距離市中心距離;②路網密度;③POI 設施密度(本文以商業POI 為例)。對三個空間要素與社區生活圈的面積規模進行了相關性分析:與區位(距離市中心距離)之間存在弱相關(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266);與路網密度之間存在中等程度相關(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547);與商業POI 密度之間存在弱相關(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313)(圖6)。

圖6 社區生活圈(N=135)的面積規模與空間要素之間的相關關系Fig. 6 Correlation between size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N=135) and spatial elements
從相關性分析看,三類空間要素中,只有路網密度與社區生活圈面積規模存在中等程度相關(-0.547),區位和商業POI密度與社區生活圈規模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這背后的原因,可能與中心城區高度城市化、成都豐富的市井生活形成商業網點均勻分布的特征有關(各社區都能在日常活動范圍內找到足夠多的興趣點)。下一步如果將成都城鄉結合部和鄉村社區納入分析,區位、商業POI與社區生活圈面積規模之間的相關性可能會有顯著提升。
此外,發現如果把測量社區生活圈規模的參數從面積替換為人口密度,區位、路網密度、商業POI密度與社區生活圈規模之間的相關性出現了大幅度提升:與區位(距離市中心距離)之間存在強相關(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738);與路網密度之間存在強相關(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634);與商業POI密度之間存在極強相關(皮爾遜相關系數為-0.930)(圖7)。

圖7 社區生活圈(N=135)的人口密度與空間要素之間的相關關系Fig. 7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density of community living circle (N=135) and spatial elements
三類空間要素與社區生活圈人口密度的相關性明顯高于與社區生活圈面積規模的相關性。這一事實提醒我們,定義社區生活圈的“規模”除了面積,還應當考慮人口密度,“人口密度—空間要素—面積規模”三者之間可能存在著復雜的作用機制。社區生活圈本質上是一種基于人口密度、豐富的街道生活(路網密度)和服務設施(商業POI)的聚居方式。
3 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梳理社區生活圈概念和測度方法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個假設:①從居民的日常活動看,城市存在若干規模不等的社區生活圈,這是城市空間結構的基本屬性;②社區生活圈的規模與區位(距離市中心距離)、路網密度、POI 密度等空間要素之間存在一定的相關性,這種相關背后有著復雜的空間與社會機制。實證部分,本文以成都為例,利用手機LBS動態軌跡數據,采用復雜網絡分析Infomap 算法,驗證了成都市中心城區社區生活圈的存在,且存在一定的規模差異,這種規模變化與路網密度呈現中等程度相關,與區位和商業POI 密度之間的相關性不明顯;但社區生活圈的人口密度與三類空間要素存在強相關。
研究在方法和實踐層面都具有重要意義:在方法層面,把地理位置信息引入社會網絡分析,將復雜網絡算法與GIS 分析相結合,建立基于大樣本居民活動數據的社區生活圈測度方法,可以解決當前社區生活圈規劃的關鍵技術難點(邊界劃定)。在實踐層面,基于LBS 數據的測度方法不僅可以準確識別15 min 生活圈,還可以通過單元精度和距離參數的設定,對5 min 生活圈、10 min 生活圈,甚至通勤圈、擴展圈進行識別,從而深入理解城鄉空間的多層級結構及其內在聯系,為城鄉規劃提供科學依據。
本文也存在三方面的不足:① 受數據限制,目前僅選擇一個工作日,在中心城區范圍內對區位、路網密度、POI 密度要素與社區生活圈規模的相關性進行了分析,未來研究將考慮更多工作日、重要節假日(春節、十一國慶等)以及代表夏季、冬季的關鍵日數據,從而更全面刻畫社區生活圈的動態邊界。同時還有必要將LBS 數據拓展至整個市域,增加土地使用、開發強度、商業與住宅密度、其他POI 設施等空間要素做進一步的相關性分析;② LBS數據所對應的主體與活動類型較為豐富,下一步有必要對其深入分析,嘗試提取出“與社區生活圈緊密相關”的居民活動數據后再做“鄰里識別”運算,從而精確刻畫不同社區生活圈的邊界和內部結構;③ 大數據分析僅僅揭示出空間要素與社區生活圈規模、人口密度之間的相關程度,但這種相關背后的影響機制異常復雜,還需要結合實地調研和居民訪談進行深入分析。
作者貢獻聲明:
楊 辰:提出研究問題、分析框架與論文撰寫。
辛 蕾:數據整理與分析。
馬東波:復雜網絡算法優化。
賈姍姍:論文修訂。
陳 晨:完善技術框架與算法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