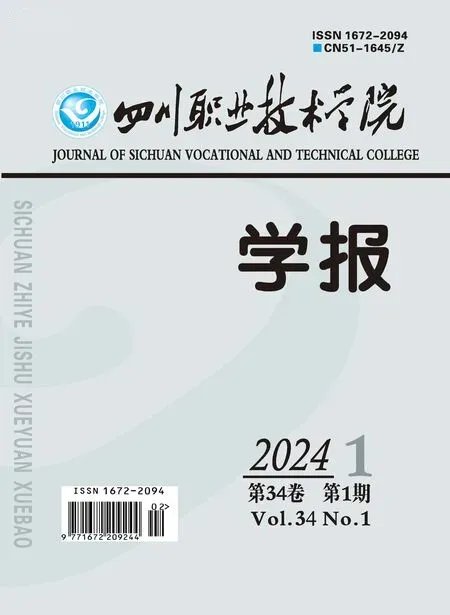從“腐草為螢”談到上古漢語中的耕元通轉
向 倩
(西南大學 漢語言文獻研究所,重慶 北碚 400715)
一、問題的提出
《黃帝內經·素問》卷一中有“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一句,下有注文“次大暑氣,初五日腐草化為螢……秋為痎瘧,奉收者少”,其中“腐草化為螢”與《逸周書》中記載相同,而在《呂氏春秋·季夏紀》中記載為“腐草化為螢蚈”;錢繹《方言箋疏》卷十一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為蠲”;《淮南子·時則》作“腐草為蚈”,高誘注:“蚈,馬蚿也。”對于以上不同的記載,清代王念孫在《讀書雜志》中疏證道:
“螢”本作“蛙”,后人習聞《禮記·月令》之“腐草為螢。”故改“蛙”為“螢”。“蛙”即“蠲”借字。《說文》:“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為蠲。”蛙從圭聲,圭、蠲古同聲,故《小雅·天保》“吉蠲為饎之蠲”,鄭注《周官·蠟氏》《士虞禮記》並引作“圭”。[1]2307
《禮記·月令》中記載:“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陳說了季夏時節動植物的習性變化。“螢、蠲、蚈”皆指“由草木所化的蟲類”,文獻中常互用。考察三者的語音關系,“螢”為匣母耕部,“蠲”為見母元部,“蚈”為溪母元部,聲母皆為喉牙音,發音部位相近,韻部關系為耕元旁轉。
耕部和元部之間語音關系密切,王念孫還曾舉過諸多例子。如《淮南子·兵略》:“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其中“端、觀”押元部韻,“垠、門”押文部韻,但“故不可得而觀”和“故莫能窺其門”句式不一致,故王念孫推測今本“故不可得而觀”有誤:
“不可得而觀”,本作“不可觀其形”,后人以“形”與“端”韻不相協,故改為“不可得而觀”也。不知元耕二部,古或相通。(《說文》“瞏”從“袁”聲,而《唐風·杕杜篇》“獨行瞏瞏”與“菁”“姓”為韻。《齊風·還篇》“子之還兮”與“簡”“肩”“儇”為韻,而《漢書·地理志》引作“子之營兮”。《淮南·精神篇》曰:“以道為紃,有待而然,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而物無能營。”《齊俗篇》:“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道應篇》曰:“為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又《莊子·大宗師篇》:“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逸周書·時訓篇》:“螻蟈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命。王瓜不生,困于百姓。”《漢書·禹貢傳》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外戚傳》《悼李夫人賦》曰:“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太玄·進·次二》曰:“進以中形,大人獨見。”《聚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嘻嘻,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易林·姤之臨》曰:“禹召諸侯,會稽南山,執玉萬國,天下康寧。”《升之震》曰:“當變立權,擿解患難,渙然冰釋,大國以寧。”皆以元耕二部通用。)“形”字正與“端”為韻也。人能觀天,而不能知其形,故曰“不得觀其形”,非謂“不可得而觀”也。《文子·自然篇》正作“故不得觀其形”。[1]2308
王念孫例證充分,詳細說明此處是因后人不知耕元部可以通轉的關系,將句子改為了“不可得而觀”,然而也有學者否認這一看法,不贊同耕元兩部有關系,如楊樹達認為:
王校非也。下文云:“圣人藏于無原,故情不可得而觀”,與此句例正同。文言“不可得而觀”者,謂天無端可觀,非謂天不可得觀。亦猶下文言地無垠,故無門可窺,非謂地不可得窺也。上下二句文例不同者,以協韻故耳。王氏誤解文義,疑“天不可得觀”為不可通,故欲改從《文子》之文,又礙于“端”“觀”為韻,故為元耕通韻之說。不悟《文子》乃以誤解文義而妄改,不足據依也。[2]
張雙棣也依從楊說[3],認為此句“端、觀”押元部韻。對于這一分歧,我們認為王校甚確。從文意上來說,“故不可得而觀”與“故莫能窺其門”既分別對應天和地,文例也應相協為適,且除《淮南子》外,《文子》一書便作“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可相對讀。此外,李寶珊更舉祖暅《天文》中對天地之形的概說,以證此處應從王氏校改[4]。從語音上看,耕元兩部相通的證據充足,下文將詳細論證。
二、耕元部語音通轉關系梳理及補證
耕部和元部的主要元音和韻尾有較大差別(元部擬音為[an],耕部擬音為[e])[5],且《詩經》中也未見兩者合韻的例子,因而前輩學者鮮少論及兩部的語音關系。過去有學者討論過古音中-n和-的相混的情況,也幾乎不涉及耕元兩部。如陸志韋先生曾認為《詩》韻中韻尾-n都通韻尾-,集中在耕部與真部之間[6],邢公畹先生也只就王力《同源字典》中所列出-n,-韻尾交替的四種情況(即耕真、陽真、陽元、東元之間的通轉)進行探討并舉出例證[7]。我們認為耕元通轉是漢語語音史上實際存在的音轉現象。依王力先生的上古音系統,耕元兩部分別為第六類、第七類的陽聲韻部,從其在語音系統中的位置來說,兩者滿足可互為旁轉的關系,最早章太炎便指出“青寒亦有旁轉者,如煢煢亦作嬛嬛,自營亦作自環是也”[8],1999年,汪啟明對齊語中耕元部相通的例子進行列舉,并總結道:“齊語中耕元部相交替的現象,在漢代以后的異文、聲訓、通假和讀若中都有發現。”[9]其后黃樹先也從諧聲、又讀、假借和異文、同族詞、詩文用韻等五個方面舉例論證了耕元部之間的密切關系,并藉助親屬語言緬語及越語的借音材料進一步探討了上古音中耕部演變的條件,認為漢語耕部到元部(*-e>*-a),應該是一種語音的異化[10]。以上諸位學者主要利用傳世文獻進行論證,也有學者利用出土文獻對耕元部間的密切關系加以證明。劉波在《出土楚文獻語音通轉現象整理與研究》中從韻文和諧聲通假兩方面整理出土楚文獻中元耕二部合韻的例子[11]:
郭店簡《老子》乙本:燥勝寒,清勝熱,清靜為天下定。[12]
“寒”屬元部,“定”屬耕部。
《上博七·君人者何必安哉》甲本:楚邦之中有食田五貞,竽管衡于前,君王有楚,不聽鼓鐘之聲,此其一回也。[13]
“貞、聲”屬耕部,“前”屬元部。以上為韻文合韻。

除上述例證外,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中還存在大量如“蠲”與“螢”通、“煢”與“嬛”通、“營”與“環”通等耕元部通轉的平行例證,試增補于下:
(一)屏、平、庰與便、辨相通
《漢書·王莽傳中》:“常翳云母屏面,非親近莫得見也。”顏師古注:“屏面即便面,蓋扇之類也。”又《漢書·敘傳》:“敝亦平平。”顏師古注:“平讀曰便。”《詩·小雅·采菽》:“平平左右。”《釋文》:“平平,《韓詩》作‘便便’。”《尚書·堯典》:“平章百姓。”《史記·五帝本紀》作“便章百姓。”《逸周書·官人解》:“屏言弗顧,自順而弗護,非是而強之。” 《大戴禮·文王官人》屏作“辨”,屏言即巧言。蔣禮鴻:“今言大便小便,便乃庰至音轉。《廣雅·釋宮》:‘庰,廁也。’大便小便,廁中事也。庰或作屏。王念孫疏證曰:‘《急就章》云:“屏廁清溷糞土壤。”屏與庰通。顏師古注《急就篇》曰:“屏廁清溷,其實一也”。’[15]“平、屏、庰”為並母耕部,“便、辨”為並母元部。
《山西珍貴文物檔案(8)》一書公布了一件山西曲沃北趙晉侯墓地出土的叔昜盤[16],其銘作:
吊(叔)昜父乍(作)寶般(盤)△,其萬年寶用。
(三)旦與丁(頂)相通,袒、綻與逞、裎相通
(四)俔與磬、鑋、頃相通

(五)諍、證與諫相通
《說文·言部》:“諍,止也。從言,爭聲。”徐鍇系傳:“《孝經》曰:‘君有諍臣,不失其天下。’謂能止其失也。”桂馥義證:“止當作正,諍、正聲相近。《周禮·司諫》注云:‘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廣雅·釋詁四》:“諍,諫也。”《說文·言部》:“證,諫也。”“諫,證也。”《戰國策·齊策(一)》:“士幃以證靖郭君,靖郭君不聽。”高誘注:“證,諫也。” 按“諍、證”二字皆訓“規諫”,“諍臣”即為“諫言之臣”,“諍、證”為耕部字,“諫”為元部字。
(六)璇與瓊(瓊)相通,睘(環)與熒相通
《說文》:“瓊,赤玉也。從玉敻聲。或體作琁,從旋省。”《史記·封禪書》:“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漢書·郊祀志》璇作瓊。

中國嘉德2010年秋季拍賣會上曾高價拍賣過一枚環錢(見圖1),過去收藏界一般將這枚錢幣上的文字釋讀為“巉環”或“燕環”,黃錫全認為應讀為“環(澤)”,對應清華簡《系年》簡19中的“睘”,也即傳世文獻《左傳》《紀年》中所記狄人伐衛的地名“熒澤”,在今之河北滑縣西北,屬衛[23]。楚簡中“環”常用“睘”來記錄,如《望山楚簡二》簡50:“一端睘(環)。”又:“一玉句(鉤),一睘(環)。”[24]“熒澤”也作“滎澤、泂澤”,“滎、熒、泂”皆為匣母耕部,“瓊”為群母耕部,“睘(環)”在匣母元部,“璇”在邪母元部。然則煢之于嬛,猶瓊之于璇、熒之于睘(環)也。
(七)骭與脛相通
《說文·骨部》:“骭,骹也。”“骹,脛也。”“脛,胻也。”段玉裁注:“脛表謂之骭。”《史記·龜策列傳》:“圣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裴骃集解:“胻,腳脛也。”馬王堆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乙本:“陽明脈系于骭骨外廉,揗(循)骭骨而上,穿賓(髕)……病甚則欲登高而歌,棄衣而走,此為骭厥。”《足臂十一脈灸經》作:“循胻中,上貫膝中,出股,挾少腹……”《靈樞·經脈》作:“下膝髕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故可知“骭骨”即“脛骨”,亦作“胻骨”,相馬術中稱“骭”為“脛”或“懸薄”[25]。“骭”為見母元部,“脛”在匣母耕部,兩者聲母皆為喉牙音,韻部為耕元旁轉。
(八)絅、褧與襌相通
《禮記·玉藻》:“纊為繭,缊為袍,襌為絅,帛為褶。”《詩·衛風·碩人》:“衣錦褧衣”,《魯詩》“褧”作“絅”。孔穎達正義:“絅與褧音義同,是褧為襌衣裳所用。《書》傳無文而婦人之服尚輕細,且欲露錦,文必不用厚繒矣,故云:蓋以襌縠為之。襌衣在外而錦衣在中,故言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按“褧”為正字,義為麻布單衣,“絅”為借字。《說文·衣部》:“襌,衣不重。從衣單聲。”絅、褧、襌皆以“單衣”解之。“絅、褧”在溪母耕部,“襌”在端母元部。
(九)耿介與狷介相通
《楚辭·離騷》:“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又《七諫·哀命》:“惡堯舜之耿介兮,世混濁而不知。”蔣禮鴻考釋云:“蓋耿介、狷介、捍格、格奸、間介並為顎音雙聲謰語,其字則異,其音與義則同。”[26]《論語·子路》:“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狷介”常用作人物品行的評語,《漢語大辭典》訓釋為“孤高潔身”[27],與“耿介”“立身正直,廉潔自持”之義相近,語音關系為耕元旁轉,可通。
(十)燕與嬰、匽相通,牼與顅相通,膻與馨相通
燕與嬰、匽相通,《詩經·邶風·燕燕》:“燕燕于飛”,“燕”阜陽漢簡作“匽”,馬王堆帛書作“嬰”。胡平生曰:“金文中燕國之‘燕’,自周初至戰國皆作‘匽’《阜陽漢簡》中‘燕王’之‘燕’已寫作‘燕’。”[28]《左傳·僖公元年》:“公敗邾師于偃。”《公羊傳》偃作“纓”。因而“燕、匽、嬰”語音相近,“燕、匽”在影母元部;“嬰”在影母耕部。
牼,通顅,《說文通訓定聲·鼎部》:“牼,假借為顅。”《周禮·考工記·梓人》“鋭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鄭玄注:“顅,長脰貌。故書顅或作牼。”“牼”,溪母耕部;“顅”,溪母元部。
膻,通馨,《說文通訓定聲·干部》:“羴(膻),假借為馨。”《禮記·郊特牲》:“故既奠,然后爇蕭合膻薌。”鄭玄注:“蕭,薌蒿也……膻當為馨,聲之誤也。”“膻”,定母元部;“馨”,曉母耕部。
然則環之于營,猶燕、匽之于嬰,顅之于牼、膻之于馨。
三、結語
除上述例證外,我們在對耕元兩部間的通轉關系進行考察時發現,兩部所對應的陰聲韻部支部和歌部關系也十分相近。段玉裁在《答江晉三論韻書》中寫道:
“仆之十七部次第,始于之,大意以之、尤相近,故之之字多入于尤;而蕭者,尤之類,蕭之入當同之,故次第二……支者似脂而不同,與歌最近,故歌之字,多入于支,蓋以支之入為入者,故次十七。此則仆以入為樞紐而求其次第之意。”[29]
由此可知,古音支歌相近,耕部乃支部陽聲,元部乃歌部陽聲,支之于歌,猶耕之于元也。此外,支部與元部也常發生對轉,如“刪”從“冊”聲,王念孫對此有詳細舉證[30]。因此耕元兩部語音關系密切這一事實是不可否認的,而對于兩部為何頻繁發生通轉,黃樹先認為耕元相通是一種方言現象,在齊、楚等地古方言中部分耕部字發生了音變,由耕部*-e>元部*-a[10]4-10。筆者贊同黃先生的這一看法,在鄭張尚芳、潘悟云兩位音韻學家的古音體系中,耕部擬音為*-e,元部則分為三個韻:元1*an、元2*en、元3*on,元1*an、元3*on與耕部元音差距較大,而元2*en與耕部雖主要元音相同,但韻尾差異仍然存在,理解為耕部字在一些地區讀音發生音變,由*-e>*-a,*-a(高元音促使韻尾的發音部位遷移(>),短元音e低化為a)再與元部字相通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了。
最后,我們還想附帶討論一下關于“宋钘”的讀音問題。《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中所記載的宋钘,是先秦時期重要的思想家,過去認為“钘”字兩讀:作“酒器”講時讀為[xíng],作“人名”時讀為[jiān][31]。最近,李佳喜結合相關古文字及音韻材料對“宋钘”的讀音再次進行了探討,指出“钘”字本從“井”聲,應讀為[xíng],“钘”所從之“井”(耕部),后來訛變為“幵”(元部),因此后人誤讀“銒”為[jiān][32]。這是很精辟的見解。不過如果考慮到上古漢語中耕元通轉的現象,或許還可以作另一種解釋。“宋钘”在《孟子·告子》中作“宋牼”,楊倞注:“牼與钘同。”前文討論了“牼”在典籍中與“顅”聲相通,也即“牼”在上古漢語中或有“肩”一類的讀音。又,“宋钘”在《莊子·逍遙游》中稱“宋榮子”,而“榮”及“熒”聲字也常與元部字相通,耕元部語音相近,那么古人以為與“牼”相通的“钘[xíng]”或讀為元部,音[jiān],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