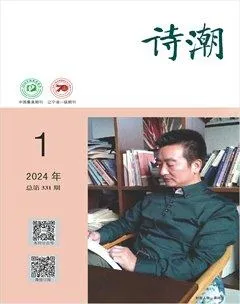魯若迪基詩歌代表作品選
魯若迪基
小涼山很小
只有我的眼睛那么大
我閉上眼
它就天黑了
小涼山很小
只有我的聲音那么大
剛好可以翻過山
應答母親的呼喚
小涼山很小
只有針眼那么大
我的詩常常穿過它
縫補一件件母親的衣裳
小涼山很小
只有我的拇指那么大
在外的時候
我總是把它豎在別人的眼前
天空太大了
我只選擇頭頂的一小片
河流太多了
我只選擇故鄉無名的那條
茫茫人海里
我只選擇一個叫阿爭伍斤的男人
做我的父親
一個叫車爾拉姆的女人
做我的母親
無論走在哪里
我只背靠一座
叫斯布炯的神山
我懷里
只揣著一個叫果流的村莊
長大的是孩子
老人一長大
就更老了
長不大的是村莊
那么一片土地
那么一條河流
那么一些房屋
生死那么一些人
有人走出村莊了
再也沒有回來
他們把村莊含在眼里
痛在心上
更多的人一生下來
就長了根
到死也沒有離開過
雪后
那些山脈
宛如剛出浴的女人
溫柔地躺在
瀘沽湖畔
月光下
她們嫵媚而多情
高聳著乳房
仿佛天空
就是她們喂大的孩子
永遠的孩子
我不是吃水長大的
我是吃奶長大的
母親的孩子
我也是夢幻天空的孩子
曾吮吸
月亮和太陽的乳汁
我更是自由大地的孩子
常把山頭
含咂在嘴里
即便有一天老了
只剩下一把骨頭
我也會在大地的子宮
長——眠
日子的尾巴
拂不凈所有的塵埃
總有一些
落在記憶的溝壑
屋檐下的父母
越來越矮了
想到他們最終
將矮于泥土
大風也無法吹散
我內心的傷悲
一群羊被吆喝著
走過縣城
所有的車輛慢下來
甚至停下來
讓它們走過
羊不時看看四周
再警惕地邁動步子
似乎在高樓大廈后面
隱藏著比狼更可怕的動物
它們在陽光照耀下
小心翼翼地走向屠場
是木頭
是木頭長出的耳朵
木頭的耳朵
它聽到了什么
當它被人活活扯下
木頭是不是暗叫了一聲
我們把它煮熟
放進嘴里的一剎那
只一聲脆響
我們仿佛咬了自己的耳朵
那一刻
我們木了
當年的新娘
如今當上了奶奶
三個兒子
大兒子在銀行當保安
幾年前除夕夜
死在了值班室
留下一個孩子
讓她領著
二兒子十多年前
去西藏打工
翻車雅魯藏布江
尸體也沒有找到
翻車前幾天
電話里說的幾句話
讓她至今念叨
三兒子在當導游
兒媳也是導游
孩子留在老家
讓她照看……
當年接親隊伍里
年紀最小的我
除了負責磕頭、牽馬
還負責偷個碗
當送親的隊伍
在茫茫雪地休息
我怯生生將偷來的瓷碗
遞給他們驗收
他們把碗傳遞著查看
最后滿意地說
沒有一點兒瑕疵
這會是一段
美滿幸福的婚姻
主人家有好幾種碗
每次見到她
我不止一次想
當年為什么不偷
那個鑲邊的銀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