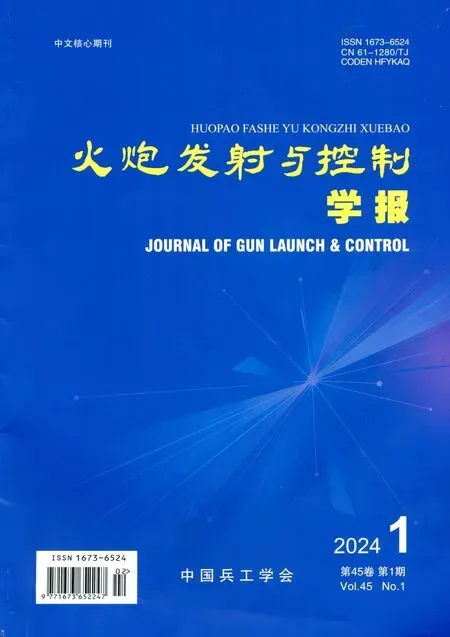大口徑火炮發射噪聲場數值仿真與實驗研究
蔣晟,阮文俊,孫雪明,劉建功
(1.南京理工大學 能源與動力工程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4;2.江西星火軍工工業有限公司,江西 南昌 331709;3.河北太行機械有限公司,河北 石家莊 052160)
火炮依靠發射藥劇烈燃燒產生的高溫高壓火藥氣體,推動彈頭經火炮身管發射而出,有必要對火炮發射時炮手區域的噪聲變化規律進行研究。
國內外研究者從炮口流場發展規律出發,對火炮發射過程進行模擬,得出了火炮炮口流場的發展規律[1-5]。內彈道參數作為影響流場分布規律的重要變量,在對炮手區域壓力變化規律的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張欣慰等[6]對不同裝藥量下水下機槍封閉發射膛口流場進行了模擬,發現裝藥量對膛口流場分布規律性有一定的影響;李曼麗等[7]研究了火藥氣體生成速率對小口徑槍發射過程中膛內流場的影響;吳勝權等[8]針對混合裝藥無后坐炮的內彈道性能,對不同裝藥比例及裝藥量對內彈道性能的影響進行了研究。牛玉光等[9]在對火炮發射時噪聲對人體影響的研究中發現,火炮發射造成的超壓會對人體的聽覺器官甚至大腦、心臟等其他器官產生不利影響。因此現代火炮設計中不僅要考慮火炮威力,還要考慮火炮發射帶來的噪聲分布,特別是對炮手區域的影響。
在火炮發射所造成的噪聲場研究方面,路寬等[10]通過對火炮炮口流場進行的非穩態數值模擬,得到了大口徑火炮炮口噪聲場分布規律;江坤等[11]對車載炮膛口沖擊流場進行數值模擬,得到火炮發射過程中車身受到壓力的分布規律;王丹宇等[12]采用BP神經網絡方法對火炮輻射范圍的最大半徑進行預測,結果為14.361 6 m。以上研究都為研究炮手區域噪聲分布做出了貢獻。
筆者結合具體試驗方法,在保證CFD計算機模擬合理性的前提下對內彈道參數改變引起的炮手區域流場變化進行了研究,并對比了不同內彈道參數下炮手區域噪聲的分布規律,建立了內彈道參數與炮手區域噪聲分布規律的聯系。
1 計算模型
1.1 物理模型
筆者研究的155 mm-52D發射平臺實體模型較為復雜,為了研究理想情況下炮手位置的壓力分布規律,對模型進行一定簡化,根據實體模型建立的三維仿真物理計算模型如圖1所示。由于計算模型的對稱特性,于火炮對稱面一側取長×寬×高為16 m×1.8 m×2 m的范圍空間作為研究對象進行計算模擬。同時為模擬彈丸出膛過程,動網格設置需要將模型分為靜止區域及運動區域。運動區域計算模型如圖1所示,計算區域內其他空間為靜止區域。筆者基于大口徑火炮發射進行研究,研究重心在于內彈道參數對炮手區域的噪聲及壓力的影響,因此,對炮口制退器進行了一定的簡化,忽略了對壓力遠場影響較小的膨脹腔室,其彈孔直徑即為彈丸直徑。

炮口制退器結構參數如圖2所示,在反作用式炮口制退器的設計中,對制退器制退效果影響最大的參數是側孔高度h、側孔寬度c、側孔導向長度l及側孔傾角α。其中側孔寬度及側孔導向長度比值固定,當刨除身管壁厚已知時,可根據側孔傾角α對其進行計算;側孔高度根據試驗中選用制退器側孔高度決定。在以上參數確定后,側孔傾角和側孔排數是對炮口制退器效果影響最大的參數,為了使火藥氣體充分發展,選擇四側孔設計方案,其側孔傾角α取150°。

1.2 網格劃分
由于膛口區域流場較為復雜,因此在炮口制退器區域進行網格加密。為了使網格分布更加合理,使用ICEM軟件對彈道區域進行結構化網格劃分,而外流場部分則進行非結構化網格劃分。
整體網格數量約為1 000萬個,初始時刻網格劃分如圖3所示。

1.3 動網格設置
為模擬火炮發射過程中彈丸水平滑移的過程,在流場計算時引入動網格進行模擬。彈丸水平移動,彈前區域被壓縮,彈后區域不斷拉伸,環境靜止區域不發生網格變化。FLUENT軟件可通過彈簧光順法(Smoothing)、動態鋪層法(Layering)及局部網格重構法(Remeshing)對網格進行動態的重新劃分,維持網格質量。筆者通過動態鋪層法來對網格進行動態的劃分,維持網格質量。
動態鋪層法的中心思想是根據臨近運動邊界網格高度的變化,添加或者減少動態層,在鋪層方法中,是否對于網格進行分裂或重組,依賴于網格層高與網格理想層高之間的關系。筆者取理想高度h0為5 mm,分裂因子αs為0.4,合并因子αc為0.2,通過UDF控制彈丸邊界運動。當網格層高度大于臨界值(1+αs)h0時,網格層將會依據定常值高度法或常值比例法進行分裂;當網格層高度被擠壓至小于臨界值αch0時,該處網格將會與上一層網格進行合并。
1.4 數學模型
內彈道作為武器系統研究與設計的基礎,通過已知膛內結構諸元及裝藥條件計算膛內火藥燃氣壓力變化和彈丸運動規律,為武器后坐運動分析、身管設計、炮口制退器設計等提供基本數據。
流場的數值模擬開始之前必須給定流場計算域內所有變量的初始值,且初始條件必須符合實際情況,否則就會出現機選結果精度下降甚至出現錯誤的情況。筆者簡化了炮膛計算模型,忽略了藥室與炮膛斷面的差異,根據比例膨脹假設,則彈丸即將離開膛口時內彈道參數遵循以下方程:
u=zv,
(1)
P=Pte-φz2,
(2)
(3)
(4)
式中:x為火炮膛內軸向坐標;u、P、T分別為膛內燃氣速度、壓力及溫度;v為彈底氣體流速;z為所研究單元混合流體的相對坐標;Pt、Pb、ˉP分別表示膛底壓力、彈底壓力及膛內平均壓力;φ為壓力衰減因子;ω、m分別表示裝藥質量及彈丸質量;φ1為阻力系數;ρ為膛內氣體密度。
1.5 初始條件及邊界條件
本文中火炮身管為壁面邊界;彈丸運動路徑與環境交界面為interface;彈丸前后面為沿運動路徑推進的壁面邊界;地面為壁面邊界;其他為壓力出口邊界,定為標準大氣壓力。邊界條件設置如圖4所示。

以彈丸出炮口時刻為初始時刻,初始條件如壓力、溫度、火藥氣體流速等參數由內彈道計算提供,其中裝藥量選取標準裝藥17.1 kg及強裝藥22.8 kg進行計算,得到兩組內彈道數據,各變量在零時刻膛內的分布如圖5所示。
2 炮射測壓試驗與模擬結果對比分析
為驗證計算模型可靠性,選取155 mm-52D發射平臺進行炮射實驗,測得火炮發射對炮手區域內監測點壓力隨時間變化規律,并將其與仿真結果進行對比。
在此次炮射試驗中選取混合發射藥進行裝填,裝藥量為17.1 kg。靶場現場布置如圖6所示,試驗儀器包括壓力傳感器(瑞典KISTLER公司211B5型,測量范圍0~344.73 kPa)和數據采集儀。試驗中以壓力傳感器測量炮手區域壓力變化,傳感器裝置由支架及傳感器組成,旨在測量距地面1.5 m處壓力變化,更為貼近炮手頭胸部在火炮發射時所受到的沖擊情況。

在計算模型中選擇試驗傳感器放置的坐標進行監測點設置,1號傳感器為第1監測點,2號傳感器為第2監測點。對比試驗與仿真所得結果監測點超壓隨時間變化曲線如圖7所示。可見試驗測得的p-t曲線與模擬趨勢一致,說明建立的計算模型及數值模擬是合理的,能夠反映現實試驗中的數值變化。但模擬壓力變化規律仍與實際情況有所區別:由于實際上布置場地存在大量設備及障礙物,如火炮發射架等,大大削弱了經地面反射的沖擊波,使得第一輪沖擊時間短且弱,而數值模擬中忽略了火炮發射架,獲得了發展較為全面的沖擊波;同時可見,試驗傳感器所得曲線有擾動,而模擬實驗所得曲線更為平滑,這是由于在實際試驗中傳感器會不可避免地受到來自固體地面及炮尾漏氣等因素影響,而模擬實驗中僅考慮流體對監測點噪聲的影響。

由于筆者旨在分析超壓對炮手區域影響,因此在模擬準確性上主要對模擬曲線峰值進行誤差分析。對比模擬與試驗結果,第1、第2測點超壓峰值誤差分別為9.03%與12.61%,處于可接受范圍內,可證明計算模型的可靠性。
3 仿真計算及分析
3.1 壓力監測點設置
由于試驗中僅在炮手區域內設置兩個傳感器對數據進行采集,無法對區域內壓力分布規律進行分析,因此為了得到流場區域不同位置處的壓力值,在監測區域內設置網格狀監測點,于X軸及Y軸上每隔0.5 m設1個監測點,如圖8所示。由于噪聲對炮手的影響大多集中在頭部以及胸部,因此在選取檢測點所處面高度時,選取平行地面1.5 m平面進行監測點設置。

3.2 裝藥量對噪聲場分布規律影響
針對內彈道參數與壓力遠場分布規律之間內在聯系,選取兩種不同裝藥量工況進行模擬分析。在標準裝藥17.1 kg工況下的監測點壓力變化規律如圖9所示。

從圖9(a)可知,在X=0 m處的各監測點所檢測到的最大壓力峰值隨著監測點與炮身軸向之間的距離減小而減小,相較各監測點超壓,坐標點(X,Y)在(0,0.1)上的監測點超壓峰值最大,在(0,1.6)上監測點超壓峰值最小。說明在沖擊波向壓力后場發展的過程中,由于火炮模型對稱特性,流場在發展過程中在對稱面區域形成了較高的壓力峰值,使得在不同橫向距離上,距離對稱面較近的監測點接收到了較高的壓力信號。而如圖9(b)顯示了在軸向上的監測點壓力變化,可見在各點第1次與第2次波峰峰值與其在X軸上的坐標呈反比,即越遠離沖擊波發展源頭,監測點所接收到的超壓越小,第3次波峰最大值于X=3 m處取到。
對標準裝藥17.1 kg和強裝藥22.8 kg兩種工況下的監測點超壓數據進行處理,得到監測區域內噪聲峰值分布云圖,如圖10所示。

可見噪聲主要集中于X=3 m處靠近對稱面區域。標準裝藥及強裝藥噪聲皆于(3,0.1)處達到峰值,其中標準裝藥噪聲峰值為177.6 dB,強裝藥噪聲峰值為178.4 dB,其炮手區域超壓分布規律相同,但在炮手位置噪聲峰值水平上強裝藥監測點所得聲壓級高于標準裝藥;除此之外兩次模擬實驗中均在(4,1.6)處獲得最低聲壓級。
在垂直方向上對火炮發射沖擊波到達炮手位置時的噪聲分布規律進行研究,選擇(3,0.1)處為監測點,于此點建立垂直于地面直線進行分析,監測線段如圖11所示;時刻上選擇監測點壓力隨時間變化曲線壓力達到峰值的時刻,即t=50 ms左右。

對計算結果進行數據提取,結果如圖12所示,橫軸為數據監測點與地面垂直距離。可見強裝藥地面附近所得聲壓級高于標準裝藥,兩次模擬均表現出了相同的噪聲變化曲線,即隨著數據提取點與地面距離的上升,其聲壓值迅速下降。這是由于地面附近存在邊界層,靠近壁面附近的氣體流速較低,相比與地面有一定距離的流動區域其壓力更高;另一方面隨著與地面距離的增大,沖擊波影響力逐漸減小,在距地面較遠區域受到沖擊波影響較小,因此形成了如圖12所示的壓力分布規律。

4 結論
筆者通過動網格技術模擬了從彈丸出膛瞬間到膛口流場完全發展至炮手區域的過程,得到了不同內彈道參數下相應炮手區域超壓隨時間變化規律,從而通過分析內彈道參數與炮手區域噪聲分布的內在聯系,得到在實際發射中炮手區域噪聲分布規律,以便更好地保護炮手生理健康以及設備安全。從本文的數值模擬中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1)強裝藥工況下炮手區域所承受的噪聲峰值高于標準裝藥,噪聲峰值由177.6 dB上升至178.4 dB,這表明在155 mm-52D平臺發射工況下,炮手區域噪聲幅值的變化對內彈道參數并不敏感,但提升裝藥量使得炮手區域噪聲存在明顯上升趨勢,使得炮手及設備承受更大的危害。
2)在總體噪聲分布規律上,炮手位高壓區域集中于火炮模型對稱面及靠近地面區域,于炮尾后3 m處取得噪聲峰值;同理,遠離火炮對稱面、地面及炮口位置的區域承受噪聲峰值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