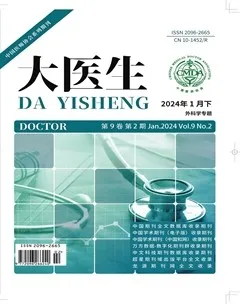中藥熏洗方聯合功能鍛煉在踝關節骨折術后康復中的應用研究
王華杰,何 杰,馬 林,周 峰,趙宇新,周 晨,姜紅波,楊中華
(泰州市姜堰中醫醫院中醫科,江蘇 泰州 225599)
踝關節作為重要的支撐關節之一,該部位骨折通常是由間接暴力引起,且在直接劇烈撞擊時會發生復雜性骨折[1]。據相關統計顯示,踝關節骨折發病率在成人骨折中約占6.8%[2]。手術復位外固定常用于治療單側內踝或外踝骨折,切開復位內固定術則應用于有移位的踝關節骨折[3]。為提高整體康復效果需要在術后實施康復治療,單純的功能鍛煉易出現關節疼痛、腫脹和不穩定的情況,會影響踝關節功能的恢復,無法滿足踝關節骨折患者的康復需求。中藥外用作為中醫常用的治療手段,具有止痛消腫、活血止血的作用,不僅可以促進關節功能的恢復,還可以減少關節僵硬的發生。但單一外敷無法促進其功能恢復,本文旨在將兩種方案聯合應用于踝關節骨折治療,深入分析其具體應用價值,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2022年9月至2023年9月泰州市姜堰中醫醫院收治的40例踝關節骨折患者,以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20例。觀察組中男性患者12例、女性患者8例;年齡22~68歲,平均年齡(44.25±6.82)歲;病程2.2~10.5 h,平均病程(6.11±0.42)h;BMI 18~28 kg/m2,平均BMI(23.11±2.14)kg/m2。對照組中男性患者11例、女性患者9例;年齡23~67歲,平均年齡(44.28±6.74)歲;病程2.2~10.5 h,平均病程(6.14±0.48) h; BMI 18~28 kg/m2,平均BMI (23.14±2.11) kg/m2。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組間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泰州市姜堰中醫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及家屬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納入標準:①符合裸關節骨折的診斷標準[4];②患者年齡20歲及以上;③均實施切開復位內固定術治療;④臨床資料完整;⑤單側損傷;⑥新鮮骨折;⑦閉合性骨折。排除標準:①存在病理性骨折;②代謝性疾病者;③嚴重臟器組織損傷者;④無法進行下地活動;⑤妊娠期及哺乳期婦女;⑥過敏體質患者;⑦術后切口感染者。
1.2 治療方法對照組接受單純功能鍛煉:①術后3周,由護理人員對患者身體情況進行詳細評估,同時指導患者及其家屬進行抗阻力訓練與肢體按摩,用手法作最大限度的屈伸、內外翻活動,以患者能耐受的疼痛為度,2次/d,30 min/次,療程1周,共3個療程。②術后4周,應用踩滾木的方法對踝關節內收、背伸、外展、跖屈功能進行鍛煉,2次/d,20 min/次。③術后5~7周,每天將踝關節最大限度地進行內收、外展、背伸、跖屈運動6~8次,踩滾木鍛煉2次/d,30 min/次。④術后8周,進行單純的功能鍛煉并囑患者遵守循序漸進的原則由無負重訓練過渡到負重、阻力、完全負重訓練。若在鍛煉過程中出現任何不適癥狀,應及時停止并即刻就醫。
觀察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聯合使用中藥熏洗方治療:①中藥熏洗方方劑為紅花30 g、蘇木30 g、花椒20 g、海桐皮20 g、艾葉15 g、桑枝15 g、劉寄奴30 g、透骨草30 g、制川烏15 g、制草烏15 g、伸筋草30 g。②將藥物放入紗布袋中,封口,然后放入3 000 mL水中煮20~30 min;取出藥袋,加入100~150 mL白醋,再次煮沸藥液;暴露患肢,用藥液蒸汽熏蒸15 min;當藥物溫度降至40~50 ℃時,將患肢浸入藥物15 min。早晚用干毛巾擦拭,每次持續30 min,3次/周。
1.3 觀察指標①關節活動度。術后第3、6周進行踝關節主動活動度測試,連續測量3次取平均值[5]。②關節功能評分。術后第3、6周分別參考美國足與踝關節協會(AOFAS)踝-后足評分對關節功能進行評價,分值0~100分,得分越高提示關節功能恢復越理想[6]。③疼痛評分。術后第3、6周參考視覺模擬量表(VAS)疼痛評分評價機體疼痛程度,分值0~10分,得分越高提示疼痛程度越高[7]。④炎癥因子水平。術后第3、6周分別采集患者空腹狀態下靜脈血3 mL,以轉速3 000 r/min,半徑16 cm,時間10 min進行離心處理。離心后以全自動生化分析儀(貝克曼,型號AU5800)測定白細胞介素-6(IL-6)、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⑤不良反應總發生率。不良反應包括皮膚過敏、傷口紅腫或滲出、疼痛加重等。不良反應總發生率=不良反應發生總例數/總例數×100 %。
1.4 統計學分析用SPSS 23.0統計學軟件完成數據分析,計數資料以[例(%)]表示,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者關節活動度對比術后3周,兩組患者背伸、跖屈活動度對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術后6周,兩組患者背伸、跖屈活動度較術后3周均升高,且觀察組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1。
表1 兩組患者關節活動度對比(°,±s)

表1 兩組患者關節活動度對比(°,±s)
背伸跖屈術后3周術后6周術后3周術后6周觀察組2010.28±2.1433.58±4.246.32±2.4216.54±2.66對照組2010.24±2.1127.55±2.926.72±2.4112.26±2.34 t值0.0595.2380.5235.402 P值0.953<0.0010.603<0.001組別例數
2.2 兩組患者關節功能對比術后3周,兩組患者AOFAS踝-后足評分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6周,兩組患者AOFAS踝-后足評分較術后3周升高,且觀察組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患者關節功能對比(分,±s)

表2 兩組患者關節功能對比(分,±s)
注:AOFAS踝-后足評分:美國足與踝關節協會踝-后足評分。
組別例數AOFAS踝-后足評分術后3周術后6周觀察組2031.44±4.8277.82±3.42對照組2031.42±4.6257.84±4.88 t值0.01314.994 P值0.989<0.001
2.3 兩組患者疼痛程度對比術后3周,兩組患者VAS疼痛評分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6周,兩組患者VAS疼痛評分較術后3周降低,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患者疼痛程度對比(分,±s)

表3 兩組患者疼痛程度對比(分,±s)
注:VAS疼痛評分:視覺模擬量表。
組別例數VAS評分術后3周術后6周觀察組204.91±1.651.16±0.12對照組204.92±1.721.34±0.26 t值0.0182.811 P值0.9850.008
2.4 兩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對比術后3周,兩組患者IL-6、TNF-α對比,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0.05);術后6周,兩組患者IL-6、TNF-α較術后3周降低,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均P<0.05),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對比(±s)

表4 兩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對比(±s)
注:IL-6:白細胞介素-6;TNF-α:腫瘤壞死因子-α。
組別例數IL-6(pg/mL)TNF-α(pg/mL)術后3周術后6周術后3周術后6周觀察組206.82±1.342.38±1.1135.25±7.2623.24±4.82對照組206.81±1.423.98±1.0835.22±7.1428.61±5.11 t值0.0234.6200.0134.418 P值0.982<0.0010.9890.002
2.5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總率對比觀察組不良反應總發生率與對照組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兩組患者不良反應總發生率對比[例(%)]
3 討論
踝關節結構復雜,在站立、行走、深蹲等運動中起重要作用,臨床治療踝關節骨折多采用手法復位,針對發生移位的關節進行切開復位內固定治療,促進踝部各功能恢復[8-10]。
中醫認為氣血供養筋骨,一旦患者出現氣血衰弱、局部瘀滯的情況,筋骨便發生活動不暢,筋骨損傷后需通過氣血供養才能恢復。因此,需要選擇活血化瘀方案,使全身的氣血旺盛,繼而疏通局部[11]。
本研究結果顯示,術后6周,觀察組患者背伸及跖屈活動度、關節功能評分均高于對照組,提示中藥熏洗方聯合功能鍛煉可提高踝關節骨折患者的康復效果。中藥熏洗方中大部分藥物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通過熬煮、降溫后擦洗,使藥物滲透至皮膚及組織內,達到活血化瘀、消腫止痛的目的,從而加快康復進程;功能鍛煉可針對患者踝關節情況提供康復方案,在增強肢體功能的同時改善臨床癥狀,二者聯合可達到協同作用,促進踝關節功能恢復[12-14]。
本研究顯示,術后6周,觀察組患者VAS疼痛評分、IL-6、TNF-α均低于對照組。由此可見,踝關節骨折術后康復應用中藥熏洗方聯合功能鍛煉可降低炎癥因子水平及疼痛程度,減少疼痛加重等情況,提高整體康復效果。與傳統熏洗方相比,中藥醋制的加入可增強活血化瘀、理氣止痛的功效,有助于提高熏洗的療效。與功能鍛煉配合,更能顯著緩解踝關節骨折術后疼痛、腫脹等癥狀,減輕局部炎癥級聯反應,降低治療后炎性損傷,在改善關節功能的同時,促進機體各功能恢復[15]。
TNF-α是一種細胞因子,在機體炎癥和免疫反應中起重要作用,踝關節骨折后TNF-α水平會升高,過高的TNF-α水平會對患者的預后產生不良影響[16]。而術后功能鍛煉是踝關節骨折治療過程中重要的一環,其可以促進血液循環減輕腫脹,加快愈合,同時功能鍛煉還可以調節機體的免疫反應,減少炎癥反應,從而控制TNF-α的水平。
綜上所述,將中藥熏洗方聯合功能鍛煉應用在踝關節骨折術后,可減輕機體炎癥因子水平,達到提高康復效果與安全性的目的,值得借鑒與實施。
但本研究仍因部分患者依從性較差、納入樣本數量有限、研究范圍較窄等原因,導致研究結果存在一定偏倚性,后期將結合不同骨折類型、傷情嚴重程度和個體差異等對研究方案進行優化,針對性解決研究不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