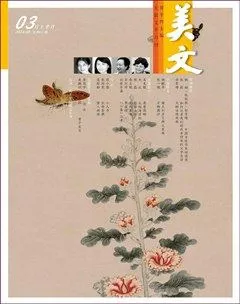“三秦”三老
在一磚頭就可能砸著好幾個“老總”的當下,你可千萬別以為“老總”都是些眼里只有錢、胸中無學識的家伙。如果你沿著厚厚磚頭包裹的西安明城墻的東南角散步,就有很大幾率碰到三位學識淵博、年高德劭的“老總”,他們都是住在對面的陜西日報社家屬院里的退休老頭。我之所以稱他們為“三秦”三老,是因為他們都當過三秦都市報的老總:宋總、高總為首任、第二任總編;戴總則是先后與他倆搭班子的副總編,退休前為執行總編。
宋總大名宋桂嘉,是從陜西省委原機關刊物《共產黨人》總編的位置上調任陜西日報副總編的。到陜報不久,他就帶領一幫人挑起為報社“開疆拓土”的重擔:創辦《三秦晚報》。雖然報名在正式“上戶口”時變為《三秦都市報》,但冠名國際體操邀請賽,評選振興陜西經濟最“火”的人,關注貧困大學生、都市貧困戶,以及一篇篇引起強烈社會反響的監督報道,使新生的《三秦都市報》聲名大振,很快成長為全國最有影響力的都市報之一。這其中,不知滲透了宋總及其創業團隊多少心血和汗水!在退休后創作的一首詩的引言中,宋總將報社同仁表現出來的奮斗精神總結為總編輯的“雄鷹精神”、記者們的“蜜蜂精神”、編輯們的“做嫁衣精神”。其實,身為總編的宋總不只有認準目標、不屈不撓的“雄鷹精神”,也有勤奮的“蜜蜂精神”和甘為人梯的“做嫁衣精神”。三秦報初創那幾年,年近花甲的他經常和年輕人一起加班加點、挑燈夜戰,甚至累到吐血。他十分愛惜人才,在位時,像老鷹護小鷹一樣,對幾個經常寫監督調查報道的記者關照有加,一旦“上邊”因某篇報道怪罪下來,他總是首先擔責,全力保護記者;退休后,他偶然看到一位大學畢業生的新聞作品,發現人才難得,找到三秦報人力資源部負責人,放下作品,只說了一句話:“我看這個娃水平比我都高!”果然,這位年輕人進報社后沒幾年,就獲得中國新聞獎。對于那些素質不高想通過旁門左道進報社的人,他一律拒絕。公開招聘記者編輯時,好多領導給他寫條子,宋總把官職最大的一位領導寫的條子裝在一個信封里,束之高閣;還有的人看找領導不靈,便帶著錢物去他家里,無一不被推出門外。不僅別人送錢送物不要,外出參加活動時偶爾收到主辦方的紅包,他也會偷偷交給辦公室。要求別人做到的,宋總總是首先做到。一次帶記者去山西出差,偶得空閑,不知哪位提議打撲克玩,輸者在床上翻跟頭。宋總不想掃記者的興,積極參與。幾位記者年輕,跟頭翻起來很容易。可偏偏宋總輸得多,翻得很吃力。記者就勸他別翻了,或者由他們代翻,可宋總說,講好的“規則”要遵守,堅持自己翻。別看宋總平時不打官腔,沒有架子,總是這樣和下屬打成一片,但編輯記者們都發自內心尊重他,有時還有點怕他。這一點,“吃瓜群眾”深有體會。有一次,幾位編輯加班時買來西瓜解暑,每一塊都是啃個大概就扔了,正好被路過的宋總發現,他盯著瓜皮嚴肅地說:“我吃的話肯定要把紅瓤吃盡的!”編輯們的臉登時比瓜瓤都紅。宋總還是一位郭小川、賀敬之式的詩人,他的詩歌主題向上、激情奔涌,有詩文集《心聲與腳印》行世。2019年1月,《三秦都市報》創刊25周年時,他寫了首題為“把沉淀的厚愛釋放出來”的詩,將對三秦報的愛盡情釋放:“年輕記者入伍履職/自然不那么熟悉老練/工作中出現差錯誰都難免/出了問題,我們一不推諉,二不抱怨/頭家們慣于推功攬過,把責任首擔”“保護記者的尊嚴和銳氣/是頭家們始終恪守的理念/因為實踐一再得出結論/有一個良好的人際環境/人們的積極性首創精神/也會來自內心的溫暖”。“頭家”大概是他老家的方言,即帶頭人之意。我將這首詩加了“編者按”,發于陜西日報秦嶺詩社的公眾號上,轉發者眾多。前些日子見到宋總,他剛從醫院回來,我詢問他的身體狀況,他摸了摸肚子,幽默地說:“這里邊‘腐敗的東西不少。”其樂觀豁達的心態溢于言表。確實,每個人的肉體最終都會“腐敗”,但總有那么一些人,能將閃光的精神留給后人。宋總就是其中一位。
高總大名高質一,出生于陜北之北神木縣(現神木市)的一個小山村。別看神木現在財大氣粗,那時可是窮得出了名。1948年陜北大旱,青黃不接之際,父母帶著年僅5歲的他和兩個哥哥逃荒要飯大半年,回來后實在無法養活,忍痛將他抱養給神木縣城的高鐵匠。于是,原本姓王的他開始姓高。多年后,當他大學畢業成為陜西日報榆林記者站的一名記者時,根據幼年的記憶,專門去尋訪過當年隨父母討飯時的路線,沙圪堵、伊金霍洛……留在記憶中的一個個地名,原來大部分屬于內蒙古。高總說,當年要不是養父收養他,他可能早就餓死了,他至今都時常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種饑餓的感覺。令我感到奇怪的是,饑餓的童年并未影響高總的身體發育,他反倒長得高大魁梧,年輕時可算得上百里挑一的帥哥。也正因如此,加上誠實厚道的品行,他到報社工作后,當時管理報社的空軍軍管會為討好“上頭”,竟把他的資料推薦到北京。原來,林彪夫人葉群正通過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在全國秘密選婿。后來,此事隨著林彪的叛逃殞命不了了之。雖然苦難歲月并未影響他的身體,但卻在他的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記。他待人接物總是低調、謙虛、善良。任三秦都市報總編后,按當時的規定完全可以用公車接送上下班,可他每天都是騎一輛除了鈴不響全身都響的自行車往來于單位與家之間。即使是公事,只要是在城區,他也經常騎著自己的“私家車”去。有一次騎車去開會,途經大差市的自行車和機動車混合道時,前邊一輛小車的車門突然開了,把他撞得摔了個“馬趴”,好在只是皮膚擦傷,他勉強站起扶起“坐騎”打算一走了事,后邊跟著的一位記者看不下去了,向小車司機吼道:“你咋開的車?這可是我們三秦報的總編,副廳級領導!”司機說:“你別嚇唬我,哪有這么大的官還騎自行車的?”也許正因為他過度的低調,加上當時的體制機制所限,他任總編的那幾年,雖然夙興夜寐、竭盡全力,但還是未能實現三秦報的“蝶變”。退休后,他被返聘到報社夜班做校檢工作,不知怎么就愛上了“挖坑”,隔三差五被幾個年輕人叫去玩這種撲克游戲,幾乎每場都輸,搞校檢掙的一點錢基本都輸完了。有一次,我在旁邊看他打牌,發現他的牌技還不如我,結束后便勸他:“‘挖坑是需要算計的,咱們一輩子不會給人挖一個小小的坑,玩撲克又咋能贏?您還是不要玩了。”他卻說:“我不來,他們幾個就湊不起攤子了。”他總是這樣,遇事先為別人著想。前段時間,當我上班路過家屬院時,發現他在長椅上獨坐,便邀他到我辦公室喝茶,他卻說:“你要工作,我不能去打擾。”在為紀念陜西日報創刊八十周年而出版的一本書中,他談到三秦報當年未能抓住機遇取得更大發展時,竟這樣寫道:“除了社會大環境及社內諸多環節上的因素外,我本人素質低下、經營無方、缺乏魄力,無掌控技能是造成重大失誤的原因。”還有誰能如此自省自責,在公開的文章里說自己“素質低下”?這種幾乎低到塵埃里的姿態,足以讓那些慣于搶功推責、自私自利的人矮下一大截!和站在鐵匠鋪里的養父一樣,他一生都在揮動一把道德的鐵錘,鍛造著自身高尚的品質。
戴總大名戴超,江蘇人,1964年大學畢業后先被分配到中央組織部,“文革”開始后又被“下放”到陜西日報社。他可謂是三秦報的“四朝元老”:宋總離任后,他又協助高總;高總離任后,他又先后協助過兩任總編。1999年到了退休年齡,主要領導還是不讓他離開,反而委以執行總編的重任。他只好跨世紀“服役”,直到2000年5月才退休。其實,此后他還是退而未休,先應邀擔任了《今早報》的高級顧問,后又應邀任《高新區導報》顧問。2009年初,他被推薦到省新聞出版局報刊審讀中心任審讀員,一干就是12年,先后審讀了八九個地市報,直至今年2月,年過八旬的他才算徹底休息在家。不知是因為思考問題用腦過度導致頭發脫落,還是因為頭頂“水土流失”之后考慮問題才更加細致縝密,反正我認識戴總時已是這般“絕頂”聰明、足智多謀的模樣,這也是他受多任領導重用、退休后仍然搶手的主要原因。大概是我入職三秦都市報半年后的一天,時任副總編的他突然拿著一篇稿件到我們特別報道部的大辦公室,徑直來到我的工位前,一邊把稿件遞給我,一邊說:“你把這篇稿件好好編一下。”我一看,原稿很啰嗦,根本夠不上發表水平,便用了大半天時間,幾乎重寫了一遍,第三天交給他,他看后說:“編得好。”稿件很快就見報了。他做了報刊審讀員后,有一次出差到榆林,報社在榆駐站的同志一起請他吃飯。席間說的話大多忘記了,只記得他談的與新聞寫作有關的一個問題對我啟發很大。而真正讓我感動的,是在我任《報刊薈萃》主編之后。我的辦公室在陜報那座沒有電梯、古色古香的辦公樓的最高層。有一天,好幾年不見的戴總突然來到我的辦公室,說他很愛讀《報刊薈萃》,自己要訂一份,還要給朋友贈訂幾份。我說:“給您贈一份,希望以后每期都能幫我們審讀審讀、提提意見。”其他的很快讓人辦理。之后,他隔段時間就來取雜志、聊聊天。疫情暴發后,看他戴著口罩氣喘吁吁的樣子,我說:“樓層高,今后您別來了,我讓人給你送去。”當時,為了陜西日報的整體發展,《報刊薈萃》更名已提上議事日程,但面對戴總這樣一位忠實讀者,我沒敢說這件事。直至2020年下半年,才連續兩次在卷首語中向讀者說明、致謝,我能想象他看到卷首語時的心情。當雜志正式改為《黨風與廉政》后,戴總再也未到我的辦公室。為了表達我的歉意,前不久的一天中午,我邀他和宋總、高總一起在報社附近吃飯。雖然他們三人中,年齡最小的高總也已近耄耋之年,但他們那天或多或少都喝了酒。為了活躍氣氛,五音不全的我還唱了陜北民歌。過了幾天,我又在家屬樓下遇到手提一袋饅頭的戴總,他說:“那天只顧著唱歌說笑,是不是忘記照相了?”我說:“是忘了,應該照幾張相片來著。”于是,久不作文的我便用文字來給三位老總“合影”。
《黨風與廉政》雜志社的辦公地址在標新街陜報家屬樓的一樓,每當我工作累了或遇到困難了,就會走出雜志社正門,仰望頭頂的高樓及其上空的藍天白云,很快就能精神煥發、力量倍增,因為三位“老總”都住在這兩棟家屬樓上。他們似養云的高山,仰之彌高;如垂蔭的大樹,望之彌大。《三秦都市報》之所以能不斷開枝散葉甚至被譽為報界“黃埔”,之所以能在報業市場如此萎縮的情況下逆勢而上,就是因為擁有從三位“老總”等老報人身上傳承下來的團結奉獻、包容拼搏的精神。這種精神,也是每個由“三秦”人執掌的報刊社生存發展的根與魂。
(責任編輯:李雪)
白居不易 本名白亮,曾在《人民日報》《詩刊》《延河》等全國50多家報刊發表散文、詩歌等文學作品,現為黨風與廉政雜志社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