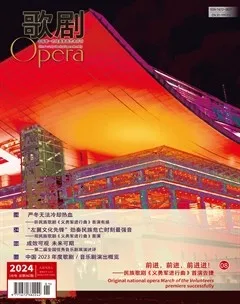如何在歌劇舞臺(tái)上制造“影視感”
丁丁

民族歌劇《義勇軍進(jìn)行曲》是講述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誕生的故事,因此創(chuàng)制意義重大。它誕生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關(guān)頭,凝聚著中華兒女“不做亡國奴”的怒吼。
初讀劇本,第一印象就是,該劇具有很強(qiáng)的影視感,好像在看一個(gè)快速切換的電視節(jié)目,目不暇接,連貫不停,帶著我從一個(gè)場景進(jìn)入另一個(gè)場景。
舞美設(shè)計(jì)的過程,如同解一道多元多次方程式。鑒于鏡框式舞臺(tái)的時(shí)空制約,歌劇演劇樣式的要求,20多次的舞臺(tái)場景變換,舞臺(tái)設(shè)計(jì)起來困難很大。這些場景,有戰(zhàn)爭場面、提籃橋左翼小組秘密基地、藝華公司和電通公司的攝影棚、“三友”式錄音機(jī)試聽發(fā)布會(huì)、左翼人士的家庭空間等等。
起先,我一直苦惱于這部歌劇情景多、變化頻繁、多時(shí)空并行(現(xiàn)實(shí)時(shí)空、心理時(shí)空、當(dāng)下時(shí)空和未來時(shí)空),且遷換需要快速高效,要有那種“召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感覺。但是,也正是這種限定,決定了這個(gè)戲的與眾不同。
本劇以紀(jì)實(shí)文學(xué)《起來——〈風(fēng)云兒女〉電影攝制與〈義勇軍進(jìn)行曲〉創(chuàng)作歷程紀(jì)實(shí)》為參照,表現(xiàn)的是電影歌曲的創(chuàng)作過程。“影視感”或許是求解的“關(guān)隘”,基于此,我在舞臺(tái)上創(chuàng)造了一個(gè)“鏡頭”,一個(gè)“zoom”。具體來講,就是在舞臺(tái)三分之一深處,設(shè)置了一組可以開合的硬質(zhì)灰色邊檐幕,在深度上可以分割舞臺(tái)空間,功能上保證前區(qū)演出時(shí)后區(qū)換景的遮擋需要。再配合地面車臺(tái),這樣就可以在不打斷演出的前提下,完成下一場景的遷換。
通過這個(gè)“鏡頭”的運(yùn)動(dòng),可以形成“全景”“中景”和“特寫”,來突出或弱化某個(gè)主體或場景,組成空間,同時(shí)傳遞信息和情感。當(dāng)它移動(dòng)時(shí),竟產(chǎn)生了影視語言中剪輯和切換鏡頭的通感,如同影視中以“淡入和淡出”和“閃黑”來表達(dá)時(shí)間、空間或情節(jié)的變化。場景自然而然地遷換,同時(shí)增強(qiáng)了藝術(shù)感和觀賞性,觀眾則如同觀看電影一般,不需要漫長地等待。
20世紀(jì)30年代的上海一直令我著迷,它是這座城市一個(gè)充滿矛盾和魅力的時(shí)代——嶄新閃亮的高樓大廈,裝飾藝術(shù)和現(xiàn)代主義并置。“海派”,定義了這座城市的時(shí)代精神,這體現(xiàn)在藝術(shù)、時(shí)尚、文化、文學(xué)、電影甚至烹飪方面。一方面,“東方巴黎”是當(dāng)時(shí)中國最富裕、最開放、最現(xiàn)代、技術(shù)最先進(jìn)的城市,是遠(yuǎn)東第一國際大都會(huì),光彩奪目;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國最混亂、最危險(xiǎn)的地方,還有獨(dú)容通仄的“下只角”、弄堂、石庫門,是被日本作家存松梢風(fēng)冠名的“魔都”。就在那個(gè)波譎云詭的時(shí)代,一批有家國情懷的熱血文藝青年正齊聚這里,以筆為槍,開展左翼文化運(yùn)動(dòng),號召全國人民同仇敵愾,鼓舞著大家堅(jiān)持抗戰(zhàn)的斗志。通過我們創(chuàng)造的“鏡頭”,配合布景,運(yùn)用豐富的視覺元素和手段,對上述背景和特征做了清晰的交代和精心的描繪。
這道開合的“鏡頭”,還是多媒體影像呈現(xiàn)的重要介質(zhì)。“風(fēng)云變化”是這部歌劇的主體視覺意向。多媒體設(shè)計(jì)師胡天驥,將“風(fēng)云密布”“風(fēng)雷激蕩”“風(fēng)起云涌”投射于其上,在舞臺(tái)上營造、呈現(xiàn)了孕育《義勇軍進(jìn)行曲》誕生的“風(fēng)云時(shí)代”。

由于場景多、布景數(shù)量大、燈位受限,燈光創(chuàng)作上難度極大。燈光設(shè)計(jì)任東升老師在創(chuàng)作中非常克制,力求和布景、服裝調(diào)性一致,濃淡得當(dāng),整體呈現(xiàn)出一種老膠片的質(zhì)感。
上海戲劇學(xué)院人物造型設(shè)計(jì)專家徐家華教授,通過服裝、化裝和細(xì)節(jié)調(diào)整,來塑造劇中的這一組“風(fēng)云人物”——既要嚴(yán)格遵循歷史真實(shí)、生活真實(shí),以人物的思想、性格、職業(yè)特征等為依據(jù),同時(shí)還要為這些歌劇舞臺(tái)上的人物,進(jìn)行造型上的藝術(shù)化處理。她在追求鮮明時(shí)代特征、地域特征、人物類型特征和個(gè)性的同時(shí),也注重歲月的厚重感和精良的做工。
這是中國的波希米亞時(shí)代,上海就好像黃浦江邊的法國蒙馬特,但戰(zhàn)亂時(shí)代的悲慘景象也隨處可見。這是何等對比鮮明、錯(cuò)綜迷離的世相。在“光”和“影”的共同作用下,我們在劇場里做“剪輯”,在空間上處理“蒙太奇”,讓“田漢”“聶耳”“王人美”在舞臺(tái)上上演他們的“藝術(shù)家生涯”。就像導(dǎo)演廖向紅在她的闡述里形容的那樣:“風(fēng)云時(shí)代涌現(xiàn)風(fēng)云人物,風(fēng)云人物演繹《風(fēng)云兒女》,《風(fēng)云兒女》孕生風(fēng)云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