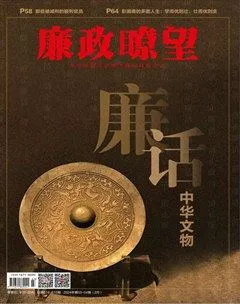揭秘宜賓“新水產”背后
許然

“個頭大的放這條道,小的放旁邊這條道。如果不好把握重量,就裝在這個小籃子里,放秤上稱一下。”春節前,在位于宜賓市江安縣的鰻魚養殖廠內,緊張忙碌的分揀工作正有序進行。
作為鰻魚養殖廠的管理者,江安縣七彩湖特種水產養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七彩湖水產公司”)總經理魏森告訴廉政瞭望·官察室記者:“像這樣的分揀每3個月就要進行一次,每次分揀要花半個月左右。分揀的目的主要是將大小相近的鰻魚放在一個池子,有利于控制養殖密度,讓其成長得更均勻。”目前廠里養殖的鰻魚達到300萬尾,分揀工作相對繁重。
作為江安縣的“新特產”,鰻魚產業從2017年落地到2019年投產僅用了不到兩年時間。而在與之相隔不遠的興文縣,當地的現代智慧農業產業園成功引進像澳洲淡水龍蝦這樣的新興水產品種。對此,不少本地人為之驚喜:“我們西南地區竟還有這些高端水產?”“終于能更便捷地買到這些鮮活的水產品了!”
驚喜的背后,又有不少人發出另一個疑問——這些看起來與內陸并不相干的水產品,是如何在當地養殖成功并集聚規模效應的?
與水產打交道,光有熱愛可不行
提起江安的鰻魚養殖基地,就不得不說其背后的推動人——沈明國。
沈明國既是七彩湖水產公司的董事長,也是海光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海光食品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在養殖基地落地前,沈明國就已在成都大邑開起了海光食品公司,對鰻魚進行深加工并出口銷售到日本、韓國、新加坡、俄羅斯等地。
“為研究一條魚,他可以說是耗費了畢生心血。”魏森如此評價他的老鄉與校友沈明國。
與鰻魚結緣是在1991年,當時達州師專畢業、只有18歲的達州人沈明國在福建找了一份工作。“那時只知道這家合資企業是做鰻魚加工出口的,至于鰻魚是什么樣的魚,我也沒深入研究過。”
作為公司的儲備干部,沈明國從生產一線的包裝組工人做起,先后經擔任班長、組長、部長等職務,直到1996年成為廠長。
“那時候年輕,就是一種對事業的熱愛。選魚、殺魚、烤魚,我樣樣都學,有時候一天要工作22小時。學得快,進步得也快。”沈明國告訴記者,看似快速的“成長”,背后都蘊藏著諸多不易。
“當時公司只有我一個四川人。尤其到了管理層,周圍更是沒有大陸人。感覺再往上走,也很困難了。留在公司,也只有停滯在生產管理這塊。”于是在成為廠長兩年后,沈明國做了個在外界看來大膽的決定——辭職。
憑借對鰻魚產業鏈的了解,他與朋友合伙做起了鰻魚產銷“中間商”的生意。“以前工廠主要是做出口。而我做的,就是把工廠經過深加工的次級鰻魚供應給國內市場上的一些連鎖日料店。”
“當時大概一年能賺個幾百萬元,市場前景還是比較可觀。”但沈明國并不滿足于此。在沈明國看來,與鰻魚打交道,光有熱愛可不行,還要有生意頭腦。只有形成一條集鰻魚生產、加工、銷售于一體的全產業鏈,才能實現自己的產業夢。
于是他做出一個最重要的決定——回四川發展,繼續在這條魚上做文章。
同樣決定把“海產”帶回鄉的,還有宜賓市興文縣潤億澳龍養殖專業合作社負責人李朝勇。“大多數人都以為澳龍只能生活在海里,事實上目前市面上很多都是澳洲淡水龍蝦了。因為個頭比較大,而且外形酷似海中龍蝦,又只生活在淡水,所以被稱為澳洲淡水龍蝦。”李朝勇向記者介紹。
“我在廣東養殖澳龍已經有10年。2014年就在廣東中山成立了農業公司,集澳龍育苗研發、專業養成、技術服務、連鎖銷售于一體。”李朝勇說。
原本李朝勇只是經營燈具產業,而之所以轉向水產養殖,是源于2013年的一次赴臺旅行。“當時去參觀了當地一個先進農業園區,對方就跟我們介紹說,‘這種蝦肉質好,還不含嘌呤,比海里的澳龍更好。”
“還有這樣的好事?也許可以養殖試試。”李朝勇和友人當即購買一萬只澳龍蝦苗,經過一個多季度,居然養殖成功了,且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在陸續又采購幾批蝦苗后,李朝勇嫌出關報稅等流程太麻煩,于是花300萬元一次性買下育苗技術,成立了農業公司。
“我就是土生土長的興文縣共樂鎮東陽村人,之所以回到家鄉,一是圓了老父親落葉歸根的夢,其次還是想帶著村里人一起發展。”李朝勇指著澳龍繁殖基地外的村道說,“這些路前些年都沒有硬化,這幾年有產業進來,基礎設施也變得越來越完善,村民們出行也更方便了。”
嗅到商機,轉向內陸布局
“其實內陸做水產并不比沿海差。沿海很多資源都已經飽和,用工成本也更高,把產業轉向內陸才能找到新的增長點。”沈明國說。
在決定回四川后,沈明國在“先建加工廠還是先建養殖廠”這個問題上犯了難。“先建加工廠的話,風險更低,盡管鰻魚的原料只能外購,但從這里加工后就可以直接出口。如果先建養殖廠,沿海的氣候與內陸相差較大,能不能大批量養殖成功還是個挑戰。就算能養殖成功,運往沿海加工,再運過來銷售,不僅有損耗,且運輸成本還更高。”
于是,沈明國決定在先規劃建設加工廠的基礎上,研究如何把沿海的鰻魚養殖經驗“移植”到內陸。
沒想到,這一鉆研就耗費了近7年時間。“鰻魚養殖的水溫要求在25℃至32℃之間,這個溫度在沿海是沒有問題的,所以沿海很多地方都是土塘露天養殖的,鰻魚的密度比較低,也不需要分揀。但內陸就不同了,氣溫與沿海相差大,所以當時內陸幾乎沒有鰻魚養殖企業。”
果不其然,在成都邛崍,第一批試驗的鰻魚苗幾乎全軍覆沒。“當時光是魚苗就花了300多萬元。更不用說試驗基地建設和聘請技術人員等方面的開銷。”
“鰻魚苗是不可再生資源,是漁民從海里撈的,所以貴的時候一條要賣到50元左右,便宜時也是20元左右,魚苗是經不起損耗的。”就這樣逐年的研究,從數據收集到論證投產,沈明國終于把影響鰻魚生長的三大要素——水量、水溫、水質研究透了,成功試驗出集約化的鰻魚養殖方法。
在養殖試驗階段,沈明國同步在成都大邑建設鰻魚加工銷售企業——海光食品公司,從養殖到深加工再到銷售的鰻魚全產業鏈正逐步形成。
試養殖的成功讓沈明國向大規模的集約化養殖邁步。可“在哪里養殖”這個問題又難住了他。
由于鰻魚養殖對水質的要求高,川內氣溫高的地方卻難以同時滿足水質和水量。經過多番選址,沈明國終于把養殖基地定在宜賓市江安縣。“當地是長江上游,水質好,氣溫也相對比川東、川北高。”
與沈明國不同,既有家鄉天然的氣候優勢,再加上興文縣又正在全力推進共樂壩2萬畝稻蝦產業標準化基地建設,李朝勇認為自己的返鄉創業,算是乘上了家鄉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東風。于是他干脆把澳龍養殖和培育基地就建在自己老家附近,方便照看和打理。
“從2020年開始考察,到次年進駐,包括基地建設,十分高效。”李朝勇說,由于澳龍養殖對水質的要求較高,只能放在精養塘養殖,一年養兩季,目前養殖了數十畝。
走進澳龍培育基地,記者看到4條用于恒溫育苗的流水線。“一只澳龍可以產1300多只蝦苗,單只蝦苗可以賣到兩塊左右,經濟效益比較高。”此外,李朝勇還流轉了800多畝土地,進行“水稻+小龍蝦”生態種養。“小龍蝦的養殖較簡單,只需要把蝦苗放在稻田就行。每年在冬季出售,主打一個‘反季節早蝦。”
聯動發展,串起產業“協同鏈”
“作為四川唯一的鰻魚基地,2021年成功上市了首批約100萬尾鰻魚,實現產值4000余萬元。”沈明國說,基地運行的第一年,便陸續取得水恒溫裝置、取水方法、鰻魚投食方法等多個創新專利證書。“對于這一系列的成績,我們還是比較驚喜的。”
經過3年探索,目前一期基地占地140多畝,養殖鰻魚300萬尾,年產量600多噸。在沈明國看來,盡管基地的養殖規模在西南地區已經是首屈一指,但這還遠遠滿足不了國外客戶的需求。“加工廠目前需要的原料達到3000噸,制成鰻魚深加工產品2000多噸。大部分原料還是需要從沿海購買。”
擴大養殖的需求被提上日程。“占地220畝的二期基地正在建設,主體工程現已完成80%。”魏森指著距離一期基地不遠的廠房告訴記者。在二期基地,養殖鰻魚的100多個水池已建好,水池周圍的保溫材料搭建完畢,等待入駐的,是供氧設備等,“預計今年投產,兩期運行正常的話,年產鰻魚量可以達到1300噸左右。”
據江安縣畜牧水產業發展服務中心相關負責人介紹,當地依托鰻魚產業,創建了江安縣水產現代農業園區。考慮到二期基地的用電負荷,當地對園區水利管網進行提檔升級,以滿足企業的需求,另外還修建了產業步道以及提灌站。
上述相關負責人介紹,當地還圍繞鰻魚產業規劃了一個占地3.3平方公里的“鰻魚小鎮”,將通過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實現鄉村振興。
為帶動村民致富,基地目前正在探索土塘養殖。“在現有產業基礎上,規劃采取‘公司+農戶的經營模式,聯動發展‘循環農業+稻漁輪作+休閑漁業。”江安縣陽春鎮黨委委員、統戰委員王小彬介紹,一旦土塘養殖能實驗成功,農戶便能更多地參與進來。
“土塘養殖鰻魚,周期更長,但成本更低。我們去年4月就在園區土塘中養殖了鰻魚苗,一年后根據鰻魚的長勢再作調整。”魏森說。
對于返鄉創業的李朝勇來說,驚喜也無處不在。在去年入冬前,怕冷的澳龍已經迎來兩次豐收。“每只澳龍約200克至300克,能賣到150元到200元左右。基本在宜賓本地就賣光了,完全是供不應求。”
等到澳龍賣完了,又開始賣“早蝦”。“物以稀為貴,年初的小龍蝦能賣到80元一斤。”李朝勇說。
事實上,李朝勇只是當地的稻蝦養殖大戶之一。興文縣現代智慧農業產業園區管委會主任吳遠松向記者介紹,近年來,農業產業園區陸續引進生態冷水魚、稻蝦養殖業主共358戶。目前,全縣稻蝦產業面積達6.2萬畝、產量達8500噸、一產產值達7億元。
“為了推動稻蝦產業發展,縣上還成立四川小龍蝦產業研究院、組建特色水產專班。在解決小龍蝦產業發展融資難題上,設立‘村資貸‘興蝦貸等金融產品。此外,也同步探索三產融合的方式,提升小龍蝦產業發展附加值。”吳遠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