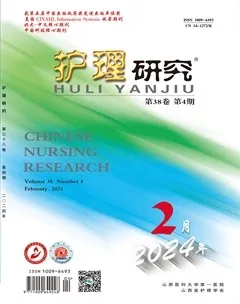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及主要照顧者疾病體驗的質性研究
趙月琰,繆群芳,仇凌晶,胡婷婷
1.杭州師范大學,浙江 311121;2.杭州師范大學附屬醫院(臨床醫學院)
抑郁癥是臨床常見的精神疾病,具有高發病率、高復發率、高自殺率及高致殘率等特點[1]。由于遺傳、生物學因素、家庭關系和人際關系等多種原因,我國抑郁癥病人逐漸呈現年輕化趨勢[2]。據《2022 年國民抑郁癥藍皮書》[3]調查數據顯示,18 歲以下的抑郁癥病人占抑郁癥總人數的30.28%,青少年抑郁癥患病率已達到15%~20%。有文獻顯示,青少年抑郁癥病人的癥狀與成年人相比更加嚴重,其會對病人身心健康、學業及社會功能等產生嚴重影響,甚至引發青少年自殘、自殺[4-6]。青春期是兒童到成人的過渡階段,也是青少年發育過程的特殊時期,青少年社會化尚未完全完成,且大腦額葉發育尚不完全[7]。所以,與成年人相比,青少年的解決問題能力、情緒管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對事物的洞察力和注意力都相對不足。主要照顧者作為青少年心身健康的第一責任人,挖掘并比較青少年抑郁癥病人與主要照顧者疾病體驗上的差異,對指導主要照顧者幫助青少年抑郁癥的康復有重要意義。國內在抑郁癥的研究上多采用量性研究方法,聚焦于疾病的病因、現狀、流行病學以及干預手段等內容[8-10],質性研究較少。在質性研究中也多關注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及其疾病體驗,缺乏對比青少年抑郁癥病人與主要照顧者在疾病體驗差異的研究,雖不同群體必然會在疾病的體驗上存在諸多方面的不一致,但是并非所有的疾病體驗差異都會導致疾病體驗感的降低。本研究僅對大多數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和主要照顧者共性的且會對家庭應對造成極大危害性的體驗差異進行討論。本研究運用質性研究方法,采用配對訪談分析法[11]和經典內容分析法[12]進行資料分析,達到更深層次挖掘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及主要照顧者疾病感知差異的內部具體原因,更好地豐富疾病體驗內涵的同時,為制訂針對該群體的精準干預和支持策略提供證據支持。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擇2022 年9 月—12 月在浙江省某三級甲等醫院兒童青少年心理聯合門診就診的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及主要照顧者為研究對象。病人納入標準:符合美國精神病協會編制的第5 版《美國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13]抑郁癥診斷標準;符合世界衛生組織對青少年的年齡界定(10~19 歲);能用語言清楚表達。排除標準:合并精神分裂癥、雙相情感障礙等其他精神障礙;存在物質濫用史及伴有嚴重軀體障礙者。主要照顧者的納入標準:年齡≥18 歲;為病人的父母或者近親屬;平均每天照顧病人時間≥6 h;能用語言清楚表達。排除標準:本人同時患有精神障礙;有明確診斷的嚴重慢性軀體疾病。采用目的抽樣的方法,研究樣本量以信息達到飽和為標準。最終選取12 對青少年病人及主要照顧者進行訪談。為保護受訪者的隱私,青少年抑郁癥病人用編號P1~P12 代替,一般資料見表1。主要照顧者用編號C1~C12 代替,一般資料見表2。本研究已通過我校倫理審查委員會的許可(倫理審查許可號:20190096)。所有研究對象均對本研究知情同意。

表1 病人的一般資料(n=12)

表2 照顧者的一般資料(n=12)
1.2 研究方法
1.2.1 確定訪談提綱
查閱大量文獻后,本研究以Leventhal 等[14]提出的疾病常識模型(common sense model,CSM)為理論基礎。Weinman 等[15]于1996 年根據疾病常識模型,結合疾病感知的五大因子,編制了疾病感知問卷(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IPQ),Moss-Morris 等[16]于2002 年將其修訂為改良版疾病感知問卷(the Revised Illness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IPQ-R)。隨后,Yan等[17-20]對IPQ-R 進行了翻譯,形成了中文版IPQ-R,并在修訂后分別應用于急性心肌梗死、創傷、乳腺癌等病人,經檢驗,問卷修訂后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目前尚未檢索到修訂好且經過信效度檢驗的適合中國青少年抑郁癥病人群體的疾病感知問卷,同時疾病常識模型多聚焦于病因和癥狀的識別。本研究在原有的疾病感知因子基礎上,更加注重家庭在疾病上的情緒感受和應對,在疾病常識模型的基礎上,結合本研究目的進行了內容補充,在咨詢了2 名本領域的心理學專家以及1 名資深主任護師后初步擬定訪談提綱,之后對2例抑郁癥青少年病人及其主要照顧者進行預訪談,根據訪談結果對提綱進行調整,最終確定訪談提綱。提綱內容包括:在您得知自己/您的家人患病后,您是怎么看待這件事情?在自己/您的家人患病后,這件事使您產生了什么樣的感受?您覺得在疾病治療中您的家庭生活發生了什么變化?您是怎樣應對的(日常關懷、親子交流、親子沖突)?您覺得在家庭生活中,你最期待能得到改善的部分是什么?
1.2.2 資料收集方法
采用個人深度訪談法收集抑郁癥病人及主要照顧者的資料。由1 名研究者對病人在訪談室1 內進行訪談,另1 名研究者對主要照顧者在訪談室2 內進行訪談,全程避免干擾。每次訪談時間為45~60 min,訪談室設在私密、固定的單獨房間,訪談環境安靜、整潔,確保訪談對象感到放松且舒適。訪談前向研究對象詳細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內容、方法,承諾用編碼代替姓名,保護受訪者的隱私,并對訪談過程中需要進行錄音對其說明,取得訪談對象的知情同意。訪談內容是開放式問題,不加任何引導和暗示。訪談過程中,訪談者始終保持中立態度,并做好同步錄音,訪談者對不明確的感受或觀點應及時澄清,以保證信息的真實性和完整性,確定訪談資料無新主題出現,信息達到飽和時結束訪談收集資料過程[21]。
1.2.3 資料整理和分析
訪談結束后,24 h 內立即回放錄音,將受訪者陳述的所有內容和研究者的現場記錄轉錄為文字資料,并由1 名研究者進行復核,如在轉錄過程中,發現內容缺失或對內容有疑問,立即向當事人進行澄清和核實。仔細閱讀所有的訪談記錄,提取有重要意義的陳述,對反復出現的有意義的觀點進行編碼,以Nvivo 11.0 軟件為輔助,結合Colaizzi 7 步分析法[22]進行資料分析,在分析過程中研究人員采用合眾法[23],由2 名研究人員分析同一份資料,并將整理后的資料返回被訪者求證,確保研究結果代表受訪者的真實疾病體驗,最終提煉出本研究的主題。
2 結果
2.1 主題一:疾病感知不一致
2.1.1 接受疾病身份的心理過程不同步
在受訪過程中,青少年抑郁癥病人與照顧者在接受自己或家人患病這個事實的心理過程存在差異,大部分的青少年表示自己能夠較快地接受疾病這個事實,而照顧者則會經歷復雜的心理變化,主要表現懷疑、否認、后悔。C3:“我們跑了很多家醫院,都說她是抑郁癥,但是我覺得青少年叛逆期也這樣,她可能就是青春期。”P3:“剛開始我覺得我生病了,我爸媽還不信,我想來看醫生,但是爸媽覺得我就是小題大做,說我不夠勇敢。”P6:“我本來覺得我得抑郁癥是一件很倒霉的事,為什么我周圍的人都沒事,就選中我得抑郁癥了。后來我也想通能接受了,得抑郁癥也沒什么,可能我就是比較特殊吧。”P5:“其實我不開心很久了,但是周圍的人跟我說不開心也是常事,他們也這樣,但是后來我發現我總是不開心,很低落。我其實心里就很確定我是生病了,所以醫院里確診我得抑郁癥時,我也不意外。”C7:“我覺得就是我害她得了這個病,當時我要是多聽聽多理解理解她就好了,也不至于現在這樣,我真是后悔死了。”
2.1.2 對疾病病因認識不一致
通過配對訪談發現,大多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和主要照顧者對于疾病的病因和誘因有不同的看法。P6:“我其實一點都不在意我爸媽的離婚,我覺得對我影響并不大,我比較在意的是我丟失了初一的那段記憶,我想不起來了。”C6:“在她小學的時候,我和她爸爸就離婚了,也沒有其他的啥特殊事件了,可能是這件事件對她的影響比較大吧。”C8:“后來我才明白這個是從初二的時候開始,不是說初三突發的一件事情就導致他抑郁了,他初二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他跟我說他過得很辛苦,但是我沒把那個辛苦當回事。”C4:“他就是手機玩太多了,天天盯著手機屏幕瞎想才生病的。”
2.1.3 對疾病的預后信念不同
不少照顧者對于抑郁癥的預后表示擔憂,而大部分青少年在疾病的治療過程中逐漸改變消極觀念,樹立起了克服疾病的信心。C9:“我現在就是怕他這個病以后還會復發,停藥了之后又復發,復發又吃藥。”C10:“我看有些小孩子來看幾次就好了,或者一兩個月就好了,我們家的孩子是不是好得慢了一點。”C12:“有些抑郁癥的小孩子突然就會自殺、跳樓,我怕他以后會不會情緒突然控制不住,也這樣。”P2:“我現在已經不會劃手了,心情不好的時候也會盡量控制自己,盡量想想開心的事情,感覺很快就能康復了。”P3:“我盡量不去擔憂一些以后可能會發生的事情,之前我會擔憂我以后該怎么辦。但是現在想通了,把當下的每一天過好就足夠了。”
2.1.4 對疾病產生的情緒感受不一致
部分青少年表示與照顧者之間存在代溝,照顧者會固守自己的思考模板衡量抑郁癥青少年病人。P7:“我跟爸媽說我難受的時候,他們就不當一回事,說我想太多了,叫我不要放在心上。”C5:“我看她平時好好的,只要不上學,一點問題都沒有。”P5:“我請假在家,一想到學校發生的事情,還是經常會很難過。”部分青少年表示會在家中隱藏自己的情緒。P6:“如果我開心的時候能達到100 分,那我現在估計差不多40 分。雖然我爸媽覺得我挺好的了,但這只是我想表現給他們看到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內心其實并不開心,很壓抑。”C6:“如果滿分是100 分,我看她現在的狀態應該有70 分。”
2.2 主題二:疾病應對中的家庭矛盾
2.2.1 溝通障礙
部分青少年抑郁癥病人認為父母無法完全理解自己的想法,進行溝通后,反而會給自己帶來麻煩或者增添父母的負擔,從而導致不愿溝通。P2:“我不開心的時候就玩玩手機,分散分散注意力,也不想說話,跟他們也無法溝通。”P10:“我有些極端的想法都不敢也不想和他們說,但是爸爸會追著我讓我說完,說了也只會讓他們擔心。”C10:“她現在有事我們能看得出來,但是問她也不說了。”P3:“我以前跟他們說過學校里發生的不開心的事,我叫他們保密,但是他們轉頭就對老師們說了,害得我還被老師叫去談話了一頓,本來沒什么事的,被他們一說事情更多了。”
部分青少年表示在與照顧者溝通的同時,照顧者的回答不僅可能達不到自己預期甚至會碰觸自己敏感點。C5:“她對很多事情都很敏感,我有時候都不太敢跟他說話,一說得不好,她就突然不開心了。”P1:“我想讓我爸媽也贊同我的觀點,也覺得老師有錯在先,然后同意我不去上課并且安慰我,但是她總是吧啦吧啦說一堆誰都知道的大道理,我的怒氣就又上來了。”還有部分青少年會選擇通過溝通上的沖突,抒發自己的負性情緒。P4:“我現在發現,我高素質的時候過得還真憋屈,現在我素質低了,哪里不爽,我就痛痛快快罵出來,頂話的時候還挺解氣的。”C4:“他現在情緒起伏挺大的,和以前性格好像都不一樣了,現在就屬于一言不合就開懟的狀態,有時候都不講道理了。”
2.2.2 過度保護或過度寬容
通過訪問照顧者發現部分青少年曾經有過自傷行為,甚至表露過自殺意念或自殺計劃,照顧者為避免誘發因素和應激事件的再次發生,減少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實行自傷自殺的概率,故而采取過度保護。P12:“我爸媽要求我到廁所就要把廁所門打開,走到房間就要把房間門打開或者不鎖門。我出門時間久了就要給我打電話,問我在哪里在干嗎。”C12:“我怕他想不開,因為之前他跟我說過他想死,他自己也吞過藥,所以我就很害怕。索性請了假整天在家里照看他。”P8:“我媽一天到晚問我開不開心,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說話也小心翼翼,感覺特別奇怪。”C11:“我就怕她想不開,所以出門啊,干啥啊,我都陪著。”
部分照顧者認為青少年的抑郁癥是由于自己導致的,從而內心產生愧疚感,并且大多數照顧者對抑郁癥疾病知識缺乏了解,擔心干預后青少年會有過激行為,增加青少年的抑郁程度或自傷的風險,故而采取過度寬容的方式。P9:“得了病之后。我爸媽和我姐姐就都很順著我的意思,什么都不管我,但是我內心也是很想讓他們管我的,也不是,我也很矛盾,但是現在這樣的情況我也覺得不舒服,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C10:“我們現在就是她想干什么就讓她干什么,就順著她的意思來,讓她心情好一點。”C3:“她現在不是生著病嘛,說到底也是我這個當媽的沒照顧好她,以前對她有所虧欠,現在想多彌補她一點,我對她也沒什么期望了,只要她開開心心健健康康活著就好了,其他的,當父母的能讓一點就一點吧。”P11:“現在我就說什么就什么,他們基本都會答應我的要求,跟以前簡直天壤之別了。”
2.2.3 照顧者關系不和諧
部分家庭在得知自己家人患病后,照顧者之間互相責怪,部分照顧者之間在照護溝通上結果不一致,導致對子女的要求不一致。C5:“她爸有時候生氣起來就怪我沒有把小孩子帶好,然后把所有的怒火往我身上撒。”P3:“他們兩個就是一個像太陽一個像下雨,就是你站在這個中間,你會很難受,你這邊是干燥的,這邊是濕的,很難受,真的很難受。”P3:“爸爸媽媽有時候他們自己倆說的話就不一樣,我都不知道聽誰的。”部分照顧者本身在照護過程中存在言語與行為不匹配的情況。P2:“我生病后,他們口頭上是說,只要我快樂健健康康,但每天還是催著我早點讀書。”
2.2.4 期待提供的照護內容不同
通過訪談發現,部分的青少年與照顧者間最期待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改善的部分存在不同。P1 :“我最希望得到的幫助是我需要個傾訴對象,我的同學都和我同齡,我覺得他們理解不了我,他們還很幼稚,跟老師說的話,馬上又要對我家長打小報告,我也很煩。對爸媽我就更不想說了,所以我壓根沒地方可以訴說。”C1:“他現在患病后,我基本每半個月帶來醫院做心理咨詢,然后聽聽心理師的意見,我也發現我自身存在一部分的問題,但是畢竟歲數大了嘛,有時候有些生活習慣也改變不了,這是我覺得最難辦的地方。”P4:“我想讓我媽多陪陪我,不想看到我爸,看到他就煩。”C4:“他爸以前經常出差到外地,現在他爸回來了,我也想讓他多陪陪孩子,畢竟也是他爸嘛。”
3 討論
3.1 提高青少年抑郁癥病人與主要照顧者疾病感知的相對一致性
1980 年,美國學者Leventhal 等[24]提出了疾病感知的概念,即病人面對疾病特征或健康狀態時所產生的總體認知與感受。這一認知結構對病人的治療信心以及采取何種應對措施治療疾病,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重要影響。本研究中青少年抑郁癥病人與主要照顧者在接受疾病身份的心理過程中不同步,可能與我國居民對抑郁癥等心理疾病的認知不足、心理健康核心知識知曉率、心理健康素養水平較低有關[25];也可能是因為青少年抑郁癥起病隱匿,容易與青春叛逆期混淆。本研究中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和主要照顧者在疾病病因上認識不一致,其主要原因是青少年抑郁癥病因復雜,抑郁情緒的出現可被多種因素誘發,增加了青少年抑郁癥病人與主要照顧者在誘因上的尤其是應激源上存在認識差異的可能性。提示臨床護理人員自身應加強專科知識的學習,護理部應定期開展健康教育培訓與考核,提高護理人員心理專科知識和技能,從而加強護理人員對于疾病知識宣教的能力,提升抑郁癥青少年和照顧者對疾病的科學認知,為他們提供更好的醫療保障。提示社會層面應加強對公民基本心理知識的科普。
另外,本研究發現,主要照顧者對青少年病情恢復存在不確定感,對其未來生活充滿擔心。其可能與抑郁癥病程長、易反復的性質有關。有文獻顯示,抑郁癥在緩解期無維持治療的前提下6 個月內的復發率約為50%,10 年內的復發率高達85%[26]。提示臨床護理人員在科普疾病知識的同時,也要注重幫助青少年病人和主要照顧者樹立克服疾病的信心和信念。青少年病人和主要照顧者情緒感受上存在差異的研究結果,提示臨床護理人員應鼓勵和促進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和主要照顧者交流彼此的真實感受和情緒,縮小在疾病感受上的差異。知信行理論指出,認知對行為的產生與改變具有重要作用[27]。因此,提高青少年抑郁癥病人與主要照顧者疾病感知的相對一致性至關重要。
3.2 臨床醫護人員幫助制定合適的個體化家庭應對策略
應對策略是指個體用來控制、容忍、減少或最小化壓力事件的特定的行為、情感或認知努力[28]。青少年抑郁癥病人普遍存在自我效能感低、無法堅持良好的生活習慣、自我管理能力低、遵醫性差等問題。作為青少年心身健康的第一責任人,照顧者的監督、教育、引導至關重要。本研究顯示,在青少年患病時大多數家庭應對策略出現問題。個人或家庭應對壓力源的方式可以減輕或加劇所經歷的壓力水平,積極的應對策略有助于疾病的轉歸。這提示臨床護理人員應為抑郁癥家庭制定整體的個體化的家庭應對策略,并以家庭為中心進行協同護理[29],減輕抑郁癥家庭的負擔,幫助主要照顧者提高照護能力并學到幫助抑郁癥青少年積極應對的方法。有文獻指出,臨床護理工作者應將病人主要照護者納入進來,以二元共同體為整體進行討論,引導雙方相互支持協作,緩解疾病應激,增強個體適應[30]。這提示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及主要照顧者應共同參與疾病應對,充分發揮家庭的整體力量。本研究中發現部分青少年抑郁癥病人的家庭環境中存在照顧者間的沖突。有文獻指出,存在父母沖突的家庭環境,兒童青少年的抑郁情緒明顯升高[31]。提示護理人員在關注青少年抑郁癥病人與主要照顧者的同時,也要關注照顧者與照顧者間的矛盾差異,了解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及主要照顧者的不同需求,及時提供幫助,促進青少年抑郁癥的康復。
4 小結
家庭是青少年成長最主要的場所,照顧者是青少年心身健康的第一責任人,抑郁癥青少年的疾病康復和主要照顧者對疾病的感知、應對密切相關。臨床護理人員應幫助青少年抑郁癥病人和其主要照顧者正確認知疾病,鼓勵彼此之間進行情感上的交流,以獲得應對疾病的策略,為抑郁癥青少年康復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