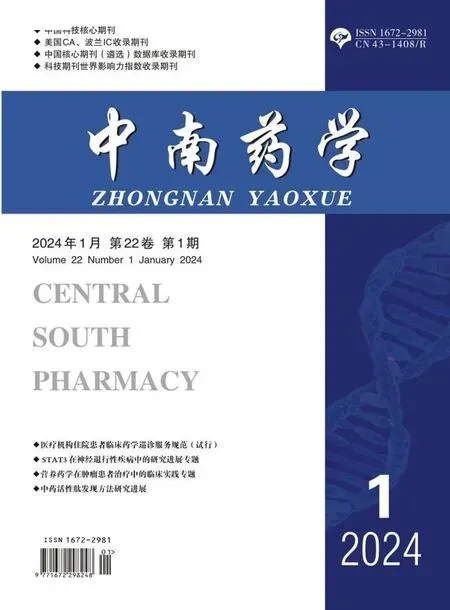中藥煮散的歷史淵源、應用特點及現代化研究進展
謝翡翡,盧曉瑩,何廣銘,葉聰,吳潤松,孫冬梅,羅文匯*(1.廣州中醫藥大學,廣州 510006;.廣東一方制藥有限公司/廣東省中藥配方顆粒企業重點實驗室,廣東 佛山 5844)
關健詞:中藥煮散;應用特點;現代化研究;質量控制;湯劑
近年來,人們對中藥材的需求急速增加,然而,原有的野生中藥資源面積逐漸縮減,導致藥價上漲,藥材質量下降,供需平衡改變[1],提高中藥材的有效利用率對中藥資源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中藥煮散是指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將中藥材粉碎成一定粒度,分裝或用時稱取,加入水或引藥煎煮,連同藥末一起或去渣服用的一種劑型[2]。2018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公布了《古代經典名方目錄(第一批)》,合計共100首方,其中煮散23首,此外有5首方(當歸建中湯、溫脾湯、溫膽湯、小續命湯、三化湯)雖定義為湯劑,但其制備工藝為先“?咀”或“剉”后再進行煎煮,實質也為煮散[3]。中藥煮散歷史悠久,其既保留了湯劑與水共煎的特性,又具有散劑的起效快、藥材利用度高和節省能源等特點,具有諸多應用優勢。
1 中藥煮散的歷史淵源
煮散是一種傳統的中藥煎法,其應用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時期,我國現存最古老的醫方典籍《五十二病方》便有“入三指一最(撮)”“(舂)桕中,煮以酒”的記載。《黃帝內經》中藥材的修治多為“?咀”,大顆粒入煎,且記載了“澤瀉飲”和“翹飲”的藥散用法,此時已始見煮散雛形[4]。
東漢時期,一些“湯、散、丸”的方劑制法與煮散高度相似[5]。張仲景所著《傷寒雜病論》中半夏散、瓜蒂散、抵當湯、防己黃芪湯等就具有煮散的特性,而《金匱要略》中對“煮散”的應用記載詳細,散劑于口服劑中的應用比例略高于《傷寒雜病論》,但書中并未予“煮散”之名[6]。東晉葛洪《肘后備急方》中亦有煮散記載,如用于辟瘟疫的“老君神明白散”。
龐安時《傷寒總病論》卷六中記載“唐自安史之亂,歷代戰亂,天災人禍,交通不便,月藥極多,供不應求,藥物緊決,為節約藥材,改湯劑為點散,以適時需”。“煮散”最早定名于唐代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其中含煮散16首,如丹參牛膝煮散、獨活煮散、茯神煮散、遠志煮散方等。《外臺秘要》中也記載了煮散25首,此時煮散的應用開始成熟,散常為“篩為粗散”,煎法上多“以綿裹”取汁服,開始將銼為粗末湯液制劑稱為“煮散”,并與一般湯劑及用細末沖服的散劑區別開來[4,7]。
《圣濟總錄》中記載“近世一切為散,遂忘湯法”,煮散的應用在宋朝達到頂峰時期,大量醫書中頻繁使用中藥煮散,包括宋代的三部官修方書《太平圣惠方》《圣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此外還有《小兒藥證直訣》《婦人大全良方》《博濟方》等醫籍。《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和《太平圣惠方》中煮散均約占總方劑數的30%,而在《婦人大全良方》和《小兒痘疹方論》中煮散占總方劑數的60%以上[8],此時煮散不僅廣泛應用于成人病患,還在兒科和婦科治療中發揮作用,宋代煮散的盛行與當時國家實行仁政、人口眾多和軍隊龐大造成中藥資源供不應求的國情息息相關。
因煮散以粗末形態入藥,與飲片相比存在“辨藥之難”問題,并且粗末經煎煮后易糊化、煎液渾濁等缺點逐漸顯露,故金元后煮散的臨床應用逐漸減少。明清以后,中草藥資源供大于求,藥材私營化,商人更青睞于生產技術成熟且易于辨認的傳統中藥飲片,煮散逐漸被飲片所取代[9]。
雖然中藥煮散的應用勢不如前,但仍有許多煮散被沿用至今,并顯示出良好的療效,如元代朱震亨《丹溪心法》中的玉屏風散等。近代有中醫名家蒲輔周、岳美中等人善用并鼓勵推廣使用中藥煮散,其中蒲老在治療各種慢性疑難雜癥時常用煮散,如應用四逆散加味治療肝胃不和,獲得了令人滿意的療效。此外,在《蒲輔周醫案》《蒲輔周醫療經驗》中均有許多煮散應用的記載[10]。歷代記載中藥煮散的相關醫籍見表1。

表1 歷代記載中藥煮散的相關醫籍[6,8]Tab 1 Relevant medical recor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owder for boiling in different dynasties[6,8]
2 煮散的應用特點
2.1 煮散與傳統飲片對比分析
中藥煮散以粉體形態入藥,質地均勻,與溶劑的接觸面積較傳統飲片大,藥效成分更易溶出,可節約藥材資源,且藥液性質穩定[11]。曹麗萍等[12]研究發現3批夏枯草精準煮散飲片的出膏率及迷迭香酸含量均顯著高于相同批次的普通飲片,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并且3批普通飲片的迷迭香酸含量存在明顯差異,RSD為28.17%,而精準煮散飲片的RSD僅為3.88%。翁艷鴻等[13]通過實驗發現29批不同產地澤瀉煮散的7種成分回收率的RSD在1.3%~2.3%,顯示煮散飲片的質量均一性較高。仝小林等[4]認為煮散比傳統湯劑節省1/2以上的飲片用量。俱蓉等[14-15]在對當歸精準飲片和傳統飲片中的4種指標性成分含量進行測定后,通過綜合加權評分發現,1 g當歸精準煮散飲片的效果大致相當于1.26 g傳統飲片,且精準煮散飲片中的4種指標成分整體含量較高;他們還比較了紅芪精準煮散飲片與傳統飲片中芒柄花苷、毛蕊異黃酮和芒柄花素3種成分的含量,結果發現1.00 g紅芪精準煮散飲片約相當于傳統飲片1.37 g。另外,有學者比較了澤瀉煮散及原飲片的煎煮得膏率,結果表明質地堅硬致密的澤瀉飲片制成煮散后得膏率明顯改善,藥材利用度大幅提升[16]。
蒲老曾言:“中藥煮散,輕舟速行。”中藥煮散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將有效成分浸出,同時避免了長時間沸騰可能造成的揮發性成分損失,如香豆素、萜類、苷類及揮發油等,進而導致藥效降低。劉月等[17]比較銀翹散煮散飲片及普通飲片的煎煮過程后發現,銀翹散煮散水煎液化學成分溶出速度較快,煮沸約5 min時,煮散水煎液中的非揮發性成分濃度已較高,意味著煮散可縮短煎煮時間,從而減少揮發性成分散失,提高療效。孫玉雯等[16]對比分析了19味根和根莖類藥材的煮散與飲片水煎液中有效成分的含量及得膏率,發現在煎煮10 min的情況下,煮散的有效成分含量和得膏率均不低于煎煮50 min的飲片。
綜上所述,中藥煮散具有“省、效、快、留、合、均”的優點,傳承和發展煮散可為緩解我國藥材資源緊張、實現中醫藥應用降本增效提供新的發展路徑。中藥煮散的具體優缺點分析見表2。

表2 中藥煮散的優點與缺點Tab 2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owder for boiling
2.2 煮散與散劑對比分析
散劑是常用的傳統中藥劑型之一,指將原料藥物或與適宜的輔料經粉碎、均勻混合制成的干燥粉末狀制,據2020年版《中國藥典》四部通則0115規定[18],散劑分為口服散劑和局部用散劑。口服散劑常分散在水、稀釋液或其他液體中服用,或直接用水送服;局部用散劑可撒布、涂敷,以及納陰、眼用、吹鼻、吸入、舌下含等多種應用形式。根據《本草綱目》記載,外用散劑多研為細末,撒于患處,起局部治療作用,或用麻油、蜜、酒、醋等調敷于患處。含有毒藥材的散劑常為外用,而無毒散劑常為內服。口服散劑的用量常為6 g以下,屬于固體制劑,實質是對中藥飲片全成分的應用;而煮散是湯劑的一種特殊應用形式,屬液體制劑,常為6~30 g,應用的是湯劑煎煮后溶出的成分。與煮散及傳統湯劑相比,口服散劑臨床應用范圍相對較小,口服散劑主要應用于不適于煎煮的礦物藥,如由“朱砂(研細入)、牛黃”兩藥研末吞服的鎮驚散[19];而煮散主要應用于植物藥,如藿香正氣散。
3 煮散的現代化研究
3.1 質量控制研究
中藥煮散的質量可控性是保證其臨床應用安全有效的重要前提,也是其研究、生產、應用和監管的重點。中藥煮散的粉碎工藝和煎煮工藝是影響其有效成分溶出和出膏率的關鍵參數,研究常以指紋圖譜、多指標成分含量測定及得膏率為檢測指標。孫玉雯等[20]通過實驗及統計分析發現粉碎粒度、加水量及煎煮次數對枳實煮散水煎液的指標成分含量和出膏率均有顯著影響。陳燕等[21]研究發現不同粒度的加味大柴胡湯煎液中化學成分存在差異,煮散飲片粒度在過4目不過10目篩,即為粗粉時各化學成分含量最高。張琦等[22]通過考察特征圖譜、相關特征峰面積及甘草酸、甘草苷得膏率對瀉白散“銼散”的粒度及煎煮工藝進行優選,確定粉碎粒度以過4目篩為宜,并優選出其煎煮工藝為置陶瓷鍋中,加水420 mL,武火煮沸后文火煮至300 mL。呼梅等[23]采用正交試驗,以五味子醇甲煎出量和得膏率為評價指標,對五味子煮散加水量、浸泡時間和煎煮時間進行考察,綜合加權評分后確定優化工藝為加20倍量水,無需浸泡,煎煮2次,每次15 min。不同粉碎粒度或不同煎煮工藝的煮散化學成分含量存在明顯差異,通過對煮散粉碎粒度和煎煮工藝進行篩選、優化有助于實現對中藥煮散的質量控制。
煮散飲片經粉碎后失去了性狀特征,傳統的鑒定方法已不適于煮散,DNA條形碼鑒定體系的出現解決了煮散的“辨藥之難”問題。陳士林等[24]開展了中藥精準煮散飲片的相關研究,采用中藥DNA條形碼鑒定體系聯合現有中藥質量標準評價和中藥指紋圖譜技術構建了精準煮散飲片質量控制體系,有助于煮散的精準化鑒定和檢測,此外精準煮散飲片還可通過二維碼識別溯源技術結合信息化技術對煮散飲片的流通信息和質量信息進行跟蹤查詢,實現中藥煮散飲片的生產全過程質量監控。張靖等[25]采用了中藥DNA條形碼鑒定結合中藥指紋圖譜技術比較了三七精準煮散飲片與其原市售飲片的差異,發現兩者屬性一致,但三七精準煮散飲片的得膏率、指標成分含量及質量均一性均更優,煮散飲片的臨床用藥精準性更高。黃娟等[26]利用第二內轉錄間隔區(ITS2)序列作為DNA條形碼實現了對丹參精準煮散飲片的精準鑒定,同時利用指紋圖譜對丹參原飲片及煮散飲片進行了化學成分分析,結果顯示煎出成分無明顯變化,指紋圖譜相似度較高,但煮散飲片的煎出效率更高。
3.2 藥效學研究
開展復方煮散藥效學研究是中藥煮散進入臨床研究的關鍵一步。近年來有不少學者對復方煮散進行了藥效學研究,為臨床應用提供了實驗數據和理論基礎,但藥效作用機制還需進一步探索。彭智平等[27]采用2型糖尿病SD大鼠動物模型,觀察不同濃度干姜黃芩黃連人參湯煮散與飲片對大鼠降血糖作用的影響,結果表明飲片組與煮散組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監測了3個月(0周、4周、8周)血糖的變化情況后發現煮散組血糖差異具有優于飲片組的趨勢,提示在同等條件下煮散工藝優于傳統飲片,并可節省約1/3等量飲片。張敏等[28]采用高糖高脂飼料聯合鏈脲佐菌素復制2型糖尿病大鼠模型,對模型大鼠服用葛根芩連湯飲片和煮散后對血清中內源性代謝物變化的一般情況、體重及空腹血糖進行比較,發現兩者均可改善內源性代謝物變化的一般情況、體重及空腹血糖,且代謝組學分析結果顯示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寧英海[29]開展了麻黃湯煮散與飲片湯劑的動物藥效學研究,對比分析了高、中、低劑量煮散與傳統飲片的解熱、止咳及抗炎作用,結果表明煮散與傳統飲片湯劑在解熱、止咳、抗炎等作用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煮散的藥材用量僅需傳統飲片的一半或更少。上述研究證明煮散在保留傳統湯劑藥理作用及臨床療效的同時,還具有節省藥材資源的優勢。
3.3 臨床研究
近代許多醫家如蒲輔周、岳美中等開始推崇“藥力盡出”的中藥煮散,煮散的臨床研究逐漸得到重視。葉亞銘[30]將茂名市中醫院收治的96例小兒支原體感染后咳嗽患兒隨機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進行了煮散三期分治的臨床效果研究,結果顯示與注射阿奇霉素的對照組相比,治療組的總有效率更高(P<0.05),說明煮散三期分治可改善小兒肺炎支原體感染后咳嗽的臨床療效。張力等[31]按照臨床對照研究的方法,觀察106例深靜脈血栓形成患者組成的血府逐瘀湯加味煮散組、血府逐瘀湯加味飲片組和抗凝組,比較治療前及治療后的局部癥狀、體征積分和凝血功能并計算總有效率,統計分析證明各組均可有效改善癥狀,且血府逐瘀湯加味對凝血功能影響及出血風險相較于抗凝組大大降低,說明血府逐瘀湯加味方可替代抗凝在臨床中應用,特別適用于長期抗凝治療。此外,有部分醫者利用多年臨床診療經驗將臨床常用方劑加減化裁并隨證加減,整理出運用中藥煮散治療的經驗方[32-34],在中醫藥治療中發揮了其獨到的作用。
現有多種慢性疾病采取西醫常規治療聯合中藥煮散辨證論治的治療方案,臨床療效得到了客觀證實。葛瑤等[35]將80例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收治的慢性冠脈綜合征合并D型人格患者按隨機數字表法分成治療組與西藥對照組,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加用枳殼煮散湯劑治療,研究結果顯示,與對照組(單純西醫常規治療)相比,治療組可提升慢性冠脈綜合征合并D型人格患者的臨床療效,同時還能有效改善臨床癥狀及情緒狀態,具有心臟與心理雙重治療的優勢。黃寶怡等[34]將80例脾虛濕蘊型高尿酸血癥無癥狀期患者按用藥情況平均分為參苓降酸煮散聯合非布司他片治療的觀察組和非布司他片治療的對照組,研究發現參苓降酸煮散聯合非布司他片治療脾虛濕蘊型高尿酸血癥無癥狀期患者效果確切,在改善中醫證候、降低血清尿酸水平方面的治療作用明顯優于單純非布司他片,并具有痛風發生率低及安全性較高的優勢。陳文輝等[36]通過實驗證明壯骨方煮散可改善脾腎兩虛夾瘀型絕經后低骨量患者的中醫癥候積分,緩解臨床癥狀,而將煮散聯合阿法骨化醇軟膠囊與碳酸鈣D3片治療可提高腰椎骨密度,提升骨量,且療效確切,不良反應少。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在西醫常規治療的基礎上聯合中藥煮散辨證論治大多具有良好的臨床療效和安全性,但仍需要大量基礎研究及臨床數據證明其臨床應用科學性,保障安全性和有效性。
4 結語
中藥煮散是一種傳統的中藥應用形式,既保留了傳統湯劑的優勢,又具有節省藥材、煎煮效率高等特點。煮散盛于唐宋,受當時技術及經濟條件的限制而衰于明清,經過數百年的發展,我國中藥制劑的研發、生產、加工等現代技術和質量控制與評價體系已逐漸成熟,中藥煮散具有巨大的開發前景。目前,中藥煮散的應用主要集中于各級醫療機構,經中醫臨床配方后使用,可以在保證療效的同時降低患者的醫療費用,適合門診推廣;中藥煮散的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植物藥,對動物藥和礦物藥較少。《蘇沈良方》中論,“湯、散、丸,各有所宜”,中藥材是否適合制成煮散飲片,應結合中藥材性狀、有效成分理化性質及生產制劑成本進行考慮。根據文獻報道,質地堅硬致密的藥材、根及根莖類藥材、使用上無特殊要求的皮類、莖木類及果實種子類藥材制成煮散可節省藥材用量或縮短煎煮時間,而對于質地輕薄的藥材如花類、葉類、全草類,還需與傳統飲片在相同煎煮條件下比較研究才可判斷是否適宜將其制成煮散[37]。
中藥煮散的現代研究仍處于探索階段,缺少標準操作規范和科學的質量標準,在制備工藝、質量控制和量效關系研究等方面還存在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煮散以粗粉形態入藥,藥材飲片粉碎后性狀消失、不利于鑒定,久置可能泛油、吸潮、氧化變色及氣味散失等,導致其質量不穩定。同時,含糖類、膠質類、蛋白質類成分的煮散飲片在煎煮過程中容易糊化、燒焦粘底,且藥液渾濁、不易過濾,影響藥效成分的溶出率及患者服藥依從性。鑒于此,建議在煎煮前進行粉碎,采取包煎的形式,加入大量水進行煎煮。然而,在相同煎煮條件下煮散與傳統飲片成方制劑的藥效存在較大差異,藥材或飲片制成煮散后的臨床使用劑量還未有科學的折算方法,目前煮散的臨床使用劑量主要依靠醫者的臨床經驗判斷,不足以保證煮散的劑量有效性和安全性。
傳承與發展中藥煮散還需要解決其“糊、渾、失、動、缺、量”的缺點,可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研究:① 以指紋圖譜、多指標成分含量及出膏率為指標,通過綜合加權評分優選出煮散飲片的最佳粉碎粒度和煎煮工藝,制定煮散的標準操作規范;② 從性狀、顯微、色譜鑒定、DNA條形碼鑒定、含量及水分測定等方面對藥材及煮散進行質量控制,建立科學、系統、可追溯的中藥煮散質量控制標準及評價體系;③ 加速開展單味煮散及復方制劑的藥動學、藥效學研究,同時進行大量的臨床試驗反復驗證,確定傳統飲片與煮散飲片組方最佳的劑量轉化比例或方法,保障其安全性和有效性;④ 與藥材或飲片對比分析,進行中藥煮散穩定性研究;⑤ 利用現代制藥工藝,經粉碎、制粒、干燥和分劑量包裝等工序制成單味藥或復方煮散顆粒,可減少調劑出錯率,且攜帶方便、便于儲存。如今,我國優質中藥材資源日益匱乏、藥價普遍上漲,傳承與發展煮散可促進形成中藥產業價值鏈和綠色供應鏈,實現中藥資源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