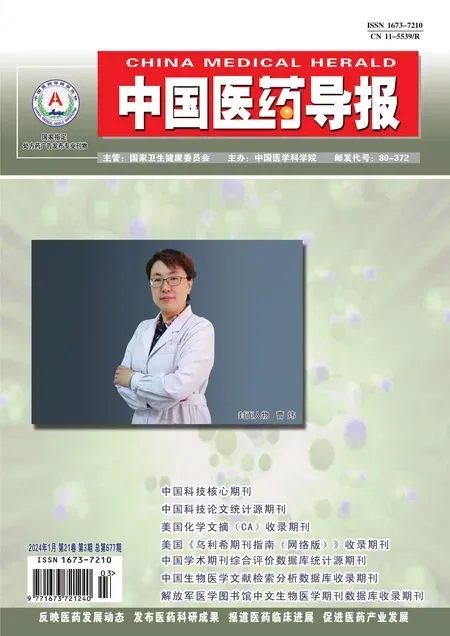腸道微生物療法干預孤獨癥譜系障礙的研究進展
鐘 佳 何麗云 趙寧俠
1.陜西中醫藥大學,陜西咸陽 712046;2.陜西中醫藥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陜西咸陽 712046;3.西安中醫腦病醫院,陜西西安 710032
孤獨癥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是一類多起病于嬰幼兒時期,以持續性的社交溝通障礙、重復刻板行為及興趣狹窄為核心癥狀的神經發育障礙性疾病,危害患兒健康,同時給家庭造成了嚴重的經濟負擔[1]。根據美國疾控中心最新篩查,8 歲兒童ASD 患病率為27.78%,且有逐年上升的趨勢[2]。目前,ASD 病因高度復雜,可能與遺傳、基因、環境、免疫等多種因素相關[3]。現尚無明確的病理診斷標志物及針對ASD 的靶向藥物,治療主要以改善癥狀為主,包括教育干預、行為矯正和藥物治療等。隨著“腦腸軸”理論的深入研究,腸道菌群失衡可能是ASD 潛在的發病機制之一。因此,筆者從腸道菌群出發,總結了腸道微生物療法的作用機制及最新研究進展,旨在為臨床治療ASD 提供參考方向。
1 ASD 與腸道菌群的聯系
構建大腦和腸道微生物組之間的雙向關系,稱為腦-腸道-微生物組系統,其通過神經、代謝、內分泌和免疫途徑進行交流[4],又稱“腦腸軸”。腸道微生物可由此影響大腦發育,造成認知、行為異常。研究表明,ASD 患兒患胃腸道疾病的可能性是正常兒童的24倍,尤其是腹痛、便秘和腹瀉[5];可能是由于ASD 患兒早期腸道菌群不成熟、不穩定造成的[6]。ASD 患兒的有益菌群豐度低,有害菌群豐度高[7]。Xu 等[8]研究ASD 患兒腸道微生物群豐度差異,發現嗜粘蛋白-阿克曼氏菌豐度較低。提示ASD 兒童腸道通透性受損。Plaza-Díaz 等[9]發現,ASD 患兒腸道中雙歧桿菌豐度較低,此菌可以分泌大量的γ-氨基丁酸(gama-aminobutyric acid,GABA),而GABA 與ASD 社交和行為障礙有關。另外ASD 患者體內梭狀芽孢桿菌濃度異常增高,其能釋放神經毒素,抑制神經遞質釋放[10]。對甲酚是一種由特定腸道菌株產生的芳香族化合物,Bermudez-Martin 等[11]發現,ASD 患兒體內對甲酚水平顯著升高,可能導致ASD 患兒的社交行為缺陷,對甲酚水平很可能被視為ASD 的生物標志物。
女性在妊娠期間,腸道微生物群能調節血液中生化物質和生長因子的利用度,支持胎兒大腦的正常發育[12]。研究表明,母親腸道微生物群的變化可能會增加后代患ASD 的風險[13]。Liu 等[14]基于一百多萬新生兒研究,提出了剖宮產分娩比陰道分娩具有更高的患ASD 風險。在嬰兒期和兒童早期使用抗生素會導致微生物生態失調,使腸道菌群種類和α 多樣性降低,可能會增加ASD 的易感性[15]。
2 腸道微生物療法
2.1 益生菌
益生菌被視為“活的微生物”,給予適量對健康有益[16]。益生菌不僅可恢復人體腸道微生物群的平衡關系,還能夠產生和運輸神經活性物質并作用于“腦腸軸”,改善大腦功能。如短乳桿菌產生的5-羥色胺(5-hydroxytryptamine,5-HT)、GABA,以及大腸埃希菌產生的多巴胺(dopamine,DA)[17]。補充羅伊氏乳桿菌和植物乳桿菌已被證明可顯著改善ASD 小鼠的社交行為,同時發現擬桿菌門數量減少與刻板行為改善有關[18-19]。Ad?güzel 等[20]研究發現,益生菌在改善丙戊酸誘導的產前ASD 大鼠的社交互動、焦慮和重復行為及增加白細胞介素(interleukin,IL)-10 水平有效,并逆轉了產前丙戊酸暴露降低的大腦前額葉皮層中的5-HT 水平。許多種類的益生菌已被用于治療ASD患兒,其中植物乳桿菌、嬰兒乳桿菌和長雙歧桿菌是最常用的三種益生菌[21]。Elisa 等[22]進行了為期6 個月包含8 種益生菌的干預,與安慰劑組比較,益生菌治療組的主要結局指標孤獨癥診斷觀察量表-校準嚴重度總評分顯著降低,益生菌不僅對ASD 胃腸道癥狀有改善,而且對適應性功能和感覺處理有積極作用。Liu 等[23]觀察了植物乳桿菌對我國臺灣地區7~15歲ASD 男性患兒行為的影響,結果顯示植物乳桿菌可以改善患兒破壞性行為及多動、沖動相關的癥狀。一項隨機對照試驗發現,益生菌對學齡前孤獨癥兒童腦電圖有所改變,表現為額極β 波段、γ 波段區域和額葉不對稱的改變[24]。提示大腦興奮性和抑制性神經元之間的不平衡得到了調節,從而可能改善ASD患兒的核心癥狀。益生菌混合物干預在ASD 患兒的相關行為癥狀方面比單一菌株益生菌干預更加顯著[21]。這可能是由于不同益生菌通過不同途徑同時起作用,以及他們的代謝物之間可能的相互作用,增強了原來的神經調節。Reichow 等[25]發現,益生菌可能對患有ASD 的年幼兒童的作用更顯著,ASD 患兒越小,病程越短,癥狀越輕,早期干預越有效。
2.2 益生元
益生元是被微生物有選擇地利用并有健康益處的物質[16]。益生元能刺激腸道中有益菌或益生菌的生長,改善腸道內環境。益生元通常與益生菌或飲食干預聯合使用。Alsubaiei 等[26]對36 只丙酸誘發ASD 行為的雄性小鼠開展了一項實驗,喂養益生菌鼠李糖乳桿菌和益生元木犀草素27 d 后發現,ASD 生化特征腫瘤壞死因子-α 和IL-6 顯著降低,緩解了神經炎癥,改善胃腸道癥狀和異常行為。在一項對26 例ASD患兒使用益生菌和低聚果糖干預的研究顯示,治療后ASD 患兒的孤獨癥治療評估量表和六項胃腸道癥狀嚴重程度量表評分顯著降低,高血清素能狀態和DA代謝紊亂得到了改善,揭示了益生菌聯合低聚果糖干預治療ASD 的潛力[7]。Grimaldi 等[27]對30 例4~11 歲的ASD 患兒進行了一項隨機雙盲對照試驗,首次評估飲食限制和益生元聯合療法對腸道中微生物的成分、代謝活性的作用,研究發現治療組(飲食限制和低聚半乳糖干預)的反社會行為評分明顯降低,顯示了飲食限制與益生元治療之間的協同效應。
盡管動物實驗已經廣泛證明補充益生菌和益生元可改善小鼠的ASD 樣癥狀和社會行為,但部分臨床試驗并不支持此結果[28]。ASD 模型小鼠是藥物等手段人工誘導的,人類ASD 的病因復雜多樣,具體機制尚不明確,出于倫理原因,一些用于評估小鼠相關指標的實驗不能用于人類。研究大多是通過相關問卷、量表等指標評估益生菌、益生元干預效果,缺乏可靠的實驗室指標。大多數研究的樣本量很小,證據總體有限,缺乏隨機對照試驗。目前試驗中菌株種類、濃度和治療持續時間各有差異,因此需要臨床研究進一步驗證并探索標準化干預方案。
2.3 糞便微生物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
FMT 是指將來自健康人的糞便微生物群引入患者的胃腸道中,以恢復患者腸道微生物平衡[29]。有研究顯示,ASD 患者的腸道微生物群定植可有效誘導小鼠特征性ASD 行為,且來自健康人的FMT 顯著改善了ASD 小鼠的焦慮和重復性行為[30]。FMT 處理可以恢復糞便梭狀芽孢桿菌的平衡,使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在海馬體中的表達正常化[31]。此外,FMT 還通過降低DA 水平和調節基因EphB6 缺陷小鼠內側前額葉皮層興奮/抑制失衡來改變孤獨癥樣社會行為[32]。Li等[33]開展了一項FMT 干預40 例ASD 患兒的開放性研究,治療分為4 周的FMT 治療階段和8 周的隨訪觀察階段,結果顯示ASD 患兒胃腸道癥狀、社交行為方面等得到改善,父母的焦慮水平也下降,治療結束后8 周恢復到基線水平,提示需要延長FMT 治療;同時發現口服或直腸FMT 給藥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Kang 等[34]對18 例ASD 患兒伴中重度胃腸道問題進行了一項開放試驗,治療方案為FMT聯合抗生素萬古霉素、奧美拉唑,研究發現胃腸道癥狀減少約80%,ASD 核心癥狀顯著改善;2 年后的隨訪提示,FMT 對腸道微生物群和自閉癥狀的作用仍在維持,證明了FMT 的長期安全性和有效性[35]。通過經結腸鏡導管向ASD 患兒注射洗滌后的糞便懸浮液,孤獨癥行為量表和兒童睡眠障礙量表評分均降低,并減少了全身炎癥[36]。FMT 后,患兒血清中的5-HT、DA 和GABA 濃度下降[33],對甲酚硫酸鹽水平與正常兒童相當[37]。表明FMT 也可以降低糞便代謝物水平。
關于劑量方面,2019 年我國FMT 標準化研究小組建議10 cm3是臨床使用的基本單位[38]。國外尚無標準菌量方案,關于FMT 治療ASD 的合適菌量、療程、給藥途徑和移植前是否需要預處理及預處理方式,還需大樣本量的試驗以進一步明確。
3 小結
ASD 已成為危害兒童生存與健康的公共衛生問題,隨著研究的挖掘,已經發現ASD 患兒的胃腸道生理異常,如腸道通透性增加、整體微生物群改變和腸道感染。此外,腸道菌群的改變程度與胃腸道和ASD嚴重程度呈正相關。可以通過腸道微生物療法,恢復腸道微生態平衡,干預ASD 的發生與進展。雖然前景看好,但至今尚未明確ASD 的發病機制與某種特定菌直接相關,當前證據也只是提示性信息,但可通過“腦腸軸”理論繼續補充和完善。腸道菌群、神經遞質與ASD 行為的相互作用機制還不完整,試驗缺乏長期療效資料,研究干預并未區分ASD 亞型,在未來,還需評估基于腸道微生物干預的治療效果和探索潛在的作用機制,制訂方案更加精準于不同分型,并追蹤觀察其長遠效益,從而構建體系化、標準化、全面化管理方案。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