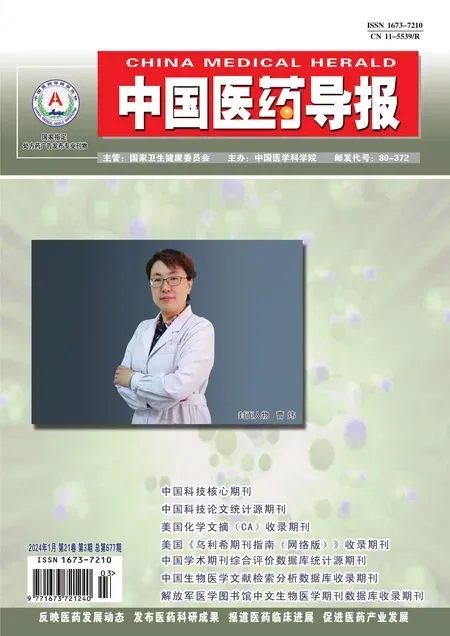早期家庭康復干預對單調性扭動運動早產兒神經行為發育的影響
張 雙 賈玉鳳 李 陽 高靜云 高淑芝 李 爽
河北省唐山市婦幼保健院兒童康復科,河北唐山 063000
圍生期醫學技術的進步使早產兒的存活率穩步提高,但早產兒神經發育缺陷的高風險仍然存在,其中輕度缺陷的患病率增加,給家庭和社會造成很大的經濟和社會壓力[1]。全身運動(general movements,GMs)評估是一種針對新生兒和小嬰兒的神經運動行為的評估工具[2];其結果為痙攣-同步或不安運動缺乏對腦性癱瘓有較強的預測價值,但單調性扭動運動的發育結局不具有特異性,對非腦癱早產兒的回顧性研究提示其可能與遠期認知發育障礙相關[3]。目前國內外針對單調性扭動運動早產兒的早期康復干預及轉歸的研究較少,且多為醫院康復[4]。故探索以家庭為中心的康復干預管理模式對有神經殘疾風險的早產兒有重要意義[5]。鑒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討早期家庭康復干預對單調性扭動運動早產兒神經行為發育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河北省唐山市婦幼保健院2022 年4 月至2023 年1 月兒童康復科門診GMs 評估結果為單調性扭動運動的64 例早產兒為研究對象。納入標準:①符合第九版《兒科學》[6]診斷標準,胎齡<37 周的早產兒;②GMs 評估為單調性扭動運動;③出生資料完整齊備;④患兒家屬簽訂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合并嚴重腦損傷、先天性心臟病、畸形、遺傳代謝病;②聽力、眼底篩查不通過。脫落標準:①干預及評估過程中發現嚴重疾病;②家長要求退出或不服從統一管理。本研究經河北省唐山市婦幼保健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2022-048-01)。
按照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干預組和對照組,各32例。兩組早產兒及父母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見表1。

表1 兩組早產兒一般資料及父母基本情況比較
1.2 研究方法
對照組行常規家庭護理指導,包括保暖、科學合理喂養、預防感染、皮膚黏膜護理及定期預防接種等措施。干預組在對照組基礎上,由康復治療師指導家長實施家庭康復干預,家長掌握之后返回家中實施干預。干預內容以發育支持性護理為主[7];并參考Poggioli 等[8]早產兒家庭康復干預指導。具體如下:①運動及姿勢管理。體位支持,讓早產兒自由地活動四肢,鼓勵練習穩定的仰臥、俯臥、側臥,在部分輔助下抬頭并促進雙手中線位運動。②豐富的多感官刺激。視聽覺刺激與追蹤,皮膚接觸(袋鼠護理),觸覺刺激(溫柔觸摸),早產兒按摩。③交流互動。注視眼睛、溫柔地說話、笑,尤其在哺乳、照護的時候;模仿早產兒的喃語并與其交流。干預的頻率和時間根據早產兒身體情況調整。訓練時間集中,動作輕柔,及時安撫早產兒情緒并滿足其要求。每天訓練2 次,每次15~20 min,實施12 周。治療師與家長建立微信群,家長隨時上傳家庭康復干預視頻或提出遇到的問題,每天至少有1 名工作人員負責查看視頻及監督指導。
1.3 觀察指標
1.3.1 GMs 評估 干預后采用GMs 評估評價不安運動階段結果。不安運動階段結果分為正常不安運動、異常性不安運動、不安運動缺乏。其中不安運動缺乏對腦性癱瘓具有較高的預測價值[9-10]。
1.3.2 Gesell 發育診斷量表 干預前后采用Gesell 發育診斷量表評價適應性、大運動、精細動作、語言和個人-社交行為五個能區發育商(developmental quotient,DQ)[11]。DQ>85 分為正常,75<DQ≤85 為邊緣狀態,55≤DQ≤75 為輕度缺陷,40≤DQ<55 為中度缺陷,25≤DQ<40 為重度缺陷,<25 極重度缺陷。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比較采用t 檢驗;計數資料用例數或百分率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 確切概率法。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干預后不安運動階段結果比較
兩組均未出現異常性不安運動患兒。干預組正常不安運動患兒31 例(96.88%),不安運動缺乏患兒1例(3.12%);對照組正常不安運動患兒32 例(100.00%)。兩組不安運動階段結果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1.000)。
2.2 兩組干預前后各能區DQ 比較
干預前,兩組各能區DQ 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后,兩組各能區DQ 均高于干預前;且干預組大運動、個人-社交行為DQ 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2。
表2 兩組干預前后各能區DQ 比較(分,±s)

表2 兩組干預前后各能區DQ 比較(分,±s)
注t1、P1 為兩組治療前比較;t2、P2 為兩組治療后比較。DQ:發育商。
3 討論
近年來,全球大部分國家和地區早產兒發生率呈上升趨勢,我國為7%~8%[12]。早產兒發生神經系統疾病的風險較足月兒明顯增高,如腦癱、智力障礙、語言障礙等[13-14]。故早期發現腦損傷風險并及時采取合理的干預措施,已成為醫療工作人員及家長所關注的重要問題。GMs 評估是預測嬰兒腦功能異常的可靠工具[15]。扭動運動階段表現為單調性扭動運動,其可能與認知發育障礙相關[3]。劉蕓等[16]以GMs 評估的結果對早產兒進行分級管理,其中對單調性扭動運動的早產兒進行選擇性康復治療和家庭康復指導,初步探索了超早期分級康復模式。
出生后3 個月是神經系統發育的關鍵時期,本研究以家庭為中心,指導家長提供豐富的感官刺激、誘導主動運動和姿勢控制、交流互動,并隨訪評估。干預方案的設計符合《NICU 出院高危兒0~3 歲生長發育隨訪管理技術的專家共識》[17]的要求,也與Peyton 等[18]提出優化高危嬰兒的神經運動健康4 個原則(主動學習、環境豐富、照顧者參與和基于優勢的方法)不謀而合。
本研究結果顯示,干預后兩組不安運動階段結果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Fj?rtoft 等[19]的研究指出,34~37 周胎齡開始的早期干預對早產兒不安運動或整體運動特征沒有顯著影響,這說明不安運動缺乏是由于永久性腦損傷所致,因此可以作為腦癱的早期預測指標。本研究隨訪評估出的1 例不安運動缺乏患兒及時轉為醫療康復和家庭康復結合的模式,突顯了GMs 評估在早產兒中的應用價值。本研究結果顯示,干預后兩組各能區DQ 均高于干預前;且干預組大運動、個人-社交行為DQ 高于對照組,與馬紅艷[20]、林春等[21]的研究結果大致相同。提示包含交流互動形式的早期家庭康復干預對單調性扭動運動早產兒的社會交往能力的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GMs 評估和Gesell 發育診斷量表的大運動能區評估的不同之處是GMs 評估評價的是運動的質量,而Gesell 發育診斷量表評價的是與年齡相適應的運動里程碑,家庭康復方案中的運動和姿勢管理可能對早產兒運動里程碑的發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兒童的社會性發展是心理、認知和社會情感的體現,也是個體適應社會必需的過程。研究表明,早期母嬰分離對神經發育有不良影響[22];早期較少的親子互動會增加社會性反應發育不良的風險[23]。早產兒在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的早期經歷使得他們在接觸刺激時比足月嬰兒表現出更多的回避、更難安撫,這些可能損害最初的親子關系[24]。因此,應當及時關注早產兒的社交情緒發育[25]。Festante 等[26]的研究也支持父母與腦性癱瘓高風險兒的早期互動對于促進嬰兒的認知和社會發展軌跡至關重要。
綜上所述,早期家庭康復干預對單調性扭動運動早產兒大運動、個人-社交及整體發育方面均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利益沖突聲明:本文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