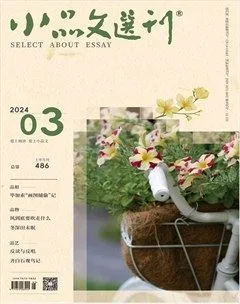那一碗麻油拌飯
彭生茂
我對芝麻的印象很深。那時母親還很年輕,她和村里的婦女們在生產隊的芝麻地里拔麻桿,我則與小伙伴們在附近玩耍。每個孩子的身上幾乎都沾滿了泥水,因為芝麻地挨著溝渠和稻田,青蛙等小動物出入其間。
生產隊收了芝麻,每家經常會分到一些麻油。那是在鄉下的榨油坊里榨的油,裝在一個透明的鹽水瓶子里,別提有多誘人了。有幾回晚上少了菜,母親就拿麻油拌飯給我們吃。香氣撲鼻的麻油,就像清寒歲月的潤滑劑,讓我們度過了一個個銹跡斑斑的艱難日子,也讓我們饑饉的童年多了一份美好回憶。
我對整個80年代記憶猶新。那時我突然多了一份使命——閑暇之時領著視力不濟的爺爺出門趕集或走親戚。我們經常穿越禾山街去江對岸的姑媽家,因此我對這條街道非常熟悉。早先禾山是個鄉名,與我們楓港鄉相鄰,為半丘陵地帶,墻上、樹上、電線桿上到處沾滿了紅褐色的泥巴。我喜歡禾山街古樸而濃郁的香氣——沿街的磨粉廠、制糖廠、榨油廠所釋放的氣味令人沉醉。我尤其喜歡那種從作坊飄出來的油香,它讓我疲憊的身心頓時輕松起來。事實上,禾山街還住著我的一個堂姑,長輩們都喊她寶香。每次路過禾山,我和爺爺總要到堂姑家歇腳,并吃上一頓飯。我喜歡吃拌有麻油的掛面,那是堂姑犒勞她叔侄的一道精美的吃食,多數時候她還會在面碗里臥上一個煎雞蛋。煎蛋黃澄澄的,比面條還誘人,大人們常常拿它就燒酒吃。
吃完飯的我和爺爺,告別堂姑一家便上路了。沿途的芝麻地開滿花朵,散發著淡淡的清香,蜜蜂嗡嗡地從眼前飛過,像一個個忙碌的信使。數月之后,芝麻成熟了,在烈日下張著嘴,空氣中隱約傳出噼里啪啦的爆裂聲。此刻我領著爺爺經過,免不了要停下來,摘下一個芝麻的果殼倒入口中,貪婪地品味著那香脆。那味道好極了,咀嚼的時候,似有一股油脂在嘴里流動。
“你摘了人家的芝麻吃吧?”爺爺聽出了身前的動靜。
“只摘了一個。”我吐了吐舌頭。遂將另一個芝麻殼藏入口袋,像揣著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爺爺在我讀小學四年級的時候便過世了。那時正值芝麻等旱地作物成熟的季節。山野浩蕩,一個草芥般的生命從此熄滅。大風淹沒了他的呼吸。是的,那是一粒生命的微光,它或將繼續在塵世間照亮真理和未卜的事物。
我從小喜歡看大人種地。小暑到來之際,天空接連下了幾場透雨。人們趕在泥土松軟之時種下芝麻。數天之后,地里便密布著嫩綠的幼苗。大概等幼苗的株高長到二十公分左右,人們開始對其進行間苗,這是為保證養分平衡和提高芝麻的產量。間苗的人往往要端著一個撮箕,將多余的葉子裝起來,繼而拿回家炒菜吃。鮮潤的芝麻葉子吃起來有種澀澀的味道,卻富含營養元素。那些年鄉下人很少得大病,其中無污染的綠色蔬菜為人們的體質提供了可靠的健康保證。還有那些清潔的水源和可供自由呼吸的新鮮空氣,它們是鄉下人唾手可得的黃金。
我懷念吃麻油拌飯時的艱辛歲月,它讓我的思想純潔,并充滿著對故土的深情。我更懷念初夏時節的芝麻花,它像瑞雪一樣潔白、玲瓏,鋪滿漫無邊際的原野。芝麻開花的季節是一年中最好的光景,泥土松軟,山巒清新,草木泛著河流般的光澤,映襯著樸素的人間。
選自《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