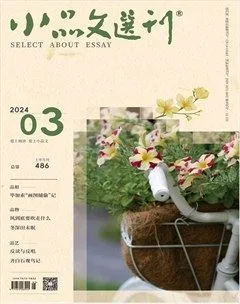年在“瘦身”
姚文冬
年,是個“大胖子”。它體格龐大,渾身“贅肉”,還“大手大腳”。
它的龐大身軀就是時間,從進入臘月到正月結束,似乎漫長的兩個月都在過年,使人盡興,也令人疲憊。年還不懂見好就收,直到被人嫌棄,才悻悻離去,臨走還用“二月二”的鞭炮,讓人恍惚一下。
小時候我雖然喜歡過年,但仍希望適可而止,只有年過去了,真正的春天才會到來。相比于人文的節日,我更喜歡自然的春天。參加工作后更加深了這種感覺,節后上班,單位的冷清(約定俗成,人們打個卯就回家,短時間工作難入正軌),大街上的寂寥,讓我頗為不適,因為我更喜歡庸常日子的熱火朝天,大街上車水馬龍的煙火氣。
年不僅只有除夕、春節,還有臘八、小年、元宵、老天倉、“破五”以及其他名目的民俗,這些“贅肉”似的小節日,各有各的講究,但在儀式上,也不過落實到吃上。有的人家,正月頻繁待客,餐桌的豐富甚至勝過年夜飯。原本對美食的享受,只剩下應酬的疲累。
年還“大手大腳”,多吝嗇的人過年也會松手,好像攢了一年的錢,就為了突擊花掉。所謂“年貨”,包含了太多的物質,吞噬了大量積蓄。直接送鈔票的,比如孝敬老人長輩、給孩子壓歲,也是一大筆。更有原本與年無關人情往來,也寄生在了年的身上,這部分消費,甚至超越了自家的年貨。曾有人抱怨,過了一個年,又把人過窮了。這話并不夸張。
過年,也不僅體現在吃喝與消費,各種具有儀式感的活動,諸如祭祀、拜年、走親,以及更具形象感的扭秧歌(各地風俗不同,僅以筆者家鄉為例),也使人腳步匆匆,閑不下來。
同樣是傳統節日,我更欣賞中秋的雅致,不過兩三日,有團圓的內涵,也有形式的美感。端午、重陽更簡潔,文化傳統沒丟,還“干凈”。同樣也稱之為“年”的元旦,更是過得干脆清爽。我不是說年不好,而是它不該過于臃腫,成為生活的負累。這并非危言聳聽。現在,有多少人對過年心生畏懼?
好在,年在一步步“瘦身”。綜合體現,就是人們常說的年味淡了。
那是年的時間在縮水,不到年跟前兒,的確聞不出年味。吃喝也失去了誘惑,誰盼過年是為了解饞?過去仿佛只有過年才能歇一歇的感覺,是不是平時也多了,各種新生活方式使人懂得了休閑是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更不必說,也不再集中于年前年后。而以前只有正月才有的扭秧歌,早已成為民間的日常活動,一年四季都有,而且似乎成了老年人的專屬。如今,早已不是放一部電影、唱一臺戲、扭一場秧歌獨攬節日精神生活的時代了。所以,年的誘惑還剩下什么?
雖說走親訪友可以凝聚親情,實際上,人們也心照不宣:一年沒走動的親戚,只憑問聲過年好,象征性買點禮品見個面,就能留住漸淡漸遠的人情嗎?所以,靠年來維系的關系并不牢靠。正因此,起初還被人排斥、受人非議的電話拜年、微信拜年等,已被人欣然接受。這也是年“瘦身”瘦掉的一部分。
年的這些“瘦身”,似乎也是隨著時代發展,水到渠成,是無意的,而有些方式則是有意的。還有一種有意的“叛逆”──吃過年夜飯,便舉家去旅行,什么拜年走親,這風俗那風俗,全當成生活的脂肪、贅肉,打包扔路上了。
所以說,年味淡了,其實是年在“瘦身”。“瘦身”后的年,會更健康。
選自《大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