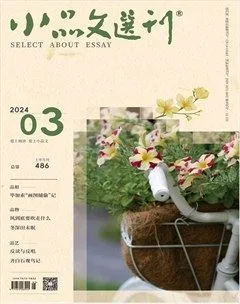難忘的記憶
馮連偉
現在的人們憶起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一個共同的感受就是貧窮,物質極度匱乏。
我家姊妹五人,大姐和我這個老小幾乎差了一代人,加上過去農村女孩子出嫁早,大姐有第一個孩子的時候,我剛剛七歲。那年娘把我送到大姐家看外甥女,是在我七歲那年秋天農忙的時候。那時候農村的小學除了寒暑假,還要在夏收秋忙的時節加放麥假和秋假。老話說得好:“三春不如一秋忙,收不到屋里不算糧。”秋收忙,忙得大隊的大喇叭早早地吆喝社員們早起晚歸去割稻扒地瓜。
我去給大姐看孩子,其實我也還是個孩子。每次出工的時候,大姐用獨輪小推車把我和外甥女放在筐里推著,到了田間地頭,我就負責看護外甥女。那時雖然生活貧窮,但家家孩子都不少,所以年齡相差不大的孩子挺多的。我在大姐家時間不長,就和一幫鄰居家的孩子混熟了。到了地頭,我就抱著外甥女和他們一起玩。有一次我一手抱著外甥女,一手好不容易逮了一個大肚子螞蚱,正好鄰居家的一幫孩子挖了個土灶在燒地瓜,我就讓他們把這個螞蚱給我一起燒熟。誰知地瓜還沒熟,螞蚱先熟了,鄰居家的小伙伴沒忍住,一口吃了。等我抱著外甥女趕過來,只聞到了螞蚱的肉香,螞蚱早進了小伙伴肚子。眼巴巴地看著就要進嘴的美味居然一轉眼沒影了,這真是希望越大失望就加倍大,委屈就更大了,我“哇哇”大哭的聲音頓時傳到了很遠,正在勞動的大姐和鄰居大嬸不得不過來安慰我。那天晚上,鄰居大嬸給大姐送來一個咸鴨蛋,讓大姐煮給我吃。這真是失了螞蚱,得了鴨蛋,賺大了。
在大姐家看孩子,回想起來印象最深的就是兩個字“累”和“饞”。現在去大姐家,走在村北的大路上,放眼看去一塊塊田地相連,沒有什么感覺這些地塊離大姐家有多么遠。但當時坐在獨輪車里,被大姐推著一步步走過來,感覺是那么遙遠。因為遙遠,出一次工就一直要到生產隊集體收工的時候才能回家,這四五個小時真是累啊。累的時候肚子就特別容易餓,因為那時的主食就是地瓜、糊豆、地瓜干、煎餅,配上辣疙瘩咸菜。吃飯時似乎撐得肚子溜圓,但沒有油水,幾泡尿下去肚子就扁了。早上有時能聽到大街上賣油條、豆腐的吆喝聲,中午頭在家里也能聽到老母雞下蛋后報功的“咯咯噠”“咯咯噠”的叫聲,可是大姐沒有那個經濟實力讓我吃啊。盡管手頭錢緊,但那時大姐還是千方百計去滿足我的愿望。有一天早上,大姐用干瓢挖了二斤多麥子去換了一小捆油條,又一天早上大姐又挖了半瓢黃豆去換了一斤豆腐,隔兩天晚上吃飯時,大姐又給我煮了一個咸鴨蛋。這在當時可都稱得上壯舉啊!油條外酥里嫩加之撲鼻的香氣令人陶醉,豆腐的清爽滑嫩甘之如飴余味無窮,讓我做夢都念念不忘啊。
選自《齊魯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