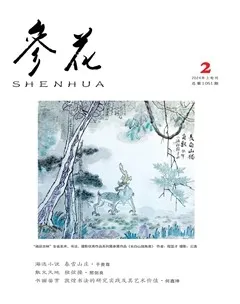兩代人的河(外一篇)
張正
我老家屬高低起伏的丘陵地貌。丘陵是丘陵,山區是山區,長期以來,老家人卻喜歡自稱是山區人。老家僅有土崗、矮山。山區,大概是相對于南面長江邊一馬平川的圩區而言。山區人戲稱圩區人為“圩鴨子”,圩區人戲稱山區人為“山雞子”,這是我后來到圩區教書時才知道的。
圩區河網密布,港汊眾多. 山區卻少水,缺少大江大河,叫法也特別,不規則的小面積的水,叫小汪子;面積稍大的,叫塘;更大的,是人工筑堤;攔截雨水形成的,叫水庫。近年來,為配合鄉村旅游發展的需要,水庫也有了“高大上”的名字,叫湖。我再熟悉不過的,是老家鴨嘴橋水庫,現在更多人叫它登月湖。
老家很少有細細長長的河。即使有,也不可能一線貫通,而被一道一道的壩截斷。壩常常也是橋,所以后來聽到有地名叫“小橋壩”,我立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橋或壩的兩側,水位高度大不一樣,雨水豐沛的季節,水從高處往低處沖下,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枯水季節,也可能有清亮的細流不疾不緩地流淌,如同山澗溪水潺潺。真正的枯水時日,橋下可能是干涸的,露出水泥勾縫的石塊斜坡,上學、放學途中,成了我們躲避老師、家長視線,集體貪玩的好去處。放哨的同學遠遠地看見老師從學校方向走來,匍匐在河坎探出半個腦袋,第一時間報告,橋下大家立馬慌作一團,很快擠在橋面上看不見的死角,屏息噤聲。等老師從橋面咚咚地走過,走遠,橋下又熱鬧依舊,歡笑如初。
我和父母居住的尹家山莊小區,西側的小河是村里唯一的河,水面細長,寬一二十米,長兩三公里,北達張良水庫,南接登月湖。這是一條人工河,以我的年齡推測,它開挖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有五十歲左右。父輩們人工開挖這條河的情景,我依稀有點印象。當時動員了全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場地彩旗飄,喇叭響,規模盛大,氣氛熱烈。任務分到大隊,大隊分到小隊,每個莊一段,下木樁做記號,木樁頂端刷紅漆,區別于放線取直的普通木樁。岸很陡,女工打鍬,男工挑土,上坡非常吃力,身子須前傾,一步一步踩實了爬,防止后仰、滑倒,號子聲喊成一片。我們尚未入學的小孩子,坐在河埂上避風的地方看,大人不允許我們亂跑,怕我們妨礙大人干活,又怕我們滾下河埂。大人干得熱火朝天,出汗了,脫下棉襖,墊在我們小屁股下。我們困了,天當屋,地當床,裹著父母的棉襖,呼吸著棉衣上父母的體味,一樣睡得香甜。隔一兩年,還是差不多的規模,整理河兩岸的農田。把一小塊一小塊高低不平的耕地,整理成一大片一大片寬廣平坦的田塊,便于耕作。這項工程,那時有個專門名詞,叫“土地方整化”。秋冬農閑季節,這樣大規模的農村集體勞動,叫“上水利”。這大概是我幼時能記住的少有的幾個時代“熱詞”。
這條河帶給我們小孩子最大的快樂,不是夏日洗澡,也不是假日釣魚,而是摘桑椹。那時,農村倡導植桑養蠶,高高的兩岸河埂上植滿了桑樹。那桑樹,比家前屋后自然野生的矮壯,桑葉要闊大鮮嫩許多,桑椹果也個兒頭大、甜汁多。到了季節,桑樹枝條上墜滿了紫紅的桑椹,伸手即能摘到,吃得我們小嘴烏紫。小孩子貪心,吃不完的用衣袋裝,結果,白色的確良襯衫染成了花褂子,被家長罵,說我們糟蹋了會客的好衣裳,放學后不及時回家放牛、打豬草,路上貪玩。從學校到小河邊,再回家,路線不在一條直線上,近乎一個等邊三角形。
剛搬進尹家山莊小區集中居住時,我看過遠期規劃,知道小區旁邊將有一條景觀河,原以為是將這條小河拓寬改造升級,實際卻是在小區南側另開挖一條人工河。沒多久,不聲不響,那條河已成形。景觀河項目承包給工程隊,全是機械作業,一天一個樣兒,快得很,完全不是過去勞師動眾“上水利”的情形。新開挖的河叫尹家河,非常美,河面及河兩岸建有漫步道、半潛水橋、棧臺、親水平臺、涼亭、膠木座椅、入口廣場、路燈、音柱等許多配套設施;東連鎮區,西貫登月湖,有專人管理。一年四季,河水清澈,波光瀲滟,入眼皆景,實為一座生態公園。這里很快吸引來附近居民在入口處跳廣場舞。黃昏后,她們早早吃過晚飯,從四面八方聚集來,站成行,排成列,伴著高亢激昂的現代音樂,如癡如醉地扭動身姿。
路燈高高亮起
廣場舞歡快跳起
音樂聲蓋過蛙鳴
歡笑聲勝過蟋蟀吟唱
樹葉在晚風中舞蹈
黃花鳶尾在水塘邊守望
五月新荷凌波蕩漾
古老的月亮哪去了
害羞了還是因為那一盞盞路燈
起了醋意
登月廣場上
每一盞路燈都是一枚月亮
無數枚啊
在天上,在水中,在春風里
在我們鄉村的新生活里
春夏之交,我觸景生情,寫了這首小詩《鄉村夜景》。我經常陪家人來尹家河邊散步。年邁的父母細說著這里原來什么模樣,誰家住哪兒,有時記憶出了差錯,意見有了分歧,老兩口還要爭執一番。我對他們談論的內容通常興趣不大。我們之間隔著一道代溝。這代溝,關乎歷史與未來。他們習慣于把目光停留在昨天,那是彼岸;而我,更多地喜歡暢想未來,這是此岸。
我們向西,走到尹家河盡頭,不遠處即是登月湖,父親望著登月湖的方向說:“過去,要是沒有這些水庫、小河,莊稼望天收,種田人連肚皮都忙不飽。”
“上水利”的艱辛,母親刻骨銘心,至今難忘。她感慨的,是他們那一代人年輕力壯時那些艱巨的體力勞動。
“過去挑河,是為了解決溫飽問題;現在挖河,主要是為了美化環境,河跟河不一樣。”我難得接住他們的話題,又感覺我這樣說,有點欠妥,因為兩代人的河,肯定在許多方面是相通的。改天換地,目的始終一樣,都是為了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
時至今日,社會發展日新月異,許多新生事物給我們的生活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對于我們這一代人,是幸運的,更是幸福的。而有些事又例外,比如,我愛煥然一新的尹家河,那里卻因為缺少歲月的“包漿”,不能勾起我的興趣,我仍然喜歡獨自去原來的那條小河邊走走、看看,讓思緒回到從前。于我,原來的小河是有記憶、有歷史的,有我童年的蹤跡,留得住鄉愁。或許,尹家河生態公園里的一切,也能給今天的孩子留下抹不去的印象。這是分屬于不同時代,分屬于兩代人或幾代人的河,都是“幸福河”。將來,不管他們漂泊到何處,故鄉的美好都豐饒地貯存在記憶里。
這個季節,原先的那條小河兩岸,長滿了壯碩的狗尾草和水蓼、鴨跖草等許多嬌艷的小野花。河床淤淺了,荇菜、菱角、雞頭蓮漂浮在水面,魚兒不時甩出圈圈水花。而新的尹家河,兩岸金絲柳、紫葉李、觀賞桃、香樟等,間隔著整齊排列,郁郁蔥蔥,平整的坡埂上也人工種植著茂盛的三葉草,綠得純凈,透著一股年輕、現代的美。兩條河的岸邊,都有垂釣者,或站立或端坐,氣定神閑,不時提竿,屢有收獲。
撈殘荷
小區外北側的蓮花塘,差不多每天我都要經過幾回,有時是接送孩子上學放學,有時是沿著岸邊散步。秋高氣爽時節,我還喜歡坐在岸邊的膠木休閑椅上,坐在荷香里,讀幾頁書,或是推敲自己新寫的文字。偶爾抬頭,也癡癡地吟著“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走著走著,讀著讀著,天氣變涼了,變冷了,滿池的荷葉不再是迎風搖曳的綠色,蕭條成了一枝枝靜默矗立的殘荷,一律枯褐色,一律蔫頭耷腦。依然綠的,是水面的浮萍,因為少了荷葉的遮擋,反而像得了勢,綠得更加恣意張揚,鋪天蓋地,幾乎覆住了水面的全部,不留一絲縫隙。
在我眼里,殘荷的墨色也是風景,可入詩入畫,何況還有翠綠的底色做鋪墊。我還是每天經過蓮花塘幾次。天氣晴好,沒有風的日子,我還是喜歡攜一本書或幾頁草稿,在岸邊小坐。我是喜歡這個地方的。此情此景,適合思考,最宜賣呆。
某一天,蓮花塘的某一區域,被橋和路隔成了至少四個區域——空蕩蕩的,不見了那些殘荷,也不見了那些翠綠的浮萍,取而代之的是一池清澈的泛著粼粼波紋的碧水。
我心中驀地生出悵然若失的感覺:那些枯荷和浮萍呢?同樣失落的,該還有水中央幾只相互追逐嬉戲的黑色野鴨,“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丑枝”,那是另一個季節的景象,現在,沒有了殘荷和浮萍的陪伴,它們也少了不少樂趣吧。
又一天,我沿著蓮花塘北岸向東走,我終于見到了正在清除枯荷與浮萍的人。他們一律穿著及胸的背帶式灰色皮衩,有男有女,有坐著藍色塑料小船在水中的,也有拿著不同工具在岸邊的。他們的工具不止一樣兩樣,有網兜,有小船,有鐵叉,有鐮刀等。岸邊,不時出現一堆他們的勞動成果——清除后集中在一起的枯荷、浮萍,還有野生的蒲草、茭白、芡實等。
是誰安排他們做這項工作的?“秋陰不散霜飛晚,留得枯荷聽雨聲”,難道他們不知道殘荷也是一道風景嗎?這項工作的組織者,是不是缺少了某種情懷?那一刻,我心里生出一絲幽怨。我不理解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做。當然,我心中的不滿很快又消失了,又化作對眼前勞動的理解和贊美。
在水中,坐在小船上清除殘荷的人,我原以為是一根一根地扚去,實際卻不是。他們手上有一把長柄的鐮刀,先探進水里,兜底割斷仍舊有力的荷莖,再用鐮刀鉤到面前,伸手逐一撈起,放在身后的船艙里。那殘荷,我們看到的露在水面的部分也許僅是筆桿一樣的一小節,牽牽扯扯拖出水面的竟很長,破布一樣的,黑色的一大片。有時我在岸上什么也看不到,他們用鐮刀從水底鉤起的,也是一大塊“破布”。正是這些近乎腐爛的“破布”,讓我理解了他們勞動的意義:這蓮花塘,是城南景觀塘,面積大,夏日荷葉密集,層層疊疊,有無數片這樣的“破布”,如果任其浸沒在水里腐爛掉,環境自身是無法消解的,水質肯定會變黑變臭,那我們看到的,將不再是一道風景,住在岸邊的人家,還會因為這一池臭水深受其害。那水邊、水中的其他植物,冬日枯萎腐敗后,也會和這些“破布”一樣,成為污染水質的幫兇。
因為這樣的發現,我為自己先前沒來由的幽怨生出慚愧來:把殘荷當風景,只是我個人的小情小調,比起河水、家園的清潔與美好,我的那點小情懷,實在算不了什么,甚至有些自私。清除河塘中的殘荷、浮萍等,不是哪個人拍腦袋一時想起的,而是由各級“河長制”規定好的,是必須做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岸邊醒目矗立著城關鎮鎮級河長公示牌、管護責任牌,上面明明白白寫著管護內容:坡面無雜草、無垃圾,水面無漂浮物。眼前在做的,只是眾多管護工作中的一項,季節性很強的一項。
因為這樣的認識上的改變,我認真觀察起眼前這群人的勞動來。
他們的勞動,在我眼里非常艱難,非常了不起。我自小有風濕的毛病,怕風,怕水,不管天氣多熱,都不敢下河塘游泳,更不要說寒冷天氣下水了。在水里作業,他們雖然穿著皮衩,戴著皮護袖,但他們的手免不了要接觸撈起的濕漉漉的殘荷,那淋下的水,還不斷地滴在他們身上、腳前。況且,空曠的水面,風大,濕氣重,氣溫更低。這樣的勞動,我是碰也不能碰的。他們卻駕輕就熟,清除完了一處,以鐮刀當槳,劃向另一處。有一位男子,在船頭系了一根細細的尼龍繩,另一端系在岸上,清理完了一處,拉一拉繩,小船立刻移向前方,非常便捷。
他們撈浮萍的技術也超出了我的預料,在我的想象中,撈浮萍也是要坐在小船上進行的,也要用網兜一下一下地撮在船艙里。不期是我想當然,浮萍都是在岸上撈的。主要的工具不僅僅是網兜,還有一張橫跨岸兩邊的大網,網上均勻、密集地拴著泡沫質地的漂浮物,從上風下水,往下風拖,把那些浮萍聚攏到一起,再探身用網兜一下一下地撈上岸。難怪他們工作過的水面那么干凈,水那樣的清。凡事都有技巧,勞動出智慧。換作我這個習慣坐而論道的人,面對這樣大的工作量,一定束手無策。
我剛好從一位正在往電動三輪車上裝勞動成果的工作人員身邊經過,這是一位身材瘦小,看上去有六十多歲的勞動者,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我主動上前搭訕:
“老師傅,這些東西還要運走啊,運到哪去?”
“不運走怎么行,要是爛在水塘里,等于沒清。”他手上不停,嘴上回答我的話:“運到垃圾中轉站,集中處理。”
“工作量不小,一個區域兩天可能都忙不完。”我沒話找話說。
“兩天哪夠!那一塊。”老師傅停下手中揮動的鐵叉,指著已經碧波蕩漾的那一大片水域:“我們幾個人忙了一個星期。”
“要抓緊時間忙了,再不忙,天更冷。
今天這風,不架事(幫不上忙),割人臉了。”
我縮了縮脖子說。這幾天,最低氣溫都接近0℃,今天又有不小的風,才是初冬,風卻已像刀子。
“冷了也要忙。我們還要趕在有風的日子忙,有風反而好弄……”
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一個有點高大上的稱謂:城市美容師。我眼前的這群人,這群在寒風中、在徹骨的河塘中忙碌的人,如同夏日揮汗如雨、起早貪黑的環衛工人,他們也是我們這座城市的美容師,正是因為有他們辛勤的付出,我們生活的家園才更加整潔、美好。“讓人民群眾在綠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這是與我們每一個普通人息息相關的生動現實。
蓮花塘,倒映著正午的陽光,倒映著兩岸高大的建筑物,波光閃爍,熠熠生輝。我的眼前不禁浮現出年年青荷弄影、蓮花飄香的宜居宜業的和美景象。“風來香氣遠,日落蓋陰移”,明年,這里將是一派更加迷人的城市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