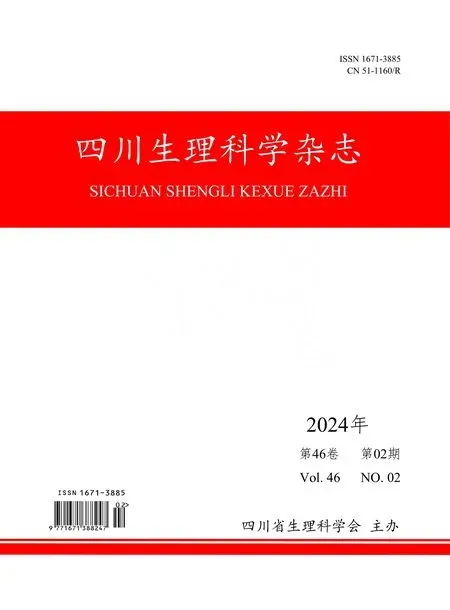慢阻肺合并呼吸衰竭患者血清ChE、PA、HMGB1 水平變化及臨床意義
郭玉
(商丘市第一人民醫院呼吸與危重癥醫學科,河南 商丘 476000)
我國慢性阻塞性肺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COPD)發病率約為8.2%~11.5%,主要特征為不完全持續進展性、可逆性氣流受限,病理表現為肺實質、氣道壁慢性結構破壞,隨著病情進展可影響換氣功能、通氣功能,引發呼吸衰竭現象,危及患者生命安全[1]。COPD 患者反復出現肺部感染、低氧血癥,可引起肺小動脈痙攣,增加血流阻力,誘發肺部動脈血管重塑,進而引起呼吸衰竭,炎性細胞介導的炎性反應、凝血功能異常,對評估呼吸衰竭患者病情進展及預測預后具有一定價值[2]。血清細胞因子可參與COPD 合并呼吸衰竭發生過程[3]。因而可通過檢測血清細胞因子評估患者病情及預測患者預后,以指導臨床制定針對性治療方案。
呼吸衰竭患者中氧化應激反應、炎性反應持續升高,增加乙酰膽堿釋放量,抑制膽堿酯酶(cholinesterase,ChE)活性[4]。前白蛋白(Prealbumin,PA)具有維持機體免疫功能蛋白活性作用,可清除外周循環有毒代謝物質,其水平降低可引起機體基礎代謝失衡[5]。高遷移率族蛋白B1(high mobility group protein B1,HMGB1)水平升高可參與肺部疾病發生發展過程[6]。目前ChE、PA、HMGB1 與COPD 合并呼吸衰竭相關研究鮮見報道。
鑒于COPD 合并呼吸衰竭病情嚴重、預后不佳,尋找可有效判斷患者預后的實驗室指標,對臨床治療方案制定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從血清ChE、PA、HMGB1 水平變化的角度探討其對COPD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預后的預測價值。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1 年1 月至2022 年12 月本院收治的86例COPD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為研究組,依據病情程度[7]分為輕度17 例、中度24 例、重度45 例,選取同期本院收治的82 例單純COPD 患者為對照組,同時選取同期于本院體檢的健康志愿者56 例為健康組。
研究組:男54 例、女32 例,平均年齡65.13±2.63歲,平均體質量指數23.16±1.74 kg·m-2,平均COPD病程12.41±1.83 d,飲酒史35 例,吸煙史28 例,合并癥:糖尿病26 例、高血壓18 例。對照組:男56例、女26 例,平均年齡66.01±3.71 歲,平均體質量指數22.96±2.18 kg·m-2,平均COPD 病程13.01±2.63 d,飲酒史32 例,吸煙史26 例。合并癥:糖尿病22例、高血壓14 例。健康組:男38 例、女18 例,平均年齡65.96±2.85 歲,平均體質量指數23.01±1.88 kg·m-2,飲酒史20 例,吸煙史16 例。各組一般資料均衡可比(P>0.05)。本研究經本院倫理委員會批準。
納入標準:符合COPD 診斷標準[8];符合呼吸衰竭診斷標準[9]:靜息狀態下動脈血氧分壓<60 mmHg或動脈血二氧化碳分壓>50 mmHg;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合并惡性腫瘤;既往免疫抑制劑治療或器官移植治療史者;合并其他肺部疾病者;入組前1 個月內接受過激素類藥物治療者;合并代謝性、自身免疫性疾病者;認知功能障礙、言語溝通障礙者;既往呼吸系統手術史者。
1.2 方法
1.2.1 治療方法
參照《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診治指南(2013 年修訂版)》[10]進行治療,包括維持水電解質平衡、解痙平喘、化痰止咳、抗感染、吸氧等。依據28 d 生存情況分為病死者、存活者。
1.2.2 評估患者臨床癥狀、生理狀態
治療前采用COPD 評估測試(COPD Assessment Test,CAT)評估患者臨床癥狀,共8 項,總分為40分,分值越高表明癥狀越嚴重[11]。急性生理學與慢性健康狀況評分(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Ⅱ,APACHEⅡ)評分包括3 部分,總分為71 分,分值越高表明生理狀態越差[12]。
1.2.3 檢測血清ChE、PA、HMGB1 水平
研究組于治療前、治療7 d 后、治療14 d 后,對照組于入組時,健康組于體檢當日,分別抽取空腹肘靜脈血5 mL,以3500 r·min-1離心5 min,獲取上清液后置于-80℃冰箱待測。采用比色法與Gi8200 全自動生化分析儀(美國雅培公司)檢測血清ChE 水平,上海烜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檢測試劑盒。采用免疫比濁法檢測血清PA 水平,杭州健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檢測試劑盒。采用 ELISA 法檢測血清HMGB1 水平,上海臻科生物公司提供檢測試劑盒。
1.3 觀察指標
(1)對比分析各組血清ChE、PA、HMGB1 水平。(2)分析研究組存活者、病死者治療前、治療7 d、治療14 d 后血清各指標水平。(3)分析研究組治療7 d、治療14 d 后血清各指標水平對預后的預測價值。
1.4 統計學分析
2 結果
2.1 各組血清ChE、PA、HMGB1 水平及APACHEⅡ、CAT 評分比較
研究組血清ChE、PA 水平低于對照組、健康組,且對照組低于健康組;研究組血清HMGB1 水平高于對照組、健康組,且對照組高于健康組;研究組APACHEⅡ、CAT 評分高于對照組(P<0.05)。表1。
表1 各組血清ChE、PA、HMGB1 水平及APACHEⅡ、CAT 評分比較(±SD)

表1 各組血清ChE、PA、HMGB1 水平及APACHEⅡ、CAT 評分比較(±SD)
注:與健康組比較,*P<0.05;與對照組比較,#P<0.05。
2.2 研究組不同預后患者血清各指標水平
病死者治療7 d、治療14 d 后血清ChE、PA 水平低于存活者,HMGB1 水平高于存活者;存活者治療14 d 后血清ChE、PA 水平高于治療7 d 后,HMGB1水平低于治療7 d 后(P<0.05),見表2。
表2 研究組不同預后患者血清各指標水平(±SD)

表2 研究組不同預后患者血清各指標水平(±SD)
注:與治療前比較,*P<0.05;與治療7 d 后比較,#P<0.05。
2.3 血清各指標對預后的預測價值
以病死者24 例為陽性樣本,以存活者62 例為陰性樣本。ROC 分析結果顯示,治療7 d、14 d 后血清ChE、PA、HMGB1 預測預后的AUC 大于單項指標預測,且治療14 d 后血清ChE、PA、HMGB1 聯合預測預后的AUC 大于治療7 d 后血清ChE、PA、HMGB1聯合預測(P<0.05),見圖1、表3。

圖1 治療7 d 后、14 d 后血清各指標對預后的預測價值

表3 血清各指標對預后的預測價值
3 討論
細菌感染誘發菌血癥時血清ChE 水平降低,其水平降低預示機體炎性反應加重,肺組織、細胞受損程度越嚴重,ChE 水平越低[13]。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血清ChE 水平低于對照組、健康組,且對照組低于健康組,提示ChE 水平降低與COPD 合并呼吸衰竭發生相關。COPD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較COPD 患者血清ChE 水平更低,可能是因為細菌毒素、病原菌感染等所致呼吸衰竭發作,機體短時間內發生嚴重全身應激反應,致使膽堿能通路活化,促進機體產生乙酰膽堿,抑制ChE 活性。PA 屬于快速轉運蛋白,可反映體內蛋白質代謝變化,其隨肺功能嚴重程度加重而下降,若機體出現炎性反應時,PA 水平隨著炎性反應加重而降低[14]。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血清PA水平低于對照組、健康組,提示PA 可參與COPD 合并呼吸衰竭發生發展過程。缺氧狀態下患者營養攝入減少,肝合成能力降低,促使PA 水平降低,并可影響機體免疫能力、呼吸系統功能,減弱呼吸肌強度,降低呼吸肌耐力,促使COPD 病情加重,進而導致COPD 合并呼吸衰竭發生。
單核細胞接受刺激后可釋放HMGB1,其與晚期糖基化終產物受體(RAGE)、Toll 樣受體(TRLs)結合,促進肺泡內炎性介質聚集,引起氣道平滑肌增生及纖維化,致使呼吸功能減退,引起呼吸衰竭發生[15]。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血清HMGB1 水平高于對照組、健康組,提示HMGB1 水平升高可能促進COPD合并呼吸衰竭發生。分析其原因可能為組織受損時單核巨噬細胞、受損細胞可分泌HMGB1,其與早期致炎因子形成正反饋環路,維持、放大炎性反應,并可作為趨化因子促進巨噬細胞遷移,直接損傷組織器官。ChE、PA、HMGB1 在炎性反應發生中的作用機制不同,本研究嘗試性將其聯合預測,結果顯示治療7 d、14 d 后血清ChE、PA、HMGB1 預測預后的AUC大于單項指標預測,提示聯合檢測ChE、PA、HMGB1對COPD 合并呼吸衰竭患者預后具有一定預測價值。
綜上所述,血清ChE、PA、HMGB1 水平聯合檢測對患者預后具有較高預測價值,但關于其具體作用機制尚需進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