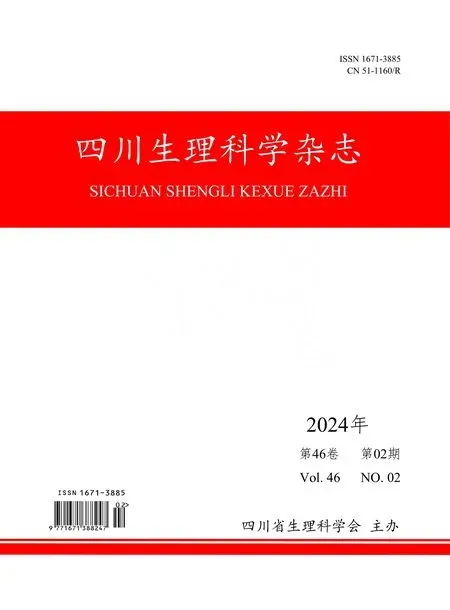神經源性膀胱合并膿毒癥不同嚴重程度患者血清炎癥介質和TGF-β1/Smads 蛋白的表達及其臨床意義
任俊英
(平頂山市第二人民醫院泌尿外科,河南 平頂山 467000)
神經源性膀胱主要是指由于神經系統病變造成膀胱以及尿道功能的失常,同時患者伴有較為嚴重的尿路癥狀。臨床癥狀主要表現為尿潴留、腎盂腎炎、尿積水以及尿路感染[1]。長時間的尿路感染容易引發菌血癥、膿毒癥,其中不同嚴重程度的膿毒癥患者病死率并不相同,且重度膿毒癥患者預后更差,因此盡早的診斷膿毒癥對治療對于患者的預后有很大的幫助[1]。目前,臨床上診斷膿毒癥主要通過血、尿培養確診,然而這些手段的耗時長、準確率并不高,且會受到外界的污染,影響檢測準確性[2]。因此,尋找合適的生物標志物對于早期的膿毒癥診斷意義重大。在膿毒癥的進展中,轉化生長因子-β1(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1,TGF-β1)在纖維組織的修復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3]。白細胞抑制因子4(SMAD4)以及白細胞抑制因子7(SMAD7)均是局部病灶部位炎性反應的重要依據[3]。
基于此,本研究旨在通過神經源性膀胱合并膿毒癥不同嚴重程度患者血清炎癥介質和TGF-β1/Smads蛋白的表達及其臨床意義分析,從而為臨床診斷以及治療效果評估提供科學依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于2016 年1 月~2019 年6 月治療的神經源性膀胱合并膿毒癥患者120 例作為觀察組,其中男性69 例,女性51 例,平均年齡(55.28±4.71)歲。根據患者的膿毒癥不同嚴重程度,將患者進一步分為單純感染組55 例,膿毒癥組39 例,重度膿毒性組26例。其中單純感染組不伴有 SIRS;膿毒癥患者為伴有SIRS 和SOFA 評分小于5 分;重度膿毒性患者為伴有 SIRS 和 SOFA 評分大于等于 5 分。另選取同期神經源性膀胱無感染患者作為對照組,兩組的一般資料無顯著差異(P>0.05),見表1。所有患者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并經倫理委員會通過。

表1 兩組的基線資料比較
納入標準:均符合神經源性膀胱診斷標準[4];患者符合膿毒癥診斷標準[5]。排除標準:尿路梗阻患者;尿路結構異常患者;近一年尿管插入患者;服用免疫抑制劑或糖皮質激素患者。
1.2 方法
1.2.1 TGF-β1、SMAD4、SMAD7 水平檢測
采集患者的膀胱組織,石蠟包埋后進行4μm 連續切片,采用PH6.0 的檸檬酸修復液對石蠟切片進行脫蠟以及脫水,采用高壓加熱法對抗原進行修復。分別采用1:100 的V TGF-β1、SMAD4、SMAD7 抗體進行滴加,4℃下孵育過夜。采用多聚物酶標二抗進行滴加后,37℃下繼續不管孵育45 分鐘。采用DAB進行顯色,蘇木精進行復染。細胞漿內出現棕黃色或棕褐色顆粒物即為TGF-β1、SMAD4、SMAD7 陽性。采用染色強度以及陽性細胞的二級計數法TGF-β1、SMAD4、SMAD7 進行評分[9]。
1.2.2 TNF-α、IL-1β、PGE2 水平檢測
所有患者均進行肘靜脈采血2 mL,3500 rpm 離心15 min,離心直徑30 cm。取上清液,采用酶聯免疫法對患者的腫瘤壞死因子 -α(TNF-α)、白介素 -1β(IL-1β)以及前列腺素 E2(PGE2)水平進行檢測。所有實驗試劑均來自上海羅氏,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
1.3 觀察指標
(1)兩組的TGF-β1、SMAD4、SMAD7 水平比較;(2)不同嚴重程度患者的TGF-β1、SMAD4、SMAD7 水平比較。(3)兩組的TNF-α、IL-1β、PGE2水平比較;(4)不同嚴重程度患者的TNF-α、IL-1β、PGE2 水平比較。
1.4 統計學方法
數據均采用spss22.0 軟件進行分析。其中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比較,三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ANOVA),進一步組間兩兩比較采用SNK-q 檢驗。P<0.05,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的TGF-β1、SMAD4、SMAD7 水平比較
觀察組的TGF-β1(t=6.379,P<0.001)、SMAD7(t=13.585,P<0.001)顯著高于對照組,SMAD4(t=7.507,P<0.001)顯著低于對照組,詳見表2。

表2 兩組的TGF-β1、SMAD4、SMAD7 水平比較
2.2 不同嚴重程度患者的TGF-β1、SMAD4、SMAD7水平比較
不同嚴重程度患者的TGF-β1(F=9.263,P<0.001)、SMAD4(F=15.016,P<0.001)、SMAD7(F=9.657,P<0.001)水平之間的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經兩兩比較,TGF-β1、SMAD7 從低到高依次為單純感染組、膿毒癥組、重度膿毒癥組,SMAD4 從高到低依次為單純感染組、膿毒癥組、重度膿毒癥組,詳見表3。

表3 不同嚴重程度患者的TGF-β1、SMAD4、SMAD7 水平比較
2.3 兩組的TNF-α、IL-1β、PGE2 水平比較
觀察組的TNF-α(t=59.196,P<0.001)、IL-1β(t=39.525,P<0.001)、PGE2(t=69.264,P<0.001)水平顯著高于對照組,詳見表4。

表4 兩組患者的TNF-α、IL-1β、PGE2 水平比較
2.4 不同嚴重程度患者的TNF-α、IL-1β、PGE2 水平比較
不同嚴重程度患者的TNF-α(F=47.805,P<0.001)、IL-1β(F=135.449,P <0.001)、PGE2(F=34.287,P<0.001)水平之間的差異存在統計學意義,經兩兩比較,TNF-α、IL-1β、PGE2 從低到高依次為單純感染組、膿毒癥組、重度膿毒癥組,詳見表5。

表5 不同嚴重程度患者的TNF-α、IL-1β、PGE2 水平比較
3 討論
尿源性膿毒癥作為臨床較為常見的泌尿系統臨床感染癥狀,患者可全身性的炎性反應以及氧化應激反應;該病具有疾病急、進展較快以及病情較為危重等特點[1]。目前,臨床上對尿源性膿毒血癥的疾病診斷中,其診斷標準較為復雜,明確神經源性膀胱合并膿毒癥不同嚴重程度,給予針對性的治療,對于控制患者疾病進展具有顯著的意義。本研究中,通過對患者的病灶部位的TGF-β1、SMAD4、SMAD7 水平的分析,發現隨著疾病的進展,患者的TGF-β1、SMAD7隨著疾病的進展顯著升高,SMAD4 顯著降低。分析認為,在膀胱組織中發揮膀胱彈性功能的為纖維細胞,在纖維細胞的自我修復過程中,TGF-β1 發揮關鍵作用[6],TGF-β1 可通過對成纖維細胞的過度增生的誘導作用,進一步促進損傷纖維細胞的修復。機體TGF-β1 的調控主要是依賴Smad7 的轉錄作用[2],在間質的成纖維細胞的疾病進展中發揮核心作用,在對敲除Smad7 的小鼠的研究中,小鼠的肉芽組織顯著增生,對于機體的纖維細胞的形成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所以,在對實驗大鼠的成纖維細胞的恢復過程中,Smad7 缺乏可造成疤痕組織的重塑作用增強。在膀胱組織的恢復中,Smad7 對機體的TGF-β1 調控作用,顯著激活下游的ERK1/2 信號通路[2,3,6],進一步促進細胞的分化以及增殖,而P38 已經被證實對于成纖維細胞的增殖以及I型膠原復合體的抑制作用中發揮重要作用,而P38 的激活主要通過對Smad7 非標準化磷酸化進行激活,進而發揮促進成纖維細胞的作用。
SMAD4 主要作為細胞內炎性反應物質的重要轉導介質,通過對細胞核傳遞信號[6],引發局部的炎性反應水平。已有的研究已經證實[2,3,6],SMAD4 可通過對受體激酶磷酸化的顯著性抑制作用,進一步形成負反饋環路。而在本研究對患者的炎性指標的分析中,隨著患者的疾病進展,患者的炎性指標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以上理論研究。馮永杰等在對膀胱癌術后患者的尿路感染的分析中指出,隨著患者的術后尿路感染風險的顯著升高,患者的病灶部位的SMAD4 顯著下降,SMAD7 顯著升高,與本研究結果一致。
綜上所述,隨著神經源性膀胱合并膿毒癥患者疾病的加重,TGF-β1 以及SMAD7 呈現顯著的上升趨勢,SMAD7 顯著下降,可作為臨床診斷的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