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相場模型的再生冷卻推力室熱機疲勞壽命分析
孫 燊 易 敏
(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 航空航天結(jié)構(gòu)力學(xué)及控制全國重點實驗室,江蘇 南京 210016)
0 引言
可重復(fù)使用運載器具有高效、經(jīng)濟、環(huán)保等特點,是目前航天技術(shù)發(fā)展的重要方向[1]。2015年以來,美國私人航天公司SpaceX回收并重復(fù)使用獵鷹9號運載火箭,國外研究機構(gòu)不斷突破,以求擺脫單次使用運載火箭高昂費用對空間探索的制約。我國一方面密切追蹤國外先進技術(shù)發(fā)展[2-3],另一方面努力推進自身關(guān)鍵技術(shù)攻關(guān)。可重復(fù)使用運載器技術(shù)既能降低空間運輸成本,貫徹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又是彰顯綜合國力、搶占空間優(yōu)勢的必要工具。液體火箭發(fā)動機作為動力裝置,其耐久性和可靠性是保障運載器可重復(fù)使用的關(guān)鍵。推力室喉部結(jié)構(gòu)是液體火箭發(fā)動機的核心部件,在服役過程中會經(jīng)歷復(fù)雜、交變的熱機載荷作用,不均勻的溫度分布、局部的塑性應(yīng)變更會加快結(jié)構(gòu)的疲勞失效。因此,對推力室喉部結(jié)構(gòu)進行傳熱分析和疲勞壽命預(yù)測具有重要意義。
推力室在工作時會經(jīng)歷急速的升溫與降溫,在局部會發(fā)生較大的熱變形,分析結(jié)構(gòu)承受的熱載荷需要計算結(jié)構(gòu)的傳熱情況和溫度分布。推力室內(nèi)壁需要承受高溫燃氣的沖刷作用,冷卻劑在冷卻通道中逆流降溫。多種材料分別具有不同的物性,對傳熱分析的計算結(jié)果提出很高的要求。吳峰等應(yīng)用湍流模型進行了三維數(shù)值模擬,計算了再生冷卻推力室通道的流動與傳熱[4]。韓煒對推力室的再生冷卻情況進行了三維數(shù)值模擬,得到了內(nèi)壁面上溫度分布一般規(guī)律[5]。吳有亮等提出了推力室準(zhǔn)二維傳熱計算的通用方法,相較于三維計算,降低了計算時間,極大地提升了計算效率[6]。根據(jù)傳熱分析得到的溫度分布可以計算結(jié)構(gòu)中的熱本征應(yīng)變,可仿真模擬燃氣溫度和燃氣壓強載荷的共同作用效果,并預(yù)估推力室使用壽命。孫冰等對推力室結(jié)構(gòu)進行了三維瞬態(tài)熱分析,并根據(jù)應(yīng)力應(yīng)變分布預(yù)測了結(jié)構(gòu)危險點的失效情況[7-9]。徐紹桐等建立了推力室壁在燃氣/冷卻液溫度和燃氣壓強載荷下的二維彈塑性計算模型,提高了失效行為模擬的計算速度[10]。張明等通過數(shù)值計算研究了變截面冷卻通道的傳熱情況[11]。目前,推力室疲勞壽命預(yù)測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損傷力學(xué)計算損傷的累積,或者根據(jù)應(yīng)力-應(yīng)變法計算材料的疲勞壽命,較少從斷裂力學(xué)出發(fā)預(yù)測壽命。
傳統(tǒng)方法處理斷裂問題往往將界面作為一個突變的量來處理,突變問題的數(shù)值奇異性增加了問題的求解難度。在材料斷裂的界面,數(shù)值上難以進行微分算法,材料參數(shù)需要考慮因材料破壞而損失的剛度。相場模型通過引入在界面處急劇變化但連續(xù)的相場變量——序參量來描述不同的相[12-14],斷裂序參量在整個計算區(qū)域上是連續(xù)變化的,因此相場模型中不再需要采用特殊的數(shù)學(xué)方法追蹤界面的幾何形態(tài),也避免了追蹤斷裂面所引起的誤差。相場斷裂方法可以反映加載過程中斷裂序參量的演化,直觀地觀察到裂紋的演化。Francfort等[15]通過對Griffith斷裂理論[16]及變分公式的研究,提出了準(zhǔn)靜態(tài)脆性斷裂的相場模型。Miehe等提出了應(yīng)變張量的譜分解方法,用以區(qū)分壓縮和拉伸對應(yīng)的應(yīng)變能,并且推廣到熱-彈-塑性耦合的斷裂問題[17-19]。文獻[20-21]通過修正斷裂相場模型中的斷裂韌性,實現(xiàn)對疲勞斷裂問題的相場模擬。
本文使用相場疲勞斷裂模型對再生冷卻推力室喉部結(jié)構(gòu)進行有限元模擬,通過熱傳導(dǎo)方程考慮溫度載荷引入的熱本征應(yīng)變,得到結(jié)構(gòu)的溫度和應(yīng)力/應(yīng)變分布情況,根據(jù)相場序參量的變化分析結(jié)構(gòu)的疲勞斷裂過程,研究推力室結(jié)構(gòu)在服役過程中的失效行為和熱機疲勞壽命。
1 熱力耦合疲勞相場模型
1.1 熱力耦合模型
銑槽式再生冷卻推力室采用等肋寬的薄壁結(jié)構(gòu),其喉部自內(nèi)向外分別為內(nèi)壁、冷卻通道和外壁,冷卻通道使用肋片進行強化傳熱。推力室中實際發(fā)生的熱量傳遞包括:燃氣對內(nèi)壁的加熱、冷卻劑對冷卻通道的對流換熱。考慮熱載荷對受力的單向耦合,采用穩(wěn)態(tài)熱平衡方程對溫度場進行傳熱分析,熱傳導(dǎo)的控制方程為無熱源的導(dǎo)熱微分方程,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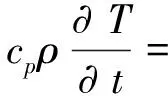
(1)
式中:cp為定壓比熱容;ρ為材料密度;T為結(jié)構(gòu)溫度;t為時間;?為哈密頓算子;λ為材料熱導(dǎo)率。
發(fā)動機推力室在工作過程中同時受到溫度載荷和機械載荷的作用。結(jié)構(gòu)的總應(yīng)變εtotal由熱應(yīng)變εth、彈性應(yīng)變εela、塑性應(yīng)變εpla和蠕變應(yīng)變εcr構(gòu)成,即
εtotal=εth+εela+εpla+εcr
(2)
熱應(yīng)變與溫度的變化成線性關(guān)系,即
εth=αthΔTI
(3)
式中:αth為線膨脹系數(shù);ΔT為相對參考溫度的溫度變化量;I為二階單位張量。
1.2 塑性模型
在分離彈性應(yīng)變和塑性應(yīng)變時,使用von Mises屈服準(zhǔn)則來判斷材料是否達到屈服,屈服條件表達式為
(4)
式中:f為屈服函數(shù);s為偏應(yīng)力張量;a為背應(yīng)力張量,即屈服面中心;σy為屈服應(yīng)力。
達到屈服面后塑性應(yīng)變產(chǎn)生,塑性應(yīng)變沿著屈服面梯度方向增加,即
(5)
式中:dλ為塑性乘子,即等效塑性應(yīng)變增量;σ為應(yīng)力張量。
1.3 蠕變應(yīng)變模型
計算蠕變應(yīng)變時,考慮陳化理論,即Norton定律。在蠕變過程中,時效、擴散和恢復(fù)等因素影響蠕變行為,其中時間是最大的影響因素。Norton模型的表達式為
(6)

1.4 斷裂相場模型
定義相場序參量c表示材料的斷裂情況,如果材料完好未損壞,則c為 1;如果存在裂紋,則c為 0。因此,變量c可以看作是損傷力學(xué)模型中的損傷參數(shù)。斷裂模型中總自由能密度由彈性應(yīng)變能、塑性應(yīng)變能和斷裂界面能組成,表達式為
ψ=ψela+(1-c)2ψpla+ψc
(7)
假定彈性應(yīng)變中只有拉伸分量驅(qū)動裂紋擴展,將彈性應(yīng)變譜分解為
εela=PΛPT
(8)
式中:Λ=diag(λ1,λ2,λ3)是與彈性應(yīng)變張量相似的對角陣,λ1、λ2、λ3為彈性應(yīng)變的特征值;P為特征矩陣。
根據(jù)譜分解,彈性應(yīng)變的正負分量為
εela+=PΛ+PT
εela-=PΛ-PT
(9)
彈性應(yīng)變能密度分解為驅(qū)動裂紋擴展的拉伸部分ψela+和不可驅(qū)動裂紋擴展的壓縮部分ψela-,表達式為
(10)
根據(jù)Borden的塑性斷裂相場模型[22],塑性應(yīng)變能密度表達式為
(11)
裂紋的相場演化方程表示為

(12)
式中:η為動力學(xué)系數(shù);l0為界面寬度尺寸;G為臨界斷裂能密度;ψh為驅(qū)動裂紋擴展的歷史變量,即
(13)
1.5 考慮疲勞的相場模型
推力室結(jié)構(gòu)在工作過程中會經(jīng)歷周期性的熱應(yīng)力或熱應(yīng)變,單次循環(huán)載荷作用下,應(yīng)力水平可能遠低于使材料斷裂的臨界應(yīng)力,但是仍會經(jīng)歷往復(fù)循環(huán)的塑性變形。因此,需要考慮循環(huán)載荷下的相場疲勞斷裂模型。通過引入疲勞退化函數(shù),對材料的斷裂韌性進行修正,使其在循環(huán)載荷下不斷衰減,模擬結(jié)構(gòu)在疲勞載荷下的斷裂失效。采用的退化函數(shù)為
(14)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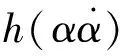
(16)
疲勞斷裂的相場演化方程表示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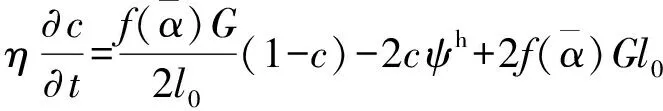
(17)
2 計算結(jié)果與討論
推力室喉部為環(huán)形對稱結(jié)構(gòu),選取1/2冷卻再生通道截面作為計算模型,結(jié)構(gòu)的幾何特征與邊界條件如圖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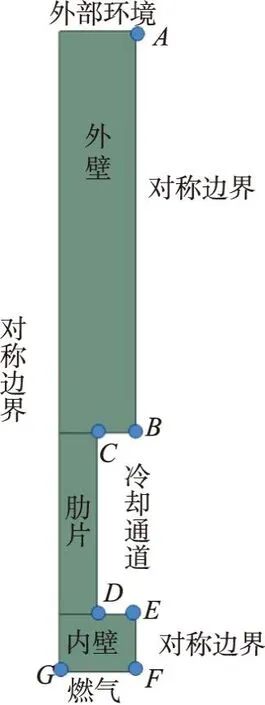
圖1 模擬結(jié)構(gòu)幾何示意圖Fig.1 Geometry of the structure
本文在 MOOSE(Multiphysics Object-Oriented Simulation Environment)框架下進行模擬,通過編寫有限元程序,利用PETSc求解器和Libmesh庫進行并行計算。為了提高計算效率,使用二維平面應(yīng)變結(jié)構(gòu)進行模擬。本文采用四邊形網(wǎng)格進行網(wǎng)格劃分。模型網(wǎng)格基礎(chǔ)尺寸為0.1 mm,在肋片和內(nèi)壁進行加密,尺寸最小為0.01 mm,網(wǎng)格數(shù)量為16 305。對于網(wǎng)格無關(guān)性驗證,進行了6 495、16 305和29 888不同單元數(shù)量的測試,3種網(wǎng)格的溫度分布基本一致,第一種網(wǎng)格與后兩種網(wǎng)格所獲得的應(yīng)力/應(yīng)變分布有明顯差別,后兩種網(wǎng)格所獲得的結(jié)果基本一致,故本文結(jié)果皆是基于第二種網(wǎng)格(16 305單元)得到的。計算采用單向耦合求解,在每一個時間步,先進行傳熱計算,得到溫度分布后,將溫度轉(zhuǎn)化為熱應(yīng)變,代入力學(xué)方程求解應(yīng)力/應(yīng)變和斷裂相場值,然后進行下一時間步的計算。模型的兩邊設(shè)置為對稱邊界。發(fā)動機工作過程分為啟動-熱試車-后冷-關(guān)機4個階段,各階段時長分別為5、300、20、600 s,環(huán)境溫度為295.15 K。結(jié)構(gòu)的溫度邊界條件和壓力邊界條件參見文獻[23]。
結(jié)構(gòu)的內(nèi)壁和肋片材料為NARloy-Z銅合金,外壁材料為1Cr21Ni5Ti。NARloy-Z銅合金性能參數(shù)參照Esposito 在高低溫環(huán)境下的單軸拉伸試驗數(shù)據(jù)[24],蠕變模型使用Ellis得到的不同溫度、不同應(yīng)力水平下的蠕變試驗數(shù)據(jù)[25]。相場疲勞斷裂模型的參數(shù)見表1。為了獲得相場模型參數(shù),根據(jù)材料的屈服強度、抗拉強度和伸長率等參數(shù)先進行不同參數(shù)下的單軸拉伸計算測試,選取能實現(xiàn)吻合實驗結(jié)果的模型參數(shù),再進行推力室受載計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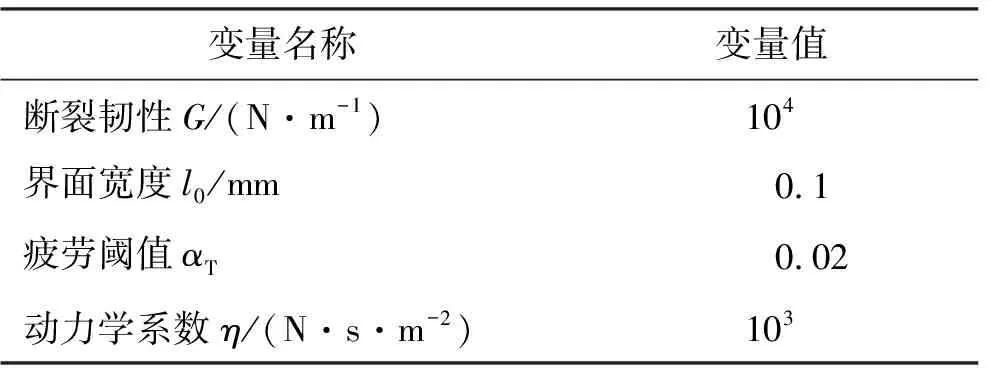
表1 NARloy-Z合金參數(shù)Tab.1 Parameters of NARloy-Z alloy
2.1 溫度分布結(jié)果
不同階段下結(jié)構(gòu)的溫度分布如圖2所示。在熱試車階段,結(jié)構(gòu)的升溫比較明顯,最高溫度出現(xiàn)在內(nèi)壁下表面,G點溫度最高可達881.17 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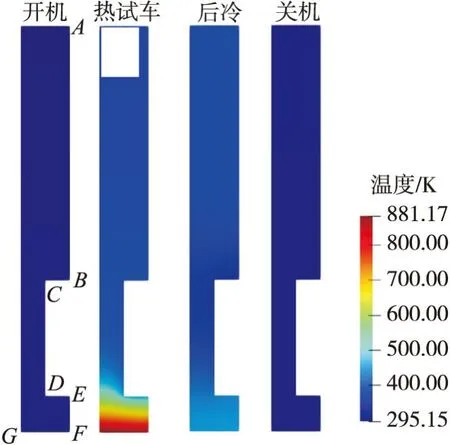
圖2 各階段溫度分布Fig.2 Temperature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選取結(jié)構(gòu)上7個參考點的溫度變化曲線,如圖3所示。可以看出:自下而上,內(nèi)壁溫度最高,肋片次之,外壁溫度最低。由于內(nèi)壁與肋片的材料熱導(dǎo)率高于外壁,外壁上參考點的升溫速率也明顯慢于其他兩部分。外壁上B、C兩點的溫度基本一致。

圖3 各參考點溫度變化Fig.3 Temperature evolution of reference points
2.2 單次工作結(jié)構(gòu)應(yīng)力/應(yīng)變分析
推力室單次工作各階段結(jié)構(gòu)的應(yīng)力/應(yīng)變分布如圖4和圖5所示。在開機階段,結(jié)構(gòu)升溫幅度較小,整體的壓應(yīng)力和壓應(yīng)變的數(shù)值較低。由于肋片膨脹受到內(nèi)、外壁的限制,整體處于壓應(yīng)力水平。在熱試車階段,結(jié)構(gòu)整體升溫,受熱膨脹,由于受到對稱邊界的限制,結(jié)構(gòu)整體表現(xiàn)為受壓。肋片膨脹受到外壁限制,C處會產(chǎn)生較高的壓力。該階段下,結(jié)構(gòu)內(nèi)壁下表面溫度最高,G點受到左側(cè)邊界的限制,受到的壓應(yīng)變最大,最高達到1.34%。在后冷階段,結(jié)構(gòu)彈性變形恢復(fù),內(nèi)壁由于壓載較大,降溫后有殘余的塑性變形。內(nèi)壁下表面F點和G點分別表現(xiàn)為殘余拉應(yīng)變和殘余壓應(yīng)變。F點受到拉伸載荷,殘余應(yīng)變約為1%。在關(guān)機階段,結(jié)構(gòu)的溫度分布與后冷階段相差不大,結(jié)構(gòu)最終的受載情況和殘余應(yīng)變與后冷階段基本一致。

圖4 各階段應(yīng)力分布Fig.4 Stress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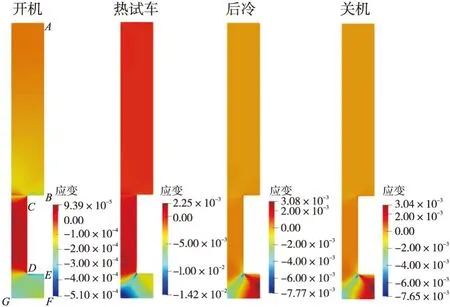
圖5 各階段應(yīng)變分布Fig.5 Strain distribu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根據(jù)應(yīng)力和應(yīng)變分布圖,確定D、E、F、G這4點在工作過程中受到的局部應(yīng)力-應(yīng)變較大,為服役危險點。這4點的應(yīng)力、應(yīng)變曲線如圖6所示。4個點在循環(huán)中都經(jīng)歷壓應(yīng)力變?yōu)槔瓚?yīng)力,D、E、G點始終受到壓應(yīng)變,F點最終由壓應(yīng)變轉(zhuǎn)變?yōu)槔瓚?yīng)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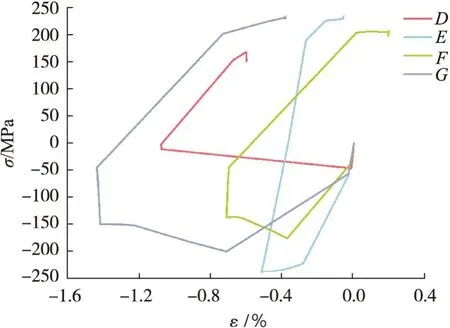
圖6 單次工作中4個特征點的應(yīng)力-應(yīng)變曲線Fig.6 Stress-strain curves of four points during single cycle
2.3 10次循環(huán)結(jié)構(gòu)應(yīng)力/應(yīng)變分析
對10個工作循環(huán)下的推力室喉部結(jié)構(gòu)進行仿真。根據(jù)單次循環(huán)應(yīng)力應(yīng)變分析,結(jié)構(gòu)的危險點位于內(nèi)壁下表面的F和G點,循環(huán)仿真后重點關(guān)注F和G點的應(yīng)力應(yīng)變情況。F點和G點10次循環(huán)的應(yīng)力應(yīng)變曲線分別如圖7和圖8所示。隨著循環(huán)數(shù)的增加,F、G兩點表現(xiàn)為應(yīng)力控制的非對稱循環(huán)加載,并且每次循環(huán)結(jié)束殘余應(yīng)變值不斷增加。其中,F點為拉伸應(yīng)變,G點為壓縮應(yīng)變。F、G兩點殘余應(yīng)變發(fā)展曲線如圖9所示。

圖7 F點10次循環(huán)應(yīng)力-應(yīng)變響應(yīng)Fig.7 Stress-strain response of point F in 10 cyc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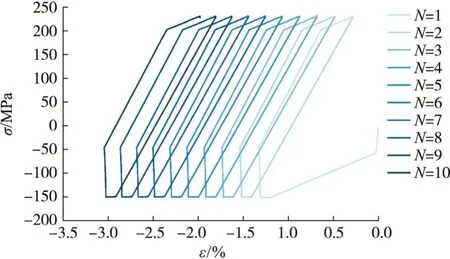
圖8 G點10次循環(huán)應(yīng)力-應(yīng)變響應(yīng)Fig.8 Stress-strain response of point G in 10 cycles

圖9 F、G點10次循環(huán)殘余應(yīng)變的變化Fig.9 Residual strain evolution at F and G in 10 cycles
2.4 結(jié)構(gòu)疲勞失效分析
由于單次循環(huán)結(jié)構(gòu)承受的最大應(yīng)力小于材料斷裂破壞的臨界應(yīng)力,結(jié)構(gòu)中的斷裂序參量增長較小。循環(huán)加載并計算結(jié)構(gòu)的斷裂序參量,直至結(jié)構(gòu)中出現(xiàn)序參量值達到0.95則停止計算。最終發(fā)現(xiàn),91個循環(huán)后結(jié)構(gòu)失效,計算停止,F點斷裂序參量最先達到臨界值c=0.95,表明結(jié)構(gòu)的疲勞壽命為91次循環(huán),失效點位于內(nèi)壁下表面F點。
單次循環(huán)后的序參量分布如圖10所示。圖10表明,結(jié)構(gòu)中內(nèi)壁下表面中心點F序參量最大,在單次工作結(jié)束后,F點的損傷最大,但此時序參量的值還處于很低的水平,對結(jié)構(gòu)的承載能力影響不大,不會使應(yīng)力衰減,仍可以進行多次循環(huán)工作。結(jié)構(gòu)在內(nèi)壁下表面受到的溫度載荷最高,并且F點由于對稱邊界受到約束,在溫度恢復(fù)常溫后,受到的拉應(yīng)力最大,所以序參量演化最快。根據(jù)應(yīng)力分布云圖,在結(jié)構(gòu)變截面處,即C、D點會出現(xiàn)應(yīng)力集中。C點受到的溫度載荷較低,所以溫度載荷恢復(fù)后受到的載荷水平較低,沒有出現(xiàn)損傷。D點受到的溫度載荷較高,相場值為6×10-7,但與F點相比仍較低,因此結(jié)構(gòu)并未在變截面處出現(xiàn)裂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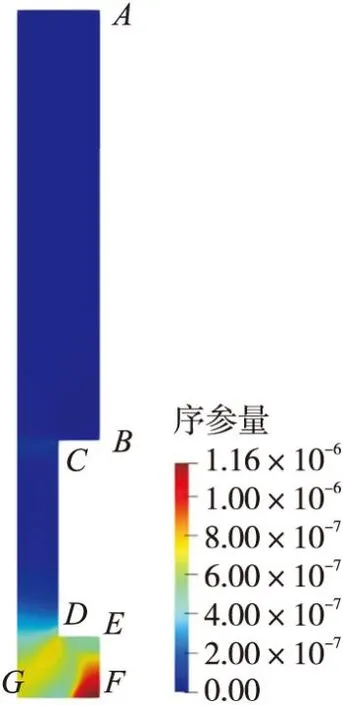
圖10 單次工作后相場序參量分布Fig.10 Distribution of phase-field order parameter after 1 cycle
10次循環(huán)后的序參量分布如圖11所示,結(jié)果與單次循環(huán)相似,仍在F點序參量值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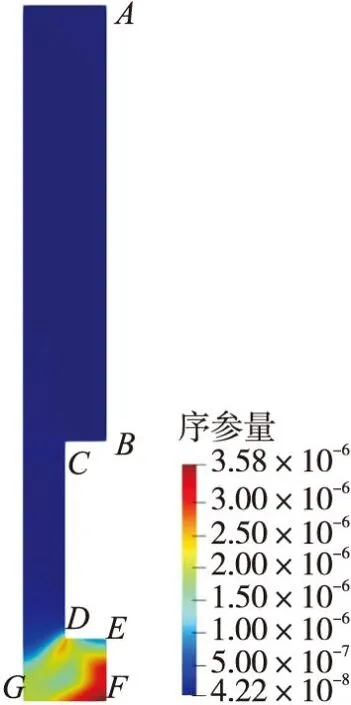
圖11 10次工作后相場序參量分布Fig.11 Distribution of phase-field order parameter after 10 cycles
結(jié)構(gòu)中的斷裂序參量演化如圖12所示。隨著循環(huán)數(shù)增加,下表面的斷裂序參量值不斷上升,并且EF邊界明顯快于內(nèi)壁其他區(qū)域,從F點到E點從大到小基本呈線性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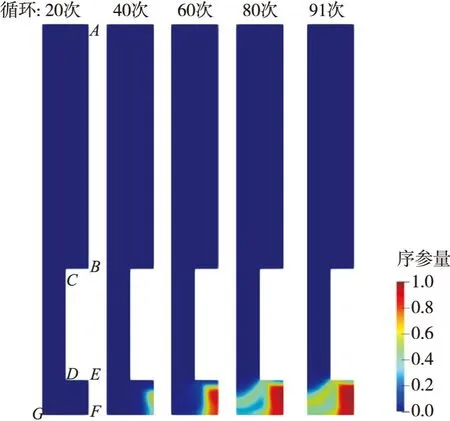
圖12 相場序參量演化Fig.12 Evolution of phase-field order parameter
結(jié)構(gòu)失效破壞時的徑向位移如圖13所示。疲勞破壞時,EF邊界明顯向下凹陷,內(nèi)壁不斷變薄,最終在F點處斷裂失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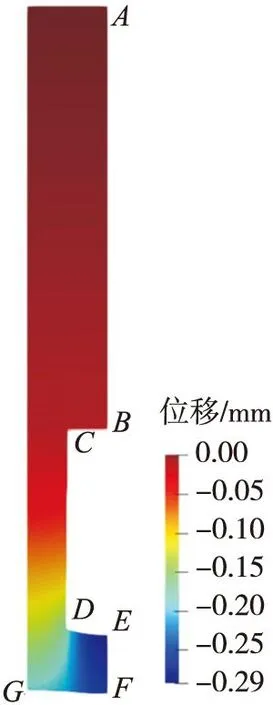
圖13 結(jié)構(gòu)破壞時的徑向位移Fig.13 Radial displacement at failure
3 結(jié)論
本文采用熱-彈-塑性耦合的疲勞斷裂相場模型,分析了火箭發(fā)動機再生冷卻推力室結(jié)構(gòu)在循環(huán)運行過程中的溫度、應(yīng)力和應(yīng)變分布及變化,根據(jù)斷裂序參量的演化,分析了熱機疲勞破壞行為并計算了結(jié)構(gòu)的疲勞壽命,主要結(jié)論如下。
1)推力室結(jié)構(gòu)在工作過程中熱量自下而上傳導(dǎo),溫度逐漸降低。結(jié)構(gòu)升溫降溫產(chǎn)生的塑性變形是導(dǎo)致結(jié)構(gòu)疲勞失效的主要因素。
2)結(jié)構(gòu)內(nèi)壁部分變形較大,隨著循環(huán)次數(shù)增加,F點和G點分別不斷累積殘余正應(yīng)變和殘余壓應(yīng)變。
3)F點受到殘余正應(yīng)變積累,驅(qū)動裂紋擴張的拉伸應(yīng)變能不斷增加,最終導(dǎo)致結(jié)構(gòu)發(fā)生疲勞破壞。內(nèi)壁中心受到殘余正應(yīng)變,使內(nèi)壁向下表面塌陷,壁面變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