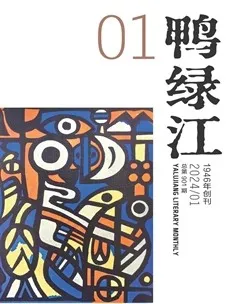勸退
劉齊
1983年秋天,有一伙人,七八個吧,在遼寧東北部山區轉了幾天。這天下午,來到努爾哈赤祖先的陵寢,史稱永陵。借發跡子孫的光,這里也修的紅門樓子、白石臺階,外加雜草密密、古木森森,便生出一種威嚴和蒼茫。聽向導說,有一年,也是秋天,幾個后生舉著旗幟,喊著口號,前來刨墳,說是要肅清封建余毒。墳太大,先刨陵前石獅,剛一舉鎬,就閃了腰,不好,神鬼不樂意了,快撤,一撤,又崴了腳,不是一個人崴,都崴了。
古漆斑駁,陵門緊鎖,門前一塊牌子,寫著“內部維修”字樣。大家門縫里瞧瞧,院墻外轉轉,西天泛黃,昏鴉爭噪,身上起了涼意,就近找一間旅舍歇息。
晚餐時飯廳寂寥,除了服務員,只他們一桌有客。喝了點兒燒酒,聊起刨墳事件。一個小伙兒,瘦高個兒,戴眼鏡,比比畫畫,分析歸納,并提及國外的靈異故事,說得自己都起了雞皮疙瘩,瞅瞅窗外,黑幽幽的,不辨人影樹影。
另有一中年壯漢,淺灰上衣,淺灰帽子,室內也不摘帽,不知是怕冷,還是怕把帽子弄丟,這時插話說,刨墳的事沒那么玄乎,不過是心理作用,心里有鬼,鬼就顯了靈。
眼鏡小伙兒說,我也知道是心理作用,我是想由此及彼,放眼世界,在各位面前顯擺顯擺。
壯漢說,看出來了。說完一笑,兩人碰杯。
壯漢能喝,八九杯下肚,仍然穩穩當當,誰敬酒都不拒,也不怎么就菜。
小伙兒卻有點喝高,大腦控制系統開閘,沒邊沒沿,一通胡侃。
桌上一女子,忽然指著小伙兒喊:你們看,他像誰?
眾人靜了,不知如何回答。
女子說,像不像溥儀?
沒等別人吱聲,小伙兒指著女子,舌頭硬撅撅地說,她,像不像,婉容?
轟的一聲,眾人笑了。
壯漢說,可以呀你,一句話揀了個皇后。又對全體說,你們總念叨清朝,一會兒祖宗墳墓,一會兒末代皇帝,從開張說到滅亡,是不是真有啥顯靈了?
人們笑道,不說了,不說了,說點現代的。
現代的小伙兒也說不出,他醉得撐不住,提前回房間休息,臨走朝壯漢揚手:婉容再見。
壯漢佯怒:你看清楚了,我是你大爺。
小伙兒吐一口粗氣:同志之間,都是,平輩。說完險些跌倒,壯漢扶了他一把。
酒席散了,各自安歇。
第二天,按計劃去看高山上的林場。
山路窄,林子密,當地委派的向導不斷說些奇聞逸事、異樹、異草,試圖讓行路人精神一些。向導微胖,五十歲左右,早年學的植物專業,綱目科屬,娓娓道來。見大家累得不出聲,從兜里摸出一把黃白色的小薄片,分給眾人,說是本地產的人參,切成片,吃了止渴解乏。
分到眼鏡小伙兒,小伙兒酡紅著臉,昨夜的酒態似未全消,擺擺手:老百姓不拿老百姓一針一線。
向導不解:老百姓也有這規定了?
壯漢說,別理他,不要就不給,這小子沒別的毛病,就是沒大沒小,逮誰泡誰。
人們含著參片繼續爬山,品評說,甜滋滋的,苦絲絲的,還真有點能量。
壯漢扯小伙兒一把,讓他挨著自己,悄聲囑咐,一會兒進了林場,多聽他們說,他們是老知青,長年待在山上,都挺單純的,你亂開玩笑,人家不一定理解,還以為是真事。
小伙兒:那我來點兒簡單的。
壯漢板著臉:什么簡單復雜,啥玩笑都別開。
小伙兒見他是在正經說話,心里有點犯嘀咕。
進了林場,跟老知青挨排握手,表示敬意。這些知青的確老,特殊年代之前,大撥新知青還在校園當小孩兒呢,他們就上了山,扎扎實實,克勤克儉,連續干到今天。
先聽老知青介紹創業歷程,聽完各處參觀,參觀完下山,走一條近道,羊腸小道,草棵子嘩嘩響,褲腿子都蹚干凈了。
小伙兒一直沉默,蔫蔫的,誰說話也不搭茬兒。
山窩里停著一輛半舊面包車,這幾天大家坐的都是它,車身發烏,灰頭土臉。
路面坑坑洼洼,減震彈簧不太靈,乘客一顛一顛,都不說話,怕咬了舌頭。
小伙兒個子高,每次顛簸,腦瓜都能碰到車頂,更是咬緊牙關。
山勢漸緩,到了平原,地里的玉米摘了棒子,空有秸稈,一片枯黃。
一塊界碑掠過,壯漢跟小伙兒說了一句話。說時帽檐一推,露出寬大額頭和淺淺皺紋。小伙兒尋思,額頭以上該不是禿頂吧?很想一把掀開,探探究竟,合計合計,沒敢。
壯漢指著窗外,說的是,到小縣了。
小縣?是說這個縣的地盤小,還是,想學古代縣太爺,謙虛一把?這是開玩笑吧?這會兒又讓開玩笑了?
見小伙兒木木的沒作反應,壯漢有點惋惜,一句多好的俏皮話,白瞎了,遂直白地說,他在這個縣里掛職。
掛什么職?為什么掛職?小伙兒一番琢磨。
面包車開進一個城市,大家下車,跟一個農民企業家座談,然后一起吃飯。
企業家敬重壯漢,邀他挨著自己坐。兩位皆是善飲之人、敞亮之人,幾杯下肚,無話不談。
其他人的性子也不悶,三敬酒兩祝詞,把場面弄得火熱,熱到高潮,便要唱歌。有唱愛情曲的,有唱戰斗歌的,還有唱地方戲的。
輪到小伙兒,左推右擋,硬是不唱。
人們不依不饒,誰誰都唱了,偏你特殊。
小伙兒推說記不住詞,哪個歌的詞都記不全。
企業家說,哼哼調子也中。
壯漢說,你就哼哼一個。
小伙兒無奈,那我就哼哼一個。說完站起來,仰臉,誰也不看,只看天花板,靜了五六秒,嘴里猛然冒出很大動靜,卻不是歌曲,是驢叫,啊——呃,啊——呃,一氣吼了好幾下,接著,又弄出一串禿嚕嚕嚕的怪聲,是在替牲口噴響鼻。
眾人忘記喝彩,統統笑,笑得東倒西歪。
企業家笑出了眼淚:小伙兒啊小伙兒,你真是農民的好朋友。
壯漢笑得喘不過氣:對啊對啊,你真是農民的好朋友。
有人想捂肚子,竟把啤酒碰灑了,灑得桌面上褲襠上哪兒哪兒都是。
小伙兒很滿意,認為自己的表演與眾不同,相當出彩。隱隱覺得,那句好朋友的評價不一般,好像話里有話,藏點兒什么,這是在夸我呢,還是夸驢?不管夸誰,能當農民的好朋友,總比當孬人強。
是夜住市里賓館,都累了,誰也不到別人房間串門。
次日,眾人到一個很大的劇場,參加一個會。
入場前,壯漢突然宣布,由小伙兒代表全體,在會上講話。
小伙兒大吃一驚,忙說,咱們這伙人,你最該講,你不講,老王講,老邊講,誰講也輪不到我講。
壯漢正色道:啰唆啥,叫你講你就講。
小伙兒:講啥呀,一點準備沒有。
壯漢:講啥你自己定。平常你挺能白話,這不算能耐,讓大家聽聽,在正式場合,你怎么表現。
小伙兒納悶,這算啥理由,這不是讓土豆生蘿卜,強迫命令瞎指揮嗎?邊想邊進入劇場,跟同伴們一起,被讓到最前排就座。
一同伴跟小伙兒耳語,注意啊,領導對你有想法了。
啥想法,小伙兒傻傻地問,我也沒咋的啊?
同伴擠眼睛,好事,考察你。
小伙兒慌了,沒等緩過神,當地一個主持人登上舞臺,歡迎另一個人講話,那人不是別人,真真確確,念的正是小伙兒名字。看來,有關方面預謀已久,在劫難逃了。
掌聲中,小伙兒笨笨磕磕上了臺,腦中一片空白,挪挪桌上的青花杯,扳扳麥克風的蛇皮管,抬頭看臺下,黑壓壓的人頭,少說有六七百。又見命他上臺的壯漢,右腿壓左腿,穩坐正中間,笑吟吟地直視臺上,目光中有幾分期許、幾分得意,還有幾分狡黠。
小伙兒一激靈,一個歪點子冒出來。哦哦試了兩下話筒,沖著臺下開了口,聲音發顫,顫也往下說:
“感謝呀,感謝撫順市的文學愛好者,周末多寶貴啊,多寶貴也不休息,都聚到這里,向你們學習,向你們致敬。我們這個采風團,團長是金河,他是著名作家,也是我們遼寧省作家協會的領導。”
說一說鎮靜了,喝口水,氣息順暢地說:“金河得過全國短篇小說獎,向他約稿的刊物很多,他的創作任務就很重,但他特意抽出時間,趕到這里,為的是,跟大家見個面,打個招呼。現在,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送金河老師回住處,繼續他的小說創作,相信他一定會寫出更多更優秀的作品。”
掌聲不知底細,海浪般轟隆隆地響著。
壯漢緊貼椅背,已然坐得舒舒服服,萬沒料到會有這么一出,狠狠瞪了小伙兒一眼,極不情愿地站起身,沖著觀眾草草揮手,孤零零地、窩窩囊囊地退場。一個工作人員打開側門,想送貴賓一程,遭到謝絕。
著名作家走了,壓力也走了,小伙兒多少有些歉意,更多的是輕松、自由,大腦開始活躍,想出一個辦法,就跟全場說,咱們都是文學同行,用不著一二三四、長篇大論,誰有啥問題,寫在紙條上,咱們共同探討,行不行啊?
沒有說不行的,紙條紛紛遞上來。
小伙兒壓下一時說不清的提問,挑出難度小的,一個一個解答。實在沒詞了,扯一扯沿途見聞、皇陵觀感,好歹將場面應付下來。
回賓館的車上,采風團成員嘻嘻哈哈,議論小伙兒,不錯啊,講得挺好,有新意,尤其開頭那幾句,充滿創造精神,竟敢勸退團長。人曹操是挾天子以令諸侯,你是挾廣大群眾以逼領導,看回去怎么收拾你,全盤否定還不至于,畢竟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暫時不會一棍子打死。
倒是壯漢沒太介意,見面只罵一句,你個渾小子,害我在街頭流浪,就沒事了,跟渾小子該說說,該笑笑。
渾小子是新人,告別大學校門,分配到作協剛剛一年。
幾個月后,他獲得提拔,到作協一個部門擔任職務。
過了一段,壯漢得了一場病,不像以前那樣喝酒了。
又過一段,渾小子離開作協,到很遠的地方生活,行前匆忙,未跟壯漢道別。
又過了很長一段,渾小子變成老漢,老漢想念壯漢,想念當年的采風和那時的氣氛,就寫了這篇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