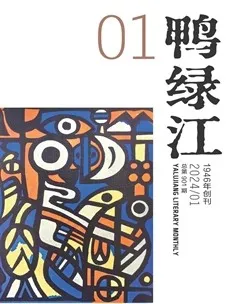我是江南第一燕
周良林
濁酒不銷憂國淚,救時應仗出群才。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
“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這是東晉詩人陶淵明《詠荊軻》里的句子,荊軻刺秦的壯舉,千古傳誦。建黨百年,又有多少像荊軻一樣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繼,舍生取義?!出生于季子故里的“常州三杰”——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尤其是瞿秋白烈士,慷慨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用滿腔熱血譜寫了一曲可歌可泣的壯美史詩。
1
“我是江南第一燕”。
瞿秋白的這句名詩,可謂家喻戶曉。全文是這樣的:“萬郊怒綠斗寒潮,檢點新泥筑舊巢。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云梢。”
“常州三杰”中,瞿秋白出生最晚,比張太雷小一歲,比惲代英小四歲,也是三人中最后一個犧牲的,去世時年僅三十六歲。但他的職務在三人中卻是最高的,他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還一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他的成就也是三人中最大的,他不僅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還是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對于瞿秋白,我并不陌生,大學讀書時就知曉和了解他的文學成就,也讀過他的文章,后來到常州工作,也數次去過瞿秋白紀念館,拜訪這位單純而執著的革命前輩。我孩子曾經就讀的小學叫覓渡橋小學,與瞿秋白紀念館僅一墻之隔。對于我,瞿秋白就像一位故人和至交,深深地印刻在我心中某一個神圣的角落。
在一個陽光燦爛、秋意盎然的日子,我又一次走進瞿秋白故居,就像去看望一個熟悉而親切的朋友。此刻的故居,好像游離于熱鬧喧囂之外,那樣安靜,那樣淡然,又有些寂寞。
說是故居,其實不是瞿秋白的家產,它只是瞿家的一座祠堂。瞿家是常州城里出了名的官宦世家,進士、舉人、布政使、知縣等功名鋪滿了瞿氏族譜。可惜傳到瞿秋白父親一輩,家道中落,他的父親雖有丹青之才,卻屢試不中,后來好不容易謀得一官半職,卻又不善專權營私,自然沒有多少積蓄和資產。也許感覺懷才不遇,心里苦悶,他父親居然吸上了鴉片,很快家里坐吃山空,債臺高筑,落得靠親戚接濟的地步。等到瞿秋白十來歲,全家早已窮得房無一間,無處棲身,只好借居在本族祠堂里,跟寄人籬下差不多了。
雖說家道破落,但書香猶在。漫步在瞿秋白簡陋的睡房和他學習書畫的地方,處處猶有書氣墨香,一個小小少年挑燈夜讀、凝神定氣的影子時隱時現。瞿秋白是不幸的,他幼小的心靈經歷了家道敗落、人情冷暖、討債不絕、停學等一系列傷痛,尤其是母親的自殺帶給了他無窮的悲傷。但瞿秋白又是幸運的,他出生在洪亮吉、趙翼等文人寓居的常州,父親畢竟是讀過書的,母親更是文史詩賦精通。所以瞿秋白很早就跟母親背古詩,跟父親學書畫,跟伯父學篆刻。他沉浸在詩書之中,以書為樂,苦中作樂,喜好《禮記》《莊子》,也看“西廂”。書打開了一扇人生的窗,給了他一個全新的世界,后來瞿秋白以優異成績考入常州府中學堂。如果順利的話,他再考上重點大學或者留學,都是順理成章的事了。可瞿秋白讀到后來,連學費都交不起,被迫輟學,外出謀生。
就從門口的這條河,他搭上了一條小船。站在船頭,他那單薄的身影漸行漸遠……如今,河早已不見,只有天井的水井依舊。沒有了菜畦,沒有了玩耍的笑聲,也沒有了與張太雷、羊牧之的談笑風生,沒有了月色下幽咽的簫聲,只有那常年不斷的井水訴說著,等待著,思念著,想念著那個單薄的身影。
2
穿過一道小門,就是瞿秋白紀念館。院落中幾棵桂花樹碧綠深沉,花還未開。若是深秋時節,此處定然芬芳怡人,香氣彌散。其實瞿秋白從小就喜歡梅花,假日與課余,常到附近的紅梅閣玩耍、嬉戲與賞梅。他還曾用鐵梅、梅影山人作為筆名,書寫紅梅閣的梅花:“出其東門外,相將訪紅梅。春意枝頭鬧,雪花滿樹開。”就連生命的最后時刻,瞿秋白留下的絕筆《卜算子》也與梅花有關:“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眼底煙云過盡時,正我逍遙處。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瞿秋白何嘗不是江南一枝梅?
紀念館里,最先入眼的便是著名散文家梁衡先生《覓渡,覓渡,渡何處》一文的碑文。這篇文章我讀過多次,應該算是寫他、評他最客觀、最公正、最真摯、最優美、最深刻的一篇美文,其言鏗鏘,其情厚重,其意深邃。
館門兩側墻壁,各裝飾一方厚重而精美的銅雕,右邊銅雕的主畫面是瞿秋白與列寧,左邊銅雕的主畫面是瞿秋白與魯迅。這兩個人都與瞿秋白息息相關。瞿秋白在蘇俄考察期間,三次見到列寧,聆聽過列寧的演說,親身感受蘇維埃的巨大變化,從此義無反顧選擇了悲壯而輝煌的理想之路。瞿秋白與魯迅則是肝膽相照的好友和同志,兩位文壇巨匠情深意切,以筆為槍,掀起了思想革命的春潮。人生短暫,瞿秋白先生卻與兩位巨人相遇,實乃幸事也。
走進紀念館,瞿秋白的高大銅像迎面而立。他身穿西服、戴著眼鏡、手握書卷,是在演說,還是在思考?琳瑯滿目的圖片和實物,向我們展示著瞿秋白多方面的才華。一個紀念館,就是一部濃縮的歷史。三十六年,短暫而豐富,曲折而華麗。
歷史永遠定格在長汀公園的六月。那天他穿著干凈的黑色中式對襟衫,白色齊膝短褲,黑線長襪,黑布鞋。質本潔來還潔去,他喜歡干凈。秋白傲然而立,兩手背在身后,雙腳呈稍息狀,神態閑適,泰然自若,一雙眼睛平靜地注視著槍口,注視著死神,注視著當時以及后來所有注視著他的人。
一位在場的記者這樣寫道:“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韭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痛飲數杯之后,瞿秋白放聲歌曰:“人之公余,為小快樂;夜間安眠,是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餐畢,瞿秋白手挾香煙,顧盼自如,信步走向刑場。其間,他用俄語、國語吟唱《國際歌》《紅軍歌》,四十分鐘的步程,若歸家之路,自如從容。抵達羅漢嶺下,看見一片草地,郁郁蔥蔥,周圍綠蔭環抱,鳥兒在吱吱鳴叫。瞿秋白對劊子手微微一笑:“此地甚好。”
于是盤腿而坐,面對槍口,微笑飲彈。
3
我在思索,這是一個怎樣的人呢?連面對死亡都這么瀟灑,這么有詩意。
他不愧是個文人,一個多才多藝的文人。生于書香世家,既有遺傳,也有天賦,酷愛文學,喜治印,善繪畫。作為記者,瞿秋白以優異的俄文專業水平被北京《晨報》和《時事新報》聘任,并被派到十月革命后的蘇俄考察。兩年記者生涯,是辛苦的,是勤奮的,更是熱血澎湃的,他寫下了六十多篇通訊和兩部報告文學,用滿腔激情和無限驚喜,全方位地向中國人民報道這個新生國家的情況,《餓鄉紀程》《赤都心史》一下成為經典。作為詩人,他擅長韻律工整的古體詩詞,也會寫朗朗上口的現代新詩,詩人的情懷伴隨著他的革命生涯,哪怕在被囚禁的歲月里,面對鐵窗和鐐銬,他一樣從容不迫,創作了七首詩詞,其中就有這首《浣溪沙》:“廿載浮沉萬事空,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棲遲芳草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犧牲的前一晚,他還集句偶成一首:“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此詩四句全從《全唐詩》信手拈來,自成一體,足見其功底。
作為翻譯家,他先后翻譯了諸多大家名作,如萊蒙托夫的《煩悶》《安琪兒》,丘特契夫的《寂》,高爾基的《阿彌陀佛》《海燕》、阿里鮑夫的《可怕的字》,托爾斯泰的《宗教與道德》和普希金的《茨岡》。最廣為人知的翻譯杰作,便是那唱徹全球的《國際歌》。經過他重新翻譯創作的歌詞,鏗鏘有力,至今不衰。他的專著《俄羅斯文學史》,系統評述了十月革命以前俄羅斯文學及其代表性作家,對普希金、果戈里、萊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人的生平、創作道路和文學成就進行了較為準確的介紹和中肯的評價。他口才一流,在黃埔軍校和上海大學講課,滔滔不絕,風度翩翩,聽課的人擠滿了禮堂,連著名作家丁玲都為之傾倒:“最好的教員卻是瞿秋白……他講希臘、羅馬,講文藝復興,也講唐宋元明。他不但講死人,也講活人。他不是對小孩講故事,而是把我們當作同游者,一同游歷上下古今,東南西北。”
當文人當到這個份上,只有瞿秋白了。
4
“左翼文壇兩領導,瞿霜魯迅各千秋。文章煙海待研證,捷足何人踞上游。”這是文壇巨匠茅盾對魯迅和瞿秋白的贊譽。他們兩人,在時空交織中演繹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曠世情誼。
他們的友誼引起了我的興趣。
自古文人相輕,但他們沒有這種陋習。他們欣賞彼此的才華,還未見面卻感覺神交已久。瞿秋白對茅盾說:“我讀過魯迅的很多文章,很佩服他的人品和文才。只是一直無以謀面,始終引為憾事。”對瞿秋白,魯迅是欣賞和愛惜的,他與馮雪峰談興最濃的便是瞿秋白的文學才華。他說:“這是個很有才華的青年,他的《莫斯科通訊》,我看過,翻譯的文章耐看好看。”“何苦(瞿秋白筆名)雜文,明白暢曉,一覽無余,真有才華,是真可佩服的。他的論文真是皇皇大論!在國內文藝界,能夠寫這樣論文的,現在還沒有第二人。”
兩人最初的往來,是從魯迅讓瞿秋白翻譯文章開始的。魯迅早就想從俄文版本直接翻譯俄羅斯文藝理論的文章,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適的人,只能從日文版本轉譯,原汁原味的效果自然就差了許多。瞿秋白到上海養病,解決了魯迅一直耿耿于懷的遺憾。誰都知道瞿秋白的俄文功底數一數二。很快,魯迅就給瞿秋白安排了一個“大活兒”——曹靖華從蘇聯給魯迅寄來《鐵流》譯稿,不知是粗心還是遺漏,序沒有譯。魯迅立即委托馮雪峰請瞿秋白翻譯。瞿秋白接受序文后,很快便流暢地翻譯出來。魯迅讀后大為贊嘆,在給曹靖華的信中高度贊揚說:“那譯文直到現在為止,是中國翻譯史上空前的筆了。”對此,魯迅還在《〈鐵流〉編校后記》中對瞿秋白大加贊賞:“沒有木刻的插圖還不要緊,而缺乏一篇好的序文,卻實在覺得有些缺憾。幸而,史鐵兒(秋白筆名)竟特地為了這譯本而將涅拉陀夫的那篇翻譯出來了,將近二萬言,確是一篇極重要的文字。”
瞿秋白給魯迅的第一印象如此完美。
不久,魯迅又將俄羅斯作家盧那察爾斯基的《被解放的唐·吉訶德》劇本交給瞿秋白。瞿秋白很快用“易嘉”的筆名將其翻譯出來。劇本先在《北斗》刊載,后又出單行本。魯迅讀過譯本后,曾對友人說“那時我的高興,真是所謂不可以言語形容”。他還在《后記》中專門稱贊這篇譯文:“注解詳明,是一部極可信任的本子。”
魯迅將日文版《毀滅》轉譯成中文,并特意讓瞿秋白對照俄文本校讀。瞿秋白校讀后,抑制不住激動的心情,給魯迅去了封長信,直接以“敬愛的同志”相稱,說:“你譯的《毀滅》出版,當然是中國文藝生活里面的極可紀念的事跡。”他還在信中表述了相見恨晚的敬仰之情:“所有這些話,我都這樣不客氣的說著,這自然是沒有禮貌。但是,我們是這樣親密的人,沒有見面的時候就這樣親密的人。這種感覺,使我對于你說話的時候,和對自己說話一樣,和自己商量一樣。”魯迅讀到這封長信,也是十分高興,立即給瞿秋白回信,以“敬愛的J、K、同志”(瞿秋白來信時的署名)相稱。
從此,書信你來我往,兩顆息息相通的心越貼越近,他們都急切地盼望著早日會面。
瞿秋白和魯迅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32年夏天。那天早上,瞿秋白由馮雪峰陪同,來到了北川公寓魯迅的寓所。兩人初次見面,竟如久別重逢的朋友,親切自然,無拘無束,一點矜持尷尬的表情也沒有。他們暢所欲言,從政治談到文藝,從理論談到實際,從希臘談到蘇聯,甚至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文壇的趣事,也談得津津有味,妙趣橫生。魯迅年長瞿秋白十八歲,在年齡上屬于兩代人,算是瞿秋白的長者與前輩,可他們沒有這種隔閡,一見如故,相見甚歡。兩個人好像有說不完的話,直到晚間,瞿秋白才告別回家。
很快,他們倆成了無所不談的文友、朋友、知己。
瞿秋白在上海養病期間,經濟上常常入不敷出。魯迅用各種適當的方法,予以雪中送炭般的扶助。魯迅原打算把他的《二心集》和瞿秋白翻譯的高爾基四篇短篇小說一起讓合眾書店出版,但書店不愿買下瞿秋白的譯作,魯迅就把《二心集》的版權一起售出,書店方才同意,《二心集》因而成為魯迅著作中唯一出售版權的書。后來,魯迅將他編譯的蘇聯短篇小說集《一天的工作》交給良友出版公司出版,這本小說集共收十篇小說,其中兩篇由楊之華譯出初稿,再由瞿秋白校改定稿。尚未得到稿酬時,魯迅就拿出六十元給瞿秋白夫婦。如果沒有魯迅持續不斷的經濟上的支持,瞿秋白在上海期間是很難寫出那么多傳諸后世的文章和譯作的,夫妻倆的生活也會捉襟見肘。更可貴的是,魯迅冒著生命危險,四次將瞿秋白藏于家中避難,朝夕相處,親如一家。為了使瞿秋白有一個比較安全的生活和寫作環境,魯迅委托日本友人出面,在比較僻靜的山陰路東照里十二號,幫他們夫婦租下一處仿日式的三層建筑的二樓南間。雖然面積只有十六平方米,但居室整齊,南有四扇大窗,光線充足,既可寫作,又可養病。魯迅還親書對聯以賀瞿秋白喬遷:“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簡簡單單的十六個字,濃縮了這對生死之交、惺惺相惜的人生知己的全部情誼。
1935年初,瞿秋白在福建長汀不幸被捕。在生命最危險的時刻,他向魯迅發出求救信號,將身家性命托付給這位認識并沒有多久的忘年交。而魯迅也真的動用所有關系營救瞿秋白……聽到瞿秋白就義的消息,魯迅極為悲憤,長時間“木然地坐在那里,一言不發,悲痛得頭也抬不起來了”。他在致蕭軍信中寫道:“足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
瞿秋白走后,據許廣平回憶,魯迅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悲痛不已,甚至連執筆寫字的興致也提不起來。但有一件事不能耽擱,那就是整理編印瞿秋白的譯述,那是對好友最大的告慰。那時魯迅的病情日漸加重,經常咳嗽和發低燒,體重只有三十幾公斤,但他頑強地撐持著病體,與鄭振鐸、茅盾等人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編輯《海上述林》上。從編輯、校對、設計、裝幀、題簽到擬定廣告、購買紙張、印刷裝訂等,魯迅事事躬親、一絲不茍,并親自為《海上述林》上下卷寫了序言。然后,魯迅托內山完造先生寄往日本東京印刷。值得一提的是,編輯所署的并不是魯迅等人的名字,而是“諸夏懷霜社”。“諸夏”即中國,“霜”為瞿秋白的原名,“諸夏懷霜”,意為中國人民永遠懷念瞿秋白。
很快,在日本印刷的《海上述林》上卷寄至上海。魯迅“即開始分送諸相關者”。為了擴大《海上述林》的影響,魯迅親擬廣告一則,讓更多人去購買,去閱讀……該書出版后十七天,魯迅病逝,他沒能看到《海上述林》下卷問世。
5
也許,瞿秋白的武器不是刀槍,而是筆墨。
就是這樣一位文人,面對審訊,他坦然說自己是一個醫生;面對款待,他坦然使用;面對誘勸,他毅然拒絕。酷刑折磨的是肉體,溫情折磨的是精神和意志。許多人沒有在酷刑中倒下,卻在溫情中背叛,有的連刑也不用就倒下了。識時務者不一定是俊杰,也許是敗類。可獄中的瞿秋白,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病人,一個瘦弱蒼白的書生,一個溫和的革命者,其內心卻是銅墻鐵壁,是鋼筋鐵骨,是堅不可摧的文人傲骨。一切勸降、軟化、利誘,在瞿秋白的信仰面前通通灰飛煙滅。
生命只有一次,他也渴望生命的長久,但他說“人愛自己的歷史,勝于鳥愛自己的翅膀,請勿撕毀我的歷史”。在真理和生命面前,他選擇了真理,寧愿站著死,也不愿跪著茍且偷生。
瞿秋白自從被俘,早已抱定必死的決心。他認為,死不過是一個結局,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就像花開花落。死亡不過是一個綿長的夢,一次不會醒來的沉睡,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死亡只是趕赴一個長眠之約罷了。他把死亡看得如此透徹,還有什么可怕的呢?
瞿秋白是一位文人,卻更像一名戰士。他要“為大家開一條光明的路”,所以他放棄了教書育人的悠閑生活,北上追求心中的夢想。面對民族危亡,有人躲進世外桃源,有人獨善其身,有人賣身求榮,他卻投身時代洪流。混沌歲月,他如黑暗中的明燈,照亮著千萬先驅者的腳步,難怪戴季陶氣急敗壞地說過:“瞿秋白赤化了千萬青年,這樣的人不殺,殺誰?”
“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在1927年那濁浪排空的日子里,脫黨的脫黨,懺悔的懺悔,叛變的叛變,有的人屈服了,有的人頹廢了,有的人畏縮了,有的人消沉了。但瞿秋白沒有,他臨危受命,柔肩擔重義,由他主持的臨時中央常委會斬釘截鐵,力挽狂瀾。八七會議,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哪一件不是一個轉折,一個巨變,一個豐碑!
作為一介書生,也許他不適合做領袖;就組織才能和軍事才能而言,他也不是最杰出的。當革命把他推到風口浪尖時,他不是退縮,不是膽怯,不是推讓,而是迎風而立,挺身而出,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拉扯著隨時都會沉沒的中國革命航船,咬著牙,一步一步地前行!
他可以挺身而出,也可以主動讓賢。他不是權力的追隨者,也不是迷戀者。面對人生曲折委屈,變節的何止少數。可他志向不改,不能指揮千軍萬馬,他就重操舊業,拿起筆做武器,在上海與親愛的戰友魯迅并肩作戰,領導左聯,利用一切機會發表各種關于時局的評論文章,文字與他,一樣是戰斗。
6
毫不夸張地說,如果瞿秋白專心致志于自己的“興趣”,足可以成為大師級的人物。不問世事,不問政治,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春夏與秋冬,全心文學事業,當學者,當作家,同樣是著述等身,睥睨學世,如同時代的作家林語堂、梁實秋等人那樣,因為選擇了“純文學”的道路,日后都成了大作家。
他還可以像千千萬萬普通的中國人一樣,經營自己的小家庭,也能使日子充滿溫馨。就性情而言,瞿秋白其實是很“小資情調”的,紀念館里那幾張他和妻子在西湖畔、黑海旁的才子佳人式的合影,處處似水柔情,浪漫迷人,即使放在今天的相館櫥窗里,也是非常時尚的。瞿秋白繞道柏林回國途中,在柏林廣場的文化角,還頗有雅興地請剪紙藝人給他剪了一張剪影。
此情可待成追憶,亂世奇緣如煙縷。民國有幾大亂世奇緣: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陸小曼、徐志摩、翁瑞午,王映霞、郁達夫、許紹棣……這些才子佳人,有的是有情人終成眷屬,有的卻反目成仇兩敗俱傷。其實,瞿秋白與楊之華的戀情,也堪稱一大奇緣。他們以浪漫開場,中間伴有戲劇性的沖突,卻以皆大歡喜結尾,演繹了一場蕩氣回腸的兒女情長。瞿秋白曾經結過婚,他與第一任妻子王劍虹因為志趣相投,目標同向,又有文學的共同愛好,很快墜入愛河,相愛不到半年就結為夫妻。他們每天過著如詩如畫的生活,回家就是談詩與寫作。只可惜兩人結婚七個月后,王劍虹就因患有肺結核而逝世。而楊之華此時已經嫁給富家子弟沈劍龍。兩個人是娃娃親,沈劍龍生得儀表堂堂,只因商場打拼失敗,不免意志消沉,沾了不少風月之氣,而楊之華十幾歲就外出求學,海闊天空,心境不斷變化,兩人奉父母之命成婚,卻有些貌合神離。
命運偏偏安排瞿秋白與楊之華在上海大學相遇了。瞿秋白的才華學識讓楊之華為之傾倒,而楊之華的花容月貌、知書達理也讓瞿秋白心有所動,兩人心心相印卻又備受煎熬。
怎么辦?
瞿秋白與楊之華做出了大膽的決定,向沈劍龍表明他們的心意。懷著惴惴不安的心情,卻出現了戲劇性的結果。三人相見,兩個男人沒有怒目相向的敵意,沒有破口大罵的粗俗,也沒有拳打腳踢的野蠻,更沒有拔劍決斗的慘烈。居然一見如故,就好似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在一起談天說地。沈劍龍欽佩瞿秋白的才華和人品,瞿秋白也欣賞沈劍龍的豪爽與膽識。于是,欣賞代替了情仇,默契滋生了寬容。結局自然水到渠成,沈劍龍主動退出,瞿秋白與楊之華幸福地走在了一起。他們離婚、結婚的告示,刊登在《民國日報》頭版的廣告欄里,一下轟動了全國。
婚后,瞿秋白還刻下一枚“秋之白華”的印章,寓意與楊之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情。而楊之華與沈劍龍所生的女兒也跟了秋白的姓,改名為瞿獨伊。秋白待她,就如同親生女兒一樣。
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瞿秋白如果就這樣“小資”下去,同樣可以生活得有滋有味,然而他沒有,因為他選擇了革命。
7
在人生的最后時光里,他偏偏留下了一篇解剖自己心靈的《多余的話》。他剖析自己一生的成敗榮辱,而不是像方志敏那樣用詩一般的語言寫下《可愛的中國》,或者像葉挺一樣在囚牢的墻上用鮮血寫下《囚歌》。
就是這篇《多余的話》,給了那些所謂純粹的人、忠貞的人、完美的人,還有那些心懷叵測、動機不純、吹毛求疵的人以話柄……于是許多人感到惋惜,感到遺憾,感到不解,感到憤怒,他們不容忍一個革命者在敵人的獄中寫下這樣斑駁的文字。
《多余的話》多余嗎?當人們逐步接近真理、還原真理時,才明白《多余的話》并不多余。
只因為,瞿秋白不僅是一個戰士,也是一位文人。
文人總歸有些理想化。講一個小故事,文字改革,瞿秋白極力主張漢字拉丁化。可他忘記了,中華上下五千年文明經久不息,正是有了漢字的獨特魅力。每一個漢字都是文明的象征,都是文化的延續。跟他同鄉的語言大師趙元任專門寫了一篇文章來反駁,全文九十六個字,就一個讀音:“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施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施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尸,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施氏始試食是十獅尸。食時,始識是十獅尸,實十石獅尸。試釋是事。”
這篇文章朗朗上口,韻律跌宕,漢語文詞的美學特征畢現,拉丁化改革就此偃旗息鼓,煙消云散。
做一個有信仰的人不難,做一個意志堅定的人也不難,但能客觀地自我解剖和反省的人,能有幾人?又有幾人敢把自己的內心袒露給世人與后人?瞿秋白是一個文人,也是一位戰士,更是一個有情有義、有血有肉、有優點也有缺點的革命者。無論生前風云際會、歷盡悲苦,還是身后備極哀榮抑或背負污名,他的內心始終真實、真誠、坦蕩,在我的面前樹起了一座豐碑,令人感嘆、折服、崇敬。
中國有句古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論語》中講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人生需要反省,社會需要反省,時代需要反省,尤其在這個物化的時代,在這個信仰和精神缺失的社會……反省會讓我們更文明,更強大。
出得門來,我再一次駐足在梁衡先生的雄文前:“秋白以沒落世家子弟受勞苦大眾之苦;以一柔弱書生當領袖之任;以學富五車、才通六藝之軀,充一普通戰士,去作生死之搏。像山高嶺險而生勁松,霧多露重而產名茶,歷史的風口、浪尖、滾雷、閃電下站起了一個瞿秋白。”在希臘神話里,普羅米修斯盜取天火,照亮塵世,而馬克思則說,“我就是普羅米修斯!”瞿秋白,還有“常州三杰”中的張太雷、惲代英,以及千千萬萬的仁人志士,他們就是中國的普羅米修斯。
讓我們記住他的名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