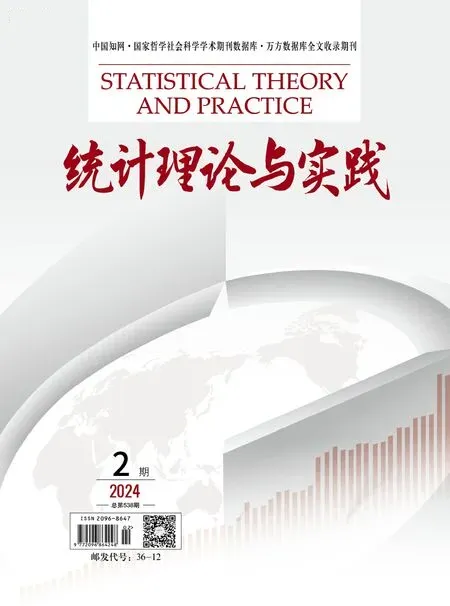中國城市相對貧困的統(tǒng)計測度及其分解
李壯壯
(宿州學(xué)院數(shù)學(xué)與統(tǒng)計學(xué)院,安徽 宿州 234000)
一、引言
據(jù)專家預(yù)測,未來全球的貧困人口分布以城市居多,特別是發(fā)展中國家,城市貧困將成為阻礙其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城市相對貧困問題越來越復(fù)雜,成為中國貧困治理的難關(guān)。2000年中國城市人口僅占總?cè)丝诘?6.22%,2022年中國城鎮(zhèn)化率已達65.22%。大量的農(nóng)村人口涌入城市,由于自身家庭經(jīng)濟條件的脆弱性,他們?nèi)菀壮蔀槌鞘械娜鮿萑后w,而且受醫(yī)療支出、教育負(fù)擔(dān)、住房條件、社會救助、負(fù)面情緒等因素影響,新進入城市的農(nóng)村居民家庭壓力越來越大,直接影響家庭成員的生活滿意度和家庭幸福感,間接給城市發(fā)展增添許多不穩(wěn)定因素。因此,緩解城市相對貧困對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具有重要意義。
分析已有研究成果,學(xué)術(shù)界關(guān)于相對貧困問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基于收入指標(biāo)的相對貧困標(biāo)準(zhǔn)線的確定[1-3];二是基于非收入指標(biāo)的相對貧困多維度體系的設(shè)置[4-6];三是基于A-F法的相對貧困綜合指數(shù)的構(gòu)建和分解[7-9]。收入指標(biāo)的相對貧困標(biāo)準(zhǔn)線以中位數(shù)或平均數(shù)的30%—60%為主。多維相對貧困指標(biāo)體系主要包括教育、就業(yè)、健康和生活水平等。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的測度方法和分解模型主要集中于對A-F法的使用。從已有研究成果看,關(guān)于中國城市相對貧困的研究文獻已有一定數(shù)量,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一是已有相對貧困研究成果的研究對象多是農(nóng)村居民家庭,對城市居民家庭相對貧困的研究匱乏;二是相對貧困多維研究以經(jīng)濟指標(biāo)為主,在非經(jīng)濟指標(biāo)體系的構(gòu)建上尚不完全一致;三是主要利用綜合評價法測度多維相對貧困程度,但綜合評價法難以量化貧困程度,在測度不同相對貧困程度時存在缺陷。本文基于以上研究不足,在構(gòu)建中國城市相對貧困評價指標(biāo)體系的基礎(chǔ)上,利用雙界線A-F法測度和分解中國城市相關(guān)貧困程度并深入探究其原因,以期為中國城市相對貧困的統(tǒng)計監(jiān)測提供對策建議。
二、理論依據(jù)
(一)相對貧困的內(nèi)涵
相對貧困是一種人與人在比較中產(chǎn)生的貧困現(xiàn)狀,主要反映相對經(jīng)濟差距,是測定社會收入不均等復(fù)雜社會現(xiàn)象的重要依據(jù)。相對貧困的存在與經(jīng)濟水平有著密切關(guān)系,其核心是收入不平等和社會分配不均衡。多維相對貧困的概念基于1983年印度學(xué)者Sen提出的能力貧困理論[10],從其觀點看,貧困不僅沒有收入來源,而且無法獲得醫(yī)療健康、教育、生活保障等基本服務(wù)。所以貧困本身應(yīng)該是多維的,多維貧困指標(biāo)體系是一種包含收入指標(biāo)在內(nèi),涵蓋多方面因素去判斷各維度指標(biāo)能力剝奪情況的評價體系。多維貧困理論測定貧困比單純以收入測定貧困更能準(zhǔn)確把握貧困的本質(zhì),為扶貧理論研究提供更加實用和有效的方案。
城市的相對貧困與傳統(tǒng)城市貧困和傳統(tǒng)農(nóng)村貧困不同。農(nóng)村貧困更多與長期的社會經(jīng)濟制度相關(guān),傳統(tǒng)城市貧困更多與無勞動能力、無撫養(yǎng)人、無生活來源的貧困相聯(lián)系。而新發(fā)展階段的城市相對貧困具有新時代制度變遷和社會發(fā)展的特征,出現(xiàn)在我國實現(xiàn)全面小康之后。我國多維相對貧困內(nèi)涵的演進如圖1所示。中國相對貧困理論以馬克思主義貧困理論為基礎(chǔ),并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zhì),隨著國情的變化不斷發(fā)展。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正在從輸血式扶貧向開放式、造血式、多角度精準(zhǔn)扶貧轉(zhuǎn)變,精準(zhǔn)扶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扶貧理論的核心[11]。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消除絕對貧困后,我國在努力構(gòu)建脫貧攻堅的長效機制和管理模式,鞏固來之不易的脫貧成果,致力于先富帶后富,有效緩解相對貧困,最終實現(xiàn)共同富裕。

圖1 我國相對貧困的概念和內(nèi)涵圖解
(二)相對貧困測度方法的探索
2010年,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UNDP)協(xié)同牛津大學(xué)貧困與人類開發(fā)倡議(OPHI)提議從健康、教育、生活水平3個角度測度多維貧困,并設(shè)置了10個指標(biāo)的貧困門檻值和權(quán)重分布,從不同視角反映全球不同地區(qū)的貧困發(fā)生率、貧困發(fā)生強度和被剝奪程度。全球多維貧困指標(biāo)體系見圖2。
此外,借助一種被稱為“知識匯合”的理論,第四世界扶貧國際運動協(xié)同坦桑尼亞、孟加拉國、法國、維多利亞、美國和英國的研究者,研究貧困的維度和指標(biāo)構(gòu)成,最終選擇了6個維度和影響貧困的5個因素,見圖3。

圖3 貧困維度和調(diào)節(jié)因素
從國際已有的貧困測度方法看,當(dāng)人類發(fā)展到一定階段,貧困測度不能僅停留在對溫飽的考察,城市相對貧困的測度更為復(fù)雜,不能僅考慮收入這一因素,需要綜合考慮貧困家庭的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和社會因素等方面[12]。結(jié)合國際多維貧困的內(nèi)涵和測度實踐,本文主要從收入水平、教育程度、健康狀況、生活水平、社會保障、就業(yè)、信息利用7個維度研究中國城市多維相對貧困問題。
三、指標(biāo)體系和測度方法
(一)多維相對貧困指標(biāo)體系的構(gòu)建
(1)收入維度。由于純收入能更好地反映收入的增加,因此2012年以后,中國家庭追蹤調(diào)查(ChinaFamily PanelStudies,CFPS)數(shù)據(jù)庫只制定并公布家庭純收入綜合數(shù)值。本文構(gòu)造的家庭收入變量主要基于2018年家庭經(jīng)濟問卷數(shù)據(jù),將人均家庭純收入作為測度收入相對貧困的指標(biāo),并將2018年我國政府制定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biāo)準(zhǔn)6956元作為剝奪臨界值,低于該水平賦值為1,視為收入維度貧困,否則為0。
(2)教育維度。相關(guān)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兒童入學(xué)率高達99%,故入學(xué)率不適合用于現(xiàn)階段的城市相對貧困測度。本文選取受教育年限作為教育維度評價指標(biāo)。將城市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不滿9年的個體視為教育貧困,賦值為1,否則為0。
(3)健康維度。考慮到健康狀態(tài)的自我評價主觀性較強,因此本文沒有選取這一指標(biāo),而是選擇CFPS數(shù)據(jù)庫中“是否患有慢性疾病”“是否患病住院”這兩個指標(biāo)。當(dāng)每戶家庭中有成員半年內(nèi)患有慢性病、有成員過去一年內(nèi)因病住院時,視為醫(yī)療健康維度相對貧困,賦值為1,否則為0。同時,在CFPS數(shù)據(jù)庫中選取幸福指數(shù)作為心理健康評價指標(biāo)。每戶家庭人均幸福值低于4,視為心理健康貧困,賦值為1,否則為0。
(4)生活水平維度。生活水平內(nèi)容涵蓋用水、炊用能源、電、金融資產(chǎn)、住房資產(chǎn)、人均耐用消費品總值等眾多內(nèi)容,基于城市經(jīng)濟生活各方面的基本標(biāo)準(zhǔn)和城市家庭特征,不再選擇水、電、炊用能源等指標(biāo),僅選取家庭住房指標(biāo)和家居整潔度指標(biāo)。家庭住宅是只有產(chǎn)權(quán)的一部分、公共住宅、廉價租賃住宅、公共租賃住宅、市場租賃的商品房、親朋之家和其他有居住條件的住宅,設(shè)置數(shù)值為1,否則為0。家居整潔度評分在4分以下,視為生活水平維度的相對貧困,賦值為1,反之為0。
(5)社會保障維度。隨著中國城市老齡化加速,沒有工作和收入的老年人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經(jīng)濟壓力,養(yǎng)老保險已變成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如果城市家庭樣本中有成年人無法領(lǐng)取養(yǎng)老保險,則該家庭被視為貧困。
(6)就業(yè)維度。考慮到城市就業(yè)壓力大但是選擇機會多等因素,將就業(yè)類型作為衡量城市相對貧困人口的依據(jù)。如果一個家庭中的成年人長期處于失業(yè)狀態(tài),則將其判定為城市相對貧困人口,賦值為1。
(7)信息利用維度。在信息化時代,智能手機為必備品,手機不僅能發(fā)消息和打電話,滿足城市居民日常社交需求,還可以進行網(wǎng)購和支付,對當(dāng)下城市人群至關(guān)重要。因此本文將是否擁有智能手機作為衡量城市居民信息利用維度的貧困標(biāo)準(zhǔn)。
本文構(gòu)建的具體指標(biāo)體系及界定見表1。

表1 多維貧困識別指標(biāo)體系
(二)多維相對貧困的測度
本文采用A-F雙臨界值法,對多維相對貧困群體進行雙重識別。A-F法是由Alkire和Foster(2011)[13]為計算貧困指數(shù)而提出的方法。它綜合不同維度、指標(biāo)權(quán)重以及個人、家庭的貧困數(shù)據(jù)建立多維貧困指標(biāo)體系,主要通過設(shè)定兩層界線識別貧困。
首先是貧困的第一層識別:建立指標(biāo)體系,設(shè)置各指標(biāo)臨界值,識別未達到臨界值的指標(biāo)。
其次是貧困加總:將不達標(biāo)指標(biāo)的個數(shù)相加,根據(jù)設(shè)定的權(quán)重,測算個體在所有維度下的剝奪得分。
接著是貧困的第二層識別:通過加總后設(shè)定門檻值的界限,判別陷入多維貧困的個體數(shù),計算剝奪率和平均剝奪份額。
最后計算MPI指數(shù),即多維貧困剝奪率和平均剝奪份額的乘積。
1.多維相對貧困的識別
構(gòu)造一個n×d維的矩陣Y=[yij]nd,矩陣任一元素yij表示樣本中第i個人的第j個維度的取值,i的取值范圍為[1,n],j的取值范圍為[1,d]。向量yi表示d個維度個體i的值;向量yj表示在j維度有n個個體。假定每個維度的貧困標(biāo)準(zhǔn)線用zj表示,對于矩陣Y建立一個剝奪矩陣G=[gij],當(dāng)yij≥zj時,gij=0,表示未陷入貧困;當(dāng)yij<zj時,gij=1,表示陷入貧困。
當(dāng)識別貧困的第一層次后,開始第二層次的貧困識別。設(shè)置各維度的權(quán)重為wj,并對剝奪矩陣值進行加權(quán)求和。假設(shè)個體i陷入多維貧困的門檻值界限為k,通過比較加權(quán)貧困剝奪值與k值,可以得到多維貧困剝奪份額矩陣C=[ci]T,即當(dāng)當(dāng)時,ci=0。
構(gòu)造多維貧困矩陣Q=[q1,q2,…,qn]T,識別個體的多維貧困狀況。當(dāng)ci>0時,qi=1,表明個體陷入多維貧困;當(dāng)ci=0時,qi=0,表明個體未處于多維貧困狀態(tài)。
2.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計算
MPI指數(shù)根據(jù)各個維度的貧困程度加總計算得出,具體計算公式如下:
其中,q是在陷入多維貧困的臨界值取k的情況下的多維相對貧困人口數(shù),H是多維相對貧困發(fā)生率即剝奪率,A為多維相對貧困強度即平均被剝奪份額。
3.多維相對貧困的分解
先按照指標(biāo)計算全體樣本的貧困指數(shù),再按照指標(biāo)維數(shù)加權(quán)得到按指標(biāo)分解的多維貧困指數(shù),公式如下:
不同指標(biāo)維度下的各指標(biāo)對貧困的貢獻率為:
為進一步得到各地區(qū)城市家庭樣本的貧困特征,按子樣本進行分解,具體公式如下:
其中,M(αk)為第α個(α=1,2,…,m)子樣本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n=nα為城市家庭樣本總量。
4.指標(biāo)權(quán)重的設(shè)置
通用做法是采用等權(quán)重法,即將所有指標(biāo)采用等額權(quán)重的方法進行計算。對具有不同維度的評價體系來說,首先賦予維度等權(quán)重,再對各維度下的指標(biāo)賦予等權(quán)重。本文采用等權(quán)重賦權(quán)法設(shè)置的各指標(biāo)權(quán)重見表1。
四、數(shù)據(jù)來源、測度結(jié)果和分解
(一)數(shù)據(jù)來源
本文的實證數(shù)據(jù)來自2018年CFPS數(shù)據(jù)庫,即中國家庭追蹤調(diào)查數(shù)據(jù)庫,涵蓋全國31個省(區(qū)、市),是北京大學(xué)中國社會科學(xué)調(diào)查中心帶頭組織實施的社會跟蹤調(diào)查項目。問卷內(nèi)容分為個人和家庭樣本數(shù)據(jù),可以反映中國社會、經(jīng)濟、人口、教育等變化,為監(jiān)測中國城市居民的多維貧困狀況提供有力支撐。
指標(biāo)體系的構(gòu)建遵循科學(xué)、全面、有針對性原則,先選取維度指標(biāo),再在精準(zhǔn)識別指標(biāo)內(nèi)涵的基礎(chǔ)上,對其進行劃分。本文所使用的變量結(jié)合了家庭經(jīng)濟數(shù)據(jù)庫和個人自答庫的核心數(shù)據(jù),得到我國家庭多維貧困測度的基礎(chǔ)樣本17623份。對重復(fù)值、無效值和缺失值進行適當(dāng)處理后,得到有效城市居民家庭樣本7447份。
(二)測度結(jié)果
利用公式(1)、(2)、(3)測算中國城市的多維相對貧困發(fā)生率、平均剝奪份額以及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結(jié)果見表2。

表2 中國城市多維相對貧困的測算結(jié)果
表2顯示,隨著k值增加,多維相對貧困發(fā)生率和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呈下降趨勢,且下降速度較快,說明城市多維相對貧困程度隨著維度增加迅速下降;而平均剝奪份額隨著k值增加逐漸增加,說明我國城市家庭貧困人口的貧困強度隨著更多維度的貧困剝奪而逐漸增加。具體看,k=0.1時的多維相對貧困發(fā)生率為87.9%,表明有87.9%的城市家庭處于在某一指標(biāo)維度的相對貧困,剝奪強度為0.315,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為0.276;當(dāng)k的取值上升到0.8時,多維相對貧困發(fā)生率下降到0.1%,多維貧困指數(shù)下降到0.001,說明至少存在8個指標(biāo)被剝奪的家庭已經(jīng)很少,不存在9個以上指標(biāo)被同時剝奪的家庭。
(三)指數(shù)分解
利用公式(4)、(5)、(6)、(7)分解中國城市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按照省(區(qū)、市)分解的中國城市多維相對貧困結(jié)果見表3;按照維度和指標(biāo)分解的中國城市多維相對貧困結(jié)果見表4。

表3 按省(區(qū)、市)分解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k=0.3)

表4 按維度和指標(biāo)分解的剝奪貢獻率(k=0.3)
從各省(區(qū)、市)分解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看,天津、重慶、福建、江西等地區(qū)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最低;一些中西部地區(qū)如山西、陜西、江西、廣西、貴州和安徽的多維相對貧困程度較低,河南、遼寧、四川、甘肅的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較高;經(jīng)濟發(fā)展程度較高的上海、廣東等地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反而很高。表明經(jīng)濟增長雖然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居民相對貧困程度,但在新階段城市相對貧困治理中,很容易忽視收入差異和分配不均衡對外來城市居民在教育、醫(yī)療和健康等方面的影響,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城市相對貧困人口識別的難度。采用統(tǒng)一的收入相對貧困線來判定城市相對貧困人口并不能準(zhǔn)確地反映經(jīng)濟發(fā)達地區(qū)和經(jīng)濟落后地區(qū)的城市多維相對貧困人口。所以,政府部門要根據(jù)不同經(jīng)濟地區(qū)的實際情況制定符合當(dāng)?shù)爻擎?zhèn)居民人均收入差異情況的扶貧政策。
從維度看,教育維度指標(biāo)的剝奪貢獻率最高,為27.4%,其次是就業(yè)維度25.3%,接著是社會保障維度22.1%,健康、生活水平維度分別為8.6%、8.1%。從指標(biāo)分解看,受教育年限、就業(yè)狀態(tài)和養(yǎng)老保險的指標(biāo)貢獻率均超過20%;健康維度中慢性病指標(biāo)的剝奪貢獻率較高,為4.4%,略高于因病住院影響貢獻率,幸福指數(shù)指標(biāo)貢獻率最低為0.9%;在生活水平維度中,家居整潔度貢獻率為5.0%,高于家庭住房貢獻率;在信息利用維度中智能手機持有率的指標(biāo)貢獻率為7.0%;人均家庭純收入的剝奪貢獻率最少,僅有1.5%。相比收入的相對剝奪情況,其他維度指標(biāo)像教育、就業(yè)和社會保障等的相對剝奪情況更嚴(yán)重。
為深入分析各維度、各指標(biāo)對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的貢獻,查找城市居民相對貧困的主要致貧因素,本文測量得出了各指標(biāo)的剝奪貢獻率,見表5。隨著k值的增加,收入和信息利用維度指標(biāo)的相對剝奪貢獻率逐漸上升,教育維度指標(biāo)的剝奪貢獻率逐漸下降,健康、生活水平和就業(yè)維度指標(biāo)的相對剝奪貢獻率變化不大。說明考察更多維度下的相對貧困,就業(yè)、健康、生活水平對城市居民相對貧困的影響較為穩(wěn)定。

表5 各指標(biāo)剝奪貢獻率
五、主要結(jié)論和對策建議
本文構(gòu)建多維相對貧困指標(biāo)體系,實證研究了我國城市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程度、省際差異和主要致貧因素。研究發(fā)現(xiàn):第一,我國城市相對貧困發(fā)生率和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均呈下降趨勢,扶貧政策不僅對農(nóng)村的絕對貧困消除起到巨大作用,也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城市相對貧困程度。第二,按照省(區(qū)、市)樣本分解多維相對貧困指數(shù),結(jié)果顯示各省(區(qū)、市)城市居民的多維相對貧困程度不僅與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有關(guān),也與地區(qū)的外來人口規(guī)模有關(guān),重視外來常住人口發(fā)展有助于緩解城市的相對貧困水平。第三,通過對比不同指標(biāo)的貢獻率,發(fā)現(xiàn)中國城市相對貧困的中心問題是教育、就業(yè)和社會保障等一些非經(jīng)濟維度,貧困發(fā)生率最高的是受教育年限、就業(yè)狀態(tài)和養(yǎng)老保險這3個指標(biāo),相對貧困發(fā)生率和致貧貢獻率均在較高水平。
根據(jù)上述主要研究結(jié)論,提出以下對策建議:第一,對于中國城市相對貧困問題,需要構(gòu)建一套完整的城市多維相對貧困動態(tài)監(jiān)測指標(biāo)體系,盡可能實現(xiàn)中國城市相對貧困數(shù)據(jù)庫的應(yīng)用,追蹤調(diào)查城市相對貧困家庭基本狀況、心理狀態(tài)、福利狀況等,制定精準(zhǔn)識別中國城市相對貧困規(guī)模及影響的政策。第二,進行貧困人口識別時,應(yīng)從教育、就業(yè)等多個層面測度城市相對貧困,兼顧不同群體的差異性。大城市失業(yè)下崗群體和農(nóng)民工群體是最容易形成相對貧困的群體,針對這部分群體要提供更多的社會關(guān)懷,例如增加就業(yè)崗位、發(fā)放失業(yè)補貼、提高扶貧標(biāo)準(zhǔn)和工資福利等;在醫(yī)療保健和社會保障等方面,需要對這類群體開放更多福利渠道,提供更多人性關(guān)懷,多方面提高其生活水平和就業(yè)能力。第三,受教育程度對城市居民相對貧困程度的影響較大,政府要鼓勵相對弱勢家庭重視子女的教育訓(xùn)練,對其子女教育的各項投入提供便利措施和保障;同時,通過對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提供技能培訓(xùn)扶持,提高其專業(yè)技能和就業(y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