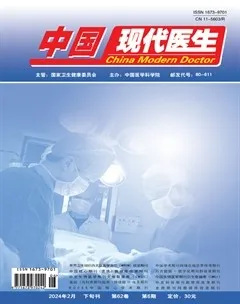眼底血管改變與腦白質高信號的相關性分析
花金萍,徐博倫,詹建梅,熊俊峰,童毓華
1.浙江中醫藥大學第二臨床醫學院,浙江杭州 310000;2.衢州市人民醫院眼科,浙江衢州 324000;3.衢州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浙江衢州 324000;4.衢州市人民醫院放射科,浙江衢州 324000
腦白質高信號(white matter hypertensity,WMH)是腦小血管疾病的影像學表現之一。2013 年,國際神經影像學血管性改變報告標準明確WMH 的定義為雙側大腦白質T2加權成像(T2weighted imaging,T2WI)或液體抑制反轉恢復序列(fluid attenuated inversion recovery sequence,FLAIR 序列)上表現為點、片、融合狀或對稱分布高信號,T1WI 序列上呈等信號或低信號,不包括深部灰質或腦干的病變[1]。WMH 在64 歲左右人群中的患病率達11%~21%,在82 歲左右人群中的患病率高達94%[2]。WMH 與腦卒中、認知障礙、癡呆及死亡的風險增加密切相關[3]。根據2016 年美國心臟協會(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AHA)及美國卒中協會(American Stroke Association,ASA)的共同聲明,腦白質高信號可能與衰老和血管危險因素相關的動脈硬化性微血管疾病有關[4]。目前MRI 是檢測腦小血管疾病最重要的工具,然而MRI 無法檢測到<500μm 的細微退行性變和微血管變化。視網膜作為中樞神經系統的一部分,其發育起源與大腦相似,并具有類似的胚胎學、解剖學和生理學特征[5]。眼底直徑為100~300μm 的小動脈和小靜脈具有與腦小血管相似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特征。因此,視網膜的異常變化可反映腦血管情況,有助于識別高危人群并促進早期干預。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22 年7 月至2023 年7 月于衢州市人民醫院神經內科確診的87 例WMH 患者作為實驗組,同期隨機選擇年齡相匹配的無WMH 的80 名健康體檢者作為對照組。實驗組中男40 例,女47 例,平均年齡(64.60±6.03)歲;對照組中男39 例,女41 例,平均年齡(63.58±6.48)歲。納入標準:①年齡50~84歲;②WMH 符合神經影像學血管性改變報告標準[1];③入選者均行頭顱磁共振檢查且自愿配合做眼底檢查;④入選者均知情同意。排除標準:①近期有皮質下小梗死者;②既往有腔隙性腦梗死者;③腦出血者;④有非血管源性的白質高信號,如多發性硬化、CO 中毒性腦病等;⑤神經退行性疾病,如帕金森、阿爾茨海默病、癡呆;⑥有嚴重的眼底病變疾病,如糖尿病視網膜病變、嚴重的老年性白內障等。本研究經衢州市人民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通過(倫理審批號:衢州市人民醫院倫審2022 研第033 號)。
1.2 方法
1.2.1 光學相干斷層掃描檢查 采用德國海德堡光學相干斷層掃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掃描儀(型號Spectralis OCT)對入選者右眼顳上方距離視盤邊緣0.5~1.0 倍視盤直徑距離的動靜脈血管進行線性掃描。操作者將掃描環的內圓與視盤邊緣等距,手動調整掃描線以確保垂直血管走形。每條血管至少獲取2 張及以上清晰的圖像。操作完成后將圖像垂直水平比率調整為1∶1μm,放大8 倍后保存血管的橫截面圖像。使用ImagJ 軟件(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和半峰寬算法對血管進行測量并計算視網膜動脈外徑及內徑、靜脈外徑及內徑,動脈血管壁厚度=(動脈外徑-動脈內徑)/2,靜脈血管壁厚度=(靜脈外徑-靜脈內徑)/2,動靜脈管徑比值=動脈內徑/動脈外徑,見圖1。

圖1 視網膜血管結構圖像和參數測量
1.2.2 光學相干斷層掃描血管成像檢查 掃描系統切換至Spectralis 光學相干斷層掃描血管成像(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angiography,OCTA),采集黃斑區3mm×3mm 范圍內的淺層毛細血管叢、深層毛細血管叢(deep capillary pleus,DCP)和中央凹無血管區面積(foveal avascular zone,FAZ)圖像,受試者固視正前方的指示燈完成操作。保存沒有明顯運動偽影、血管連續清晰的圖像。ImageJ 軟件計算圖像中的白色像素點與血流信號占圖像總像素點的百分比得到血管密度參數和自動識別獲得FAZ 面積參數,見圖2。

圖2 黃斑區3mm×3mm 微血管密度圖像和參數測量
1.2.3 OCT 測量神經纖維層厚度 掃描視盤時將中心聚焦于視杯的中心,掃描直徑為3.4mm,自動獲得視盤周圍視網膜神經纖維層(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RNFL)厚度。上述眼科檢查均由一名經驗豐富的眼科醫生完成,見圖3。

圖3 各象限視網膜神經纖維層厚度的測量
1.3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6.0 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處理分析。計數資料以例數(百分率)[n(%)]表示,比較采用X2檢驗;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間距)[M(Q1,Q3)]表示,比較采用Mann-Whitney 檢驗;采用二元Logistic 回歸,默認enter 方法分析眼底血管參數與WMH 的相關性。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入選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兩組入選者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兩組入選者的一般資料比較[n(%)]
2.2 兩組入選者的眼底血管結構參數比較
實驗組患者的右眼顳上動脈外徑、內徑小于對照組,靜脈外徑、內徑大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入選者的眼底血管結構參數比較[M(Q1,Q3)]
2.3 兩組入選者的黃斑區微血管密度參數比較
實驗組患者的深層毛細血管叢血流密度小于對照組,淺從與深叢中央凹無血管區面積大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兩組入選者的黃斑區血管密度參數比較
2.4 兩組入選者的神經纖維層厚度比較
實驗組患者的視網膜周圍平均、顳上部、鼻下部的RNFL 厚度小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兩組入選者的視網膜神經纖維層厚度比較[M(Q1,Q3),μm]
2.5 兩組眼底血管參數的二元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是否患有WMH 為因變量(有WMH=1,無WMH=2),將單因素篩選有意義的10 個眼底血管參數作為自變量進行二元Logistic 回歸,結果發現視網膜周圍顳上部、鼻下部神經纖維層厚度減少與WMH 發生風險增高相關,見表5 和表6。

表5 有關自變量賦值

表6 眼底血管參數的二元Logistic 回歸分析
3 討論
WMH 病理機制較為復雜,內皮功能障礙、腦血管反應性受損、靜脈損傷和微栓塞等均為關鍵因素[6-9]。這些因素導致微血管受損,隨后出現白質脫髓鞘和軸突損傷等病理改變。了解微血管損傷,對于識別WMH 病理變化的潛在機制至關重要。以往研究通過眼底照相方法測量視網膜微血管變化,表明小動脈變窄和小靜脈變寬與白質微結構損傷有關[10]。而本研究應用半峰寬算法測量視網膜血管可獲得視網膜血管內外徑、血管壁厚度、小動靜脈比值,顯著降低重復測量的誤差,提高血管測量的準確性[11]。本研究顯示與對照組相比,WMH 患者血管壁厚度、小動靜脈比值差異尚未達到統計學意義,眼底血管結構參數與WMH 無相關性,可能是由于樣本量小所致。
本研究中筆者使用OCTA 測量所有入選者的黃斑區微血管密度,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WMH患者的DCP 血流密度降低,淺叢和深叢FAZ 面積擴大。?evik 等[12]研究結果顯示DCP 血流密度下降有統計學意義,與本研究結果一致。筆者推測,DCP血流密度下降可能與大腦中線粒體功能障礙和高耗氧有關[13]。本研究中WMH 患者FAZ 面積擴大,這一結果與Gao 等[14]研究結果一致。視網膜內FAZ 面積擴大可能繼發于視網膜內神經元和膠質細胞的損傷及其對血流密度的影響[15]。
本研究通過OCT 測量各象限RNFL 厚度,結果顯示WMH 患者視盤顳上部、鼻下部的RNFL 厚度變薄;而正常情況下,視網膜周圍RNFL 下象限和上象限較厚,鼻象限和顳象限較薄。這反映視網膜、視神經、視束損傷導致的視神經軸突損失,這與WMH 的病理機制相似。此前的研究也揭示了WMH與視網膜周圍RNFL 厚度相關[16-17]。
綜上,眼底血管變化對WMH 的發生具有一定的預測價值,OCT 和OCTA 為WMH 患者的早期診斷提供更多可能的成像靶點,可預測腦血管的風險,有利于WMH 患者早期干預和治療。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