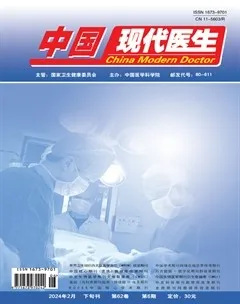麻醉在經內鏡逆行性胰膽管造影術中的應用進展
張林,張寧
臨沂市人民醫院麻醉科,山東臨沂 276000
1 經內鏡逆行性胰膽管造影術(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圍手術期并發癥
低氧血癥、高碳酸血癥、低血壓、鎮靜不足、呼吸暫停、心律失常、膽心反射、心臟驟停、反流誤吸、喉痙攣、喉頭水腫、口腔黏膜損傷是ERCP 患者圍手術期的常見并發癥。體質量指數、性別、美國麻醉醫師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級≥3 級、年齡是ERCP 患者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的獨立預測因素。從氣道管理角度看,ERCP 麻醉分為非插管全麻和插管全麻;根據鎮靜實施的主體不同,又可將ERCP麻醉分為患者自控鎮靜(patient-controlled sedation,PCS)、非麻醉醫師進行的丙泊酚鎮靜(non-anesthesiologist-administered propofol sedation,NAAP)及麻醉醫師指導的鎮靜(anesthetist-directed sedation,ADS)3 種。
1.1 低氧血癥
低氧血癥是非插管全麻期間最常見的不良事件,長時間低氧血癥是心臟驟停、大腦不可逆損傷的主要原因。鎮靜藥物的呼吸抑制及患者的俯臥位體位是導致低氧血癥的主要原因;上呼吸道阻塞、舌后墜、反流誤吸是低氧血癥發生的次要原因。相較于咪達唑侖,丙泊酚的鎮靜和恢復效果更好,但基于丙泊酚的深度鎮靜易發生呼吸抑制。瑞馬唑侖、氯胺酮、右美托米啶、羥考酮等具有低呼吸抑制的特點,可降低圍手術期低氧血癥的發生率,逐漸應用于ERCP。
聲門上氣道裝置等輔助通氣措施常用于減少低氧血癥的發生。經鼻高流量濕化氧療通過產生呼吸末正壓通氣、增加功能殘氣量,降低低氧血癥的發生率[1]。呼吸末CO2監測可實時監測患者的呼吸,降低低氧血癥的嚴重程度[2]。肥胖、馬蘭帕蒂分級≥3級是上呼吸道阻塞的危險因素。鼻咽通氣管法可緩解上呼吸道阻塞并降低低氧血癥的發生率[3]。呼吸興奮劑無法減輕ERCP 期間的呼吸抑制[4]。對于上述措施無法逆轉的低氧血癥應及時行氣管插管,氣管插管可降低俯臥位插管困難,還可提高內鏡中心效率,降低術后喉部不適[5]。
1.2 高碳酸血癥
通氣不足、內鏡期間CO2充氣是高碳酸血癥發生的主要原因。高碳酸血癥可導致患者頭痛、譫妄、顱內高壓癥、腦水腫、昏迷等并發癥。非插管全麻患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高碳酸血癥,且隨著手術時間的延長,高碳酸血癥越嚴重[6-7]。呼吸抑制作用較弱的藥物、聲門上氣道裝置是當前降低圍手術期高碳酸血癥的主要方法。瑞馬唑侖、氯胺酮、右美托咪定等的呼吸抑制作用較弱;內鏡面罩、經鼻咽通氣道高頻噴射通氣有助于維持更高的通氣水平[6-8]。非插管全麻期間,盡管無法完全避免高碳酸血癥的發生,但絕大多數患者手術結束時的CO2分壓均在輕中度范圍內,輕中度高碳酸血癥不會導致不良后果[6-7]。重度肥胖、心肺功能差、手術類型復雜、預計手術時間長的患者易發生重度高碳酸血癥,患者可從氣管插管全麻中獲益。
1.3 低血壓
低氧血癥和高碳酸血癥常見于非插管全麻ERCP 患者,而低血壓則更常見于插管全麻ERCP 患者[9]。肌松藥、揮發性麻醉藥物的擴血管作用是導致低血壓發生率更高的主要原因;俯臥位下靜脈回流減少是導致其發生的次要原因。在圍手術期,低血壓與術后腦卒中、術后病死率、術后譫妄、急性腎損傷等密切相關,且圍手術期低血壓是導致ERCP患者不良預后的主要原因[9]。ERCP 患者多為老年人,老年患者的臟器功能衰退,更易發生圍手術期低血壓。選取循環抑制作用小的藥物、應用血管活性藥物和圍手術期補液是治療圍手術期低血壓的主要手段。瑞馬唑侖、氯胺酮、依托咪酯在這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Park 等[10]研究發現乳酸林格氏液可降低患者ERCP 后胰腺炎的發生率。
1.4 鎮靜不足
鎮靜不足通常見于PCS 和NAAP。鎮靜不足可導致體動、牙齒損傷、高血壓、心率過快等不良事件,應盡量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鎮靜藥物的藥理特性、麻醉管理者的經驗、手術刺激過大等多方面因素可導致鎮靜不足。內鏡進入食道、十二指腸大乳頭切開、球囊擴張時手術刺激顯著增加,最易發生鎮靜鎮痛不足,麻醉醫師應根據手術進程及時調整麻醉深度。圍手術期應用Richmond 躁動-鎮靜評分、Ramsay 鎮靜量表、警覺/鎮靜評分和腦電雙頻指數監測可有效評估患者的鎮靜水平;但腦電雙頻指數監測更有優勢,可避免鎮靜不足或過深帶來的相關并發癥[11-12]。
1.5 其他并發癥
呼吸暫停常見于麻醉誘導完成后,給予手術刺激或面罩吸氧后絕大多數患者隨即恢復自主呼吸。抗膽堿藥物常用于內窺鏡期間解痙攣,其心率加快可增加圍手術期心律失常的風險,麻醉醫師應嚴格把握是否應給予解痙藥及給予解痙藥的劑量和時機。膽心反射可導致心動過緩、血壓下降、心律失常,甚至是心臟驟停等并發癥;急診手術、心律失常、無ERCP 史、術前未應用阿托品、術中未應用膽堿能神經阻滯藥654-2、高齡是發生膽心反射的獨立危險因素[13]。心臟驟停是ERCP 期間最嚴重的并發癥,盡管俯臥位下心肺復蘇(反向心肺復蘇術)被認為是有效的,但考慮其較低的有效按壓率和急救人員操作不熟練等因素,采用正向心肺復蘇術也許更合理。反流誤吸時有發生,處于放射室外的麻醉醫師常無法及時發現,通常是在血氧飽和度下降后才被發現。常規禁食禁飲下,膽汁反流更為常見,膽汁誤吸導致的后果更為嚴重。氣管插管全麻患者無需擔心反流誤吸,因此更具優勢。
2 ERCP 的麻醉方式及其特點
根據鎮靜深度的不同,可將ERCP 麻醉分為抗焦慮鎮靜、清醒鎮靜、深度鎮靜和氣管插管全麻4種水平。
2.1 PCS
PCS 系統包括便攜式計算機和手柄,患者通過按壓手柄控制輸注設定好的鎮靜藥物,從而達到自我控制鎮靜深度的目的。深度鎮靜患者無法繼續加深麻醉,因此PCS 系統鎮靜過度的風險較小,這有利于降低過度鎮靜導致相關并發癥的發生。與NAAP相比,PCS 中的丙泊酚用量和呼吸循環不良事件更少,但鎮靜深度相對較淺、手術耐受程度低、鎮靜失敗率高[14]。PCS 總體失敗率約為20%,手術類型復雜、手術時間過長、高齡患者對PCS 系統操作不熟練、ASA 分級≥4 級、女性患者是PCS 失敗的潛在原因[11-14]。與NAAP 相比,PCS 的麻醉成本更低,NAAP 恢復時間延長導致人力成本增加是總體費用更高的主要原因[15]。丙泊酚和阿芬太尼是最常用的PCS 藥物組合[11-15]。PCS 方式國外有所應用,國內應用較少。因其鎮靜失敗率較高,患者常處于抗焦慮鎮靜或清醒鎮靜水平,其僅能作為一種基礎麻醉方式,現已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2.2 NAAP
在我國,內鏡手術鎮靜只能由麻醉醫師實施;但在國外,NAAP 是被允許使用的。Grossmann 等[15]研究發現NAAP 有助于降低人力成本并節約醫療資源,這或許是使非麻醉醫師參與到內鏡鎮靜管理的動機。盡管NAAP 在胃腸鏡手術中已在國外被認可,但這并不代表非麻醉醫師同樣適合為ERCP 等高級內鏡手術提供鎮靜。相比于NAAP,ADS 有著更高的手術成功率及更低的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16-17]。ADS 與手術時間短、麻醉后恢復快、患者和內鏡醫師的滿意度高有關[18]。考慮到ERCP 手術的復雜性和特殊性,非麻醉醫師并不適合參與ERCP 等高級內鏡手術的鎮靜。隨著時間的推移,非麻醉醫師逐漸退出ERCP 麻醉管理[17]。
2.3 ADS
在ERCP 中,麻醉醫師提供監護下麻醉管理(monitored anesthesia care,MAC)和氣管插管全麻(general anesthesia,GA)兩種麻醉方式,是否保留自主呼吸和進行氣道管理是二者的主要區別。氣管導管和喉罩是最常用的氣管管理措施。相較于氣管導管通氣,患者對喉罩的應激反應更小[19]。與揮發性麻醉相比,靜脈丙泊酚麻醉有著更短的拔管時間、恢復時間和低血壓發生率[20]。是否進行氣道管理導致MAC 在內鏡中心周轉率、呼吸機相關不良事件、插管損傷、肌松藥不良反應、麻醉成本方面占據優勢;但同時也面臨更高的反流誤吸、通氣不足、低氧血癥、高碳酸血癥、鎮靜不足等風險。
3 MAC 和GA 在臨床中的應用
PCS 的先天“劣勢”導致其在ERCP 中應用較少,NAAP 有更高的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因此ERCP 應以MAC 和GA 為主。二者在圍手術期并發癥、內鏡中心周轉率、麻醉費用、患者預后等方面的差異導致麻醉醫師對兩種方式的偏愛不同。
3.1 偏愛GA 的原因
更少的低氧血癥、高碳酸血癥、呼吸暫停、鎮靜不足、手術中斷不良事件及無需擔心反流誤吸是麻醉醫師偏愛GA 的主要原因。相比于MAC,GA的低氧血癥、高碳酸血癥、呼吸暫停不良事件發生率更低[21-22]。肌松藥可提高患者的鎮靜水平,避免體動、咬傷、牙齒損傷等不良事件的發生;還可松弛奧狄氏括約肌、降低胃腸道蠕動,從而提高手術成功率[23]。MAC 所導致的更頻繁的手術中斷、呼吸暫停、低氧血癥事件不一定有著更高的內鏡中心周轉率。盡管無MAC 和GA 在誤吸風險方面的對比研究,但氣管插管患者即使發生反流也不會誤吸;而非插管患者反流誤吸可導致吸入性肺炎等嚴重后果。
3.2 偏愛MAC 的原因
患者更好的預后、更低的費用、更高的內鏡中心周轉率、更少的低血壓事件是麻醉醫師偏愛MAC 的主要原因。相較于GA,MAC 患者的30d 和90d 病死率、術后急性腎損傷和術后肺炎的發生率更低[9]。MAC 的血流動力學更穩定,低血壓事件更少,低血壓是導致GA 預后較差的主要原因[9]。MAC 在恢復時間方面的優勢可抵消處理低氧血癥、鎮靜不足浪費的時間,最終表現出更高的內鏡中心周轉率。盡管無研究對比GA 和MAC 麻醉的成本差異,但氣管插管全麻需要更多的麻醉藥物、耗材、人員配置、更長的術后住院時間都是可預見的,這導致總體費用更高。MAC 下大多數呼吸暫停都是一過性的,輔助鼻高流量濕化氧療、呼吸末CO2監測、高頻噴射通氣、鼻咽通氣管等措施可有效降低低氧血癥的發生率,且短暫缺氧與患者不良結局之間無相關性[9]。此外插管損傷、機械通氣帶來的呼吸機相關不良事件、肌松藥不良反應也是麻醉醫師偏愛MAC 的原因。
4 小結與展望
因PCS 和NAAP 的相對“劣勢”,目前ERCP主要以MAC 和GA 為主。盡管在某些方面尚有爭論,但目前的主流觀點是MAC 在患者預后、內鏡中心周轉率、低血壓發生率、麻醉費用方面占據優勢;GA有更低的低氧血癥、高碳酸血癥、呼吸暫停、鎮靜不足、手術中斷、反流誤吸發生風險。因此,胃腸道出血、反流風險高(胃腸道潴留)、手術時間長(胰腺假性囊腫)、手術類型復雜(大塊結石)、呼吸衰竭、通氣不足風險高(嚴重肥胖)的患者行氣管插管全麻可從中獲益;術后惡心、嘔吐高危患者、手術時間短、近期心肌梗死、低射血分數、低血壓、哮喘病史、老年患者更適合行MAC。此外,應充分認識到麻醉醫師在圍手術期的作用。盡管MAC 更易發生呼吸暫停、低氧血癥,但麻醉醫師及時地處理或應用聲門上氣道等輔助通氣措施完全可保證患者通氣安全;GA 期間積極應用血管活性藥物也完全可將圍術期低血壓發生率降至和MAC 同一水平,圍手術期麻醉醫師的作用可消除兩種麻醉方式之間的絕大部分差異。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