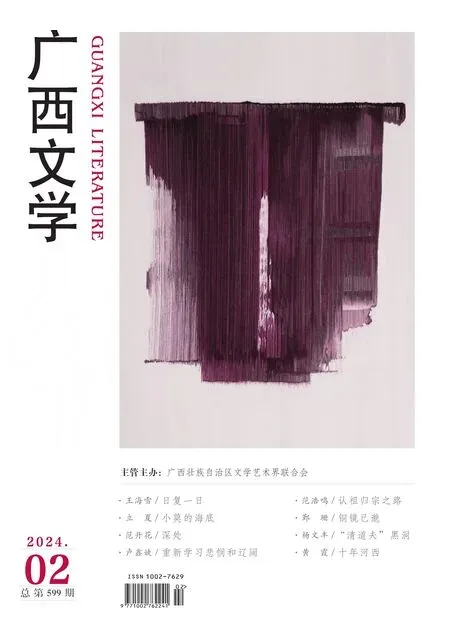傳薪草
吳克敬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于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yuǎn),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詩經(jīng)·抑》
編纂成冊的一部《大儒馬融》的文稿,磚塊般壘在我的書桌上有些日子了,我?guī)状紊焓值轿母迳希胍_來閱讀的,但有一雙無形的手,每次都會(huì)強(qiáng)橫地阻攔著我,不能把書桌上的文稿翻開來。
那雙無形的手,不會(huì)是別人的,一定是風(fēng)先生的呢。果不其然,他那似很蒼老,卻又顯得十分青春的聲音,倏忽在我的耳畔極具歷史意味地震響起來。他在朗誦《詩經(jīng)》里的那首名曰《抑》的歌謠: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xùn)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投我以桃,報(bào)之以李。彼童而角,實(shí)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于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jǐn)y之,言示之事。
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我聽得入迷,隨即請教風(fēng)先生想要知道這首歌謠傳達(dá)的意蘊(yùn)。風(fēng)先生沒有客氣,他先給我說了《毛詩序》的注解,意味此詩是用來諷刺周厲王的。他如此說來,卻并沒有茍同,又列舉一些后來的學(xué)者,闡發(fā)他的觀點(diǎn)。例如宋代的戴埴,在他的《鼠璞》里即說,“武公之自警在于髦年,去厲王之世幾九十載,謂詩為刺厲王,深所未曉”。再例如清代的閻若璩,又在他的《潛丘剳記》一文里說,“衛(wèi)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厲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詞,其人已逝,即當(dāng)杜口,是也;《序》云刺厲王,非也”。風(fēng)先生十分認(rèn)同后來人的看法,以為《抑》不可能是為了諷刺厲王。那么是為了什么呢?與后來的學(xué)者一般,不能認(rèn)同《毛詩序》觀點(diǎn)的風(fēng)先生,此時(shí)給我把《抑》誦念出來,不只是為了一種否定,而應(yīng)該還有他自己的理解呢。
我的猜測無錯(cuò),風(fēng)先生在把全詩誦念一畢,即把他新穎的見解說給了我。
風(fēng)先生言簡意賅,他說《抑》在“詩三百”中算是較長的一首,共十二章之多。其藝術(shù)手法選用了“賦、比、興”三種里的賦法,也就是直陳。詩歌直陳了一句古人的格言,“千慮一失,聰明人也會(huì)有失誤,因此聰明人也要謹(jǐn)慎小心。”極言“普通人的愚蠢,是他們天生的缺陷;而聰明人的愚蠢,則顯得違背常規(guī),令人不解”。因此到了后來,箴戒人們,王者要能夠向德為善,惠及下民;而普通百姓,則也應(yīng)該貞純有節(jié),報(bào)效民族。
風(fēng)先生化繁為簡的一段說辭,使我懵懂的心為之豁然開朗,隨口回答了風(fēng)先生一句話。
我說:一首古人做來的教化詩。
風(fēng)先生高興我的回答,他跟著我說:世間最美妙的事情,莫過于走進(jìn)你喜歡的那個(gè)人的心里,感受他的感受,體會(huì)他的體會(huì),真的理解他。
風(fēng)先生說:好了,你可以翻開《大儒馬融》的文稿,寫人家請求你的序言。
風(fēng)先生如此鼓勵(lì)我,而我卻似乎更加心慌意亂,但我沒有再遲疑,當(dāng)即在風(fēng)先生的鼓勵(lì)下,閱讀了書稿,來寫那序言了。我開篇沒繞彎子,即從漢人、漢字、漢文化上著筆,言說上秉周秦,下啟唐宋的大漢王朝,是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力和影響力最為活躍、國家權(quán)力和民族個(gè)性最為張揚(yáng)的一個(gè)時(shí)代。還說縱觀歷史,沒有哪個(gè)朝代能給中華民族留下如此深刻的印痕,大漢王朝輝煌而燦爛的文化,像熊熊不熄的火炬,一代一代薪火相傳,穿越千年,它巨大的成就和影響力,不僅在中國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上,都閃耀著無比輝煌的光芒!
我這么來說,雖然極端了點(diǎn),但誰又能否定呢?大概是不能的,甚或有我一樣的認(rèn)知。
風(fēng)先生就很認(rèn)同我的觀點(diǎn),他就說過,如果從時(shí)間的坐標(biāo)上看,大漢王朝分了西漢和東漢兩大板塊,雖然在漢武帝時(shí)董仲舒就明確提出了“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的政治主張,但西漢邊患頻仍,面對北方時(shí)刻覬覦中原,虎視眈眈的匈奴,朝廷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消除邊患,捍衛(wèi)民族生存權(quán)的戰(zhàn)爭中。漢民族經(jīng)過無數(shù)次的殘酷鏖戰(zhàn),終于敗匈奴于漠北,確保了漢民族的生存權(quán),也奠定了漢民族在中華民族中的軸心地位。所以人們看到的西漢,更多是“逐匈奴、通西域、定南蠻、服百越”,金戈鐵馬,開疆拓土,“犯強(qiáng)漢者,雖遠(yuǎn)必誅”的英雄主義時(shí)代。但正是西漢武功的強(qiáng)勢,為東漢時(shí)期在哲學(xué)、宗教、文學(xué)諸領(lǐng)域的大爆發(fā),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風(fēng)先生說來,我只有點(diǎn)頭了。西漢的確是個(gè)以“氣吞萬里如虎”而顯赫的武功時(shí)代,那么解除了邊患的東漢呢?則確實(shí)是漢文化蓬勃發(fā)展、繁榮昌盛的一個(gè)大時(shí)代。
西漢時(shí)期,萬流歸宗,在哲學(xué)思想方面,確立了以儒學(xué)為價(jià)值核心的思想體系。然而,在西漢以至東漢前期,由于秦始皇焚書、項(xiàng)羽火燒阿房宮,儒家經(jīng)典幾近不存,儒學(xué)的傳播沒有統(tǒng)一文本,都是依靠師授徒受,口口相傳,所以儒學(xué)界內(nèi)部門派林立,眾說紛紜,并無一個(gè)統(tǒng)一的格局。這樣一個(gè)時(shí)期,被統(tǒng)治階級認(rèn)定的儒學(xué)為后人稱為今文經(jīng)學(xué)。
今文經(jīng)學(xué)過度強(qiáng)調(diào)“君權(quán)神授”“天人感應(yīng)”,把世事的變化都依附歸結(jié)于自然界(天象)的變化而失之偏頗,把周密嚴(yán)謹(jǐn)?shù)娜鍖W(xué)引入了讖緯歧路。
由于西漢時(shí)期今文經(jīng)學(xué)被立為官學(xué),而此后在孔府墻壁和民間陸續(xù)發(fā)現(xiàn)部分儒學(xué)殘缺經(jīng)典,即給了學(xué)者們一次有條件管窺先秦前儒學(xué)經(jīng)典的機(jī)會(huì)。西漢末年的學(xué)者劉歆,在領(lǐng)校秘書時(shí)發(fā)現(xiàn),今文經(jīng)學(xué)不但在文字詞語上與古文經(jīng)學(xué)有異,而且每部儒學(xué)著作經(jīng)今文經(jīng)學(xué)學(xué)者的詮釋,在思想意識上也與先秦前儒家經(jīng)典相去甚遠(yuǎn),完全偏離了儒學(xué)經(jīng)典的原意。例如對孔子的評價(jià),兩者就大相徑庭。今文經(jīng)學(xué)家認(rèn)為孔子是受天命的素王,是讖緯神學(xué)中的黑帝之子的神祇,人神合一,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而古文經(jīng)學(xué)家就反對這種牽強(qiáng)附會(huì)的說法,他們把孔子請下神壇,還原為一個(gè)有血有肉的人。這截然不同的觀點(diǎn),如同水火不可調(diào)和,終于在東漢末年,儒學(xué)界爆發(fā)了今文經(jīng)學(xué)和古文經(jīng)學(xué)的大爭論。
風(fēng)先生的記憶里,就有賈逵、許慎、馬融、鄭玄、盧植等一大批著名的學(xué)者,以樸素的唯物主義認(rèn)識論,一方面批判今文經(jīng)學(xué)的謬妄,另一方面溯本追源,發(fā)掘儒家學(xué)說的真諦。這個(gè)今文經(jīng)學(xué)和古文經(jīng)學(xué)的爭論過程,以大儒馬融的學(xué)識而終結(jié),可以說馬融是今文經(jīng)學(xué)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古文經(jīng)學(xué)獲得回歸和發(fā)展的標(biāo)志性人物。
如此重要的一個(gè)人物,在風(fēng)先生的意識里一直靚麗著,然而在學(xué)術(shù)界,似乎不怎么被重視,顯得頗為冷落,除了“絳帳傳薪”這個(gè)典故外,人們對馬融知之甚少,甚至對他的評價(jià)還出現(xiàn)了爭議。風(fēng)先生對此自有主張,以為馬融是今文經(jīng)學(xué)的終結(jié)者,所以于當(dāng)時(shí)就遭到了部分心存芥蒂者的污蔑和攻擊,但馬融在經(jīng)學(xué)史上的杰出貢獻(xiàn)和嚴(yán)謹(jǐn)?shù)闹螌W(xué)態(tài)度,使得污蔑他的人無從下手,就轉(zhuǎn)而從個(gè)人生活瑣事上進(jìn)行污蔑,說他“器居奢靡,通經(jīng)而無節(jié)”。他們所謂的“節(jié)”,在風(fēng)先生看來就十分可笑了,不是節(jié)氣、節(jié)操、大義凜然的浩然正氣,而是在生活上刻意追求貧困的一種矯情,也就是說一種不健康的酸葡萄的心理。
對富足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們極為正當(dāng)?shù)南蛲oL(fēng)先生堅(jiān)持的就是這一觀點(diǎn),認(rèn)為這亦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更是推動(dòng)社會(huì)發(fā)展的動(dòng)力。所以對個(gè)人的評價(jià),應(yīng)該著眼于他對民族和歷史的貢獻(xiàn),對生活的態(tài)度和追求,不能成為臧否人物的理由。
風(fēng)先生贊賞馬融在東漢儒學(xué)發(fā)展的鼎盛時(shí)期,撥亂反正,獨(dú)樹一幟,博采眾長,遍注群經(jīng),使陷于神學(xué)泥淖的儒學(xué)革故鼎新,把以古文經(jīng)學(xué)為代表的儒學(xué)推向了更為成熟的階段,確立了以儒家學(xué)說為中心的一元化思想基礎(chǔ),對形成以漢族為主體的華夏民族共同體,功莫大焉。正如著名歷史學(xué)家侯外廬先生說的那樣,馬融“兩漢經(jīng)學(xué)結(jié)束的顯明表現(xiàn),就是今古經(jīng)學(xué)的合流,在這一點(diǎn)上,馬融恰是這一時(shí)代思想轉(zhuǎn)捩的體現(xiàn)者”。通經(jīng)博學(xué)、遍注儒家典籍的馬融,還著作了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等凡二十一篇。
讓風(fēng)先生念念不忘的是馬融著作的《忠經(jīng)》,他說為個(gè)人、為家庭、為皇帝而犧牲是私忠,以為那是小忠;而為民族、為大眾奉獻(xiàn)自己的是大忠,是忠誠、忠實(shí)、忠義、忠貞。這是難能可貴的,在他身處的時(shí)代,旗幟鮮明地說出這樣的觀點(diǎn),沒點(diǎn)兒赴死的勇氣,是做不出來的。
不僅如此,馬融在《忠經(jīng)》里還對冢臣肱骨、守宰官宦應(yīng)盡的忠道責(zé)任和推行忠道的方法進(jìn)行了全面的闡述,提出了“為官三惟”,即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牧民三要”,即篤之以仁義,導(dǎo)之以禮樂,宣君德明國法;“安民三策”,即安民、富民、愛民。這些政治主張和治國理念在今天看來,仍然具有鮮明的現(xiàn)實(shí)價(jià)值和指導(dǎo)意義。
這一切在風(fēng)先生看來,只是馬融文化貢獻(xiàn)的一小部分,而他最大的貢獻(xiàn),在于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了中國私學(xué)教育偉業(yè)。
馬融興辦私學(xué),其重要意義在于一方面溯本清源,批判今文經(jīng)學(xué)把儒學(xué)發(fā)展為讖緯神學(xué)的錯(cuò)誤做法,還儒學(xué)樸素唯物史觀的面貌,避免了儒學(xué)思想的僵化和消亡,使儒學(xué)如有源之水得以重生。更重要的意義是通過辦學(xué)培養(yǎng)了大量的儒學(xué)人才,如他的弟子鄭玄,因?yàn)槠湄暙I(xiàn),而被后人尊稱為“經(jīng)神”,他創(chuàng)立的學(xué)派亦被稱為“鄭學(xué)”,其后的追隨者一脈相承,不絕如縷,如隋朝的王通,唐代的顏師古、孔穎達(dá),宋代的朱熹、張載,元朝的程端禮,明朝的王守仁、李贄,清代的乾嘉學(xué)派等,都是極其著名的例子。
風(fēng)先生感動(dòng)于馬融興辦私學(xué)的一個(gè)特點(diǎn),就是以一己之力擔(dān)當(dāng)教化天下的重任,這在中國教育史上絕無僅有。大教育家孔子終其一生游說講學(xué),也只有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人,說到底還是“小眾教育”,沒有脫離舊式貴族教育的窠臼。馬融離卻東漢后期黑暗官場的羈絆后,雄心不已,不顧自己年老體衰,在家鄉(xiāng)扶風(fēng)筑高臺,設(shè)絳帳,面對廣大黎眾講經(jīng)布道,踐行他自己在《忠經(jīng)》里所說的“式敷大化,惠澤長久”的夙愿。
絳帳傳薪,即為后世對他教書育人的最高褒揚(yáng),也是他教育精髓的思想載體。然而風(fēng)先生搞不明白,馬融在懸掛著紅色帳幔的后邊,在給他的生徒講授學(xué)問時(shí),還要安排幾位絕色的女子,翩翩起舞,又有什么講究?或者能起什么作用?是為吸引生徒的注意力,還是為了考驗(yàn)他們讀書學(xué)習(xí)的定力?風(fēng)先生對此不能明白,后來的我,就更不能明白了。
在風(fēng)先生與我都不能明白馬融那一種作為的時(shí)候,“高臺教化”四個(gè)字驀然浮現(xiàn)在了我的意識里,我給風(fēng)先生講了呢。風(fēng)先生伸出手指,在我的額頭上戳了一下,很是快活地接受了我的說法。他說馬融的這一作為,與后來成型的戲曲演出異曲同工,可不就是為了教化民眾嗎!風(fēng)先生說得興起,還說“中國特色”應(yīng)該算上這一方法,對于傳播中國文化,使其深入人心,溶解進(jìn)人們的血液中,從而哺育和壯大中華民族的一切美德和智慧,產(chǎn)生了極其巨大的作用。
高談闊論著的風(fēng)先生,為了我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說教,還朗誦出一首北宋詩人韓駒所作的《題絳帳圖》詩:
豈有青云士,而居絳帳間。
諸生獨(dú)何事,不上會(huì)稽山。
五言絕句的一首小詩,我聽得出來,其所傳達(dá)出的意蘊(yùn)是非常深厚的哩。詩題中所說的“絳帳圖”,便是風(fēng)先生不說,我亦心中有數(shù),知曉其遺址就在今天的扶風(fēng)縣絳帳鎮(zhèn)……曾在扶風(fēng)縣文化館工作過的我,多次去到美好在我心中的“絳帳”,想要獲得馬融的青睞,讓我有所感知與覺悟。然而我去一次,失望一次。前些日子,我呼喚著風(fēng)先生,讓他帶我去到當(dāng)年石刻的“絳帳圖”故地,但依然還是失望。那處光耀歷史的故地,空空如也,除了生長得十分茂盛的玉米地,就還是玉米地。茫然若失的我,舉頭望天,而高遠(yuǎn)的天際漂浮著幾朵白云,游絲般沒有怎么理睬我,無趣的我低下頭來,抬腳踢在松軟的泥土上,踢出小小的一片土霧……善解人意的風(fēng)先生,看出了我心里的煩惱。
風(fēng)先生開導(dǎo)我說:一切固態(tài)的東西,都可能毀滅掉,如山可以崩塌,如水可能斷流,但精神性的物質(zhì),哪怕只是一頁紙上的記憶,水淹不朽,火焚不滅。
風(fēng)先生說:教化,馬融白紙黑字的教化,千秋萬代,輝映人間。
風(fēng)先生開導(dǎo)了我兩句話后,隨口又把一首七言古風(fēng)吟誦了出來:
風(fēng)流曠代夜傳經(jīng),坐擁紅妝隔夜屏。
歌吹彌今遺韻在,黃鸝啼罷酒初醒。
風(fēng)先生吟誦出的這首古風(fēng),我知道為清代扶風(fēng)知縣劉瀚芳所作。詩名也許就叫《絳帳》吧。我想就這個(gè)問題討教風(fēng)先生的,可我沒有討教出來,卻被風(fēng)先生用他掂在手上的粟秸稈敲打了一下。
這根粟秸稈是風(fēng)先生伴我走在玉米地時(shí)折下來的,我看得清楚,那不是玉米秤兒,而是一根我叫不出名稱的草秸稈,一段碧青,一段血紅。風(fēng)先生折來掂在手上,像是戲耍我似的,過一會(huì)兒,就往我的身上敲打一下。我被他敲打煩了,回頭睜眼瞪他,他樂著又還舉起那根草秸稈兒,往我的身上敲。他敲著我說了呢。說是馬融當(dāng)年坐在絳帳背后授徒講學(xué)時(shí),不只手捧書本,還會(huì)準(zhǔn)備一根這樣的草秸稈,放在手邊,哪個(gè)學(xué)生不老實(shí)聽講,甚或違反學(xué)規(guī),他即會(huì)手執(zhí)粟秸稈兒怒打之。有次他下手狠了點(diǎn),竟然打得草秸稈兒染上了血漬……馬融傷心染有血漬的草秸稈,就順手插在絳帳臺上,不承想幾天后,干枯的粟秸稈兒,居然生根發(fā)芽,開花結(jié)果,他的學(xué)生皆以為奇,就把這根秸稈叫作了“傳薪草”。
哦!好一個(gè)“傳薪草”,我從風(fēng)先生的手里接過來,一下一下,往自己的身上敲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