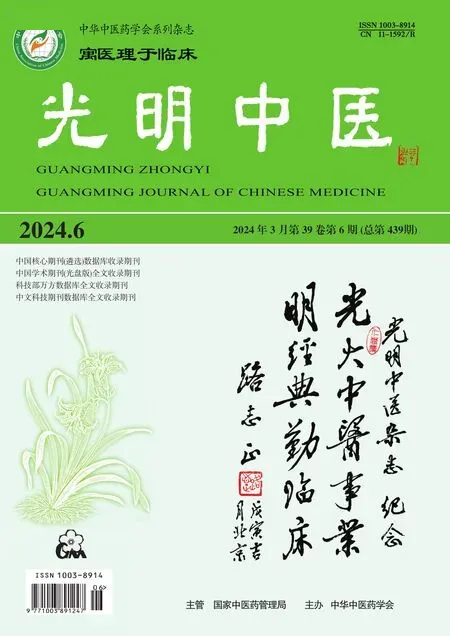基于《針灸大成》論心身疾病辨治探賾*
吳天明 席 強 李巖琪
心身疾病是在疾病發生、發展、康復過程中與社會心理因素緊密相關的一類疾病[1]。研究統計,幾乎80%的人群曾患有不同程度的心身疾病,遍布全身各器官系統、涉及臨床各科,嚴重影響了現代人的健康和生活[2]。西醫學認為,心身疾病有生物學、心理等病因,發病機制主要有神經生理機制、神經內分泌機制和免疫機制等[3],治療主要以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為主,能夠一定程度改善患者的情緒,但長期使用仍可導致一系列不良反應[4]。中醫治療心身疾病多基于古代情志致病理論,重視心理疏導,辨證遣方,用藥靈活多變[5]。針灸作為中醫特色療法之一,因在焦慮、抑郁、失眠、功能性消化不良等心身疾病的臨床治療上取得良好療效而得到廣泛應用[6]。
《針灸大成》由明代楊繼洲撰著,是針灸學術歷史上的第3次系統總結,后世醫家多有注解,具有圖文并重、重視臨證的特點。該書雖未提出心身疾病病名,但有頗多關于心身疾病的記載,驗證了七情致病學說的診療正確性與可行性[7]。本文擬對楊繼洲《針灸大成》中有關心身疾病的論述進行整理總結,以期對心身疾病的臨床選穴、學術研究提供文獻證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檢索方法以《針灸大成》[8]作為文獻檢索來源,手動檢索符合條件的心身疾病的論述、穴位治療和醫案。
1.2 納入標準①同時具有情志因素與功能性疾病的穴位主治條文,如“魚際……主心煩少氣,腹痛不下食”,情志因素包括喜、怒、憂、思、悲、恐、驚。②明確含有情志原因的疾病處方條文,如“煩心喜噫:少商 太溪 陷谷”。③提及社會、心理因素作為病因或誘因的醫案,如“己卯歲……近因下第抑郁,疾轉加增”案。
1.3 排除標準①僅含情志疾病未提及功能性改變的條文,如“喜笑:水溝 列缺 陽溪 大陵”。②普遍認為屬常見功能性疾病但原文未提及情志因素的條文,如“脹而胃痛:膈俞”。
1.4 數據規范化處理①原文未明確區分的穴位結合上下文、注解、所在經絡加以判斷,如“三里”為手三里或足三里;“通谷”為足通谷或腹通谷。②穴位名稱、歸經、特定穴的規范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經穴名稱與定位》[9]、《經外奇穴名稱與定位》[10]。
1.5 數據處理運用Microsoft Excel 2016建立數據庫,將符合條件的原文按條文編號、卷數、原文頁碼、穴位名稱、穴位歸經、穴位所在部位、特定穴屬性、刺灸方法錄入Excel軟件,并進行數據分析。
2 結果
2.1 腧穴歸經共檢索到涉及心身疾病的穴位87個,累計頻次140次。分析其歸經情況,經脈應用頻次最高的是足太陽膀胱經,共計20次,占總頻次的14.29%;其次為任脈,用穴頻次18次,占比12.86%;其后是足陽明胃經,用穴頻次16次,占比11.43%。見表1。

表1 《針灸大成》中涉身心疾病的穴位歸經分析
2.2 腧穴使用頻次選取87個穴位、140次頻次中使用頻率在3次及以上的穴位,頻次最高者為足三里(5.00%),其次為中脘(4.29%),其后為肺俞、大陵(3.57%)。見圖1。

圖1 《針灸大成》中涉及身心疾病的穴位使用頻次≥3次的穴位
2.3 腧穴所在部位將人體劃分為頭面部、頸項部、胸腹部、腰背部、脅肋部、四肢部6大部分,將穴位分布按照使用頻次進行統計,其中四肢部穴位使用頻次72次,占比51.43%;其次為胸腹部,共計26次,占比18.57%;其后為頭面部和腰背部,共計16次,占比11.43%。見表2。

表2 《針灸大成》中涉身心疾病的腧穴所在部位分析
2.4 特定穴屬性分析在所有穴位中,70個有特定穴屬性,占比80.46%;特定穴的使用頻次總計116次,占總頻次82.86%。70個特定穴中,章門、委中、足三里、陽陵泉、內關、列缺、公孫、關元、中脘、膻中、日月、期門、大陵、太淵、足臨泣、太溪、神門等17個穴位具有2種或2種以上特定穴屬性。將70個穴位按特定穴屬性分類,使用頻次最高的為五輸穴(包含井穴、滎穴、輸穴、經穴、合穴,共52次),其次為交會穴(35次),其后是募穴(16次)。見圖2。

圖2 《針灸大成》中涉及身心疾病的特定穴屬性分析
2.5 常用腧穴刺灸法對比《針灸大成》中有“治之在吾人也,有同異后先之辨”“既吞得氣,宜用補瀉”“灸不三分,是謂徒冤”之記載,體現楊氏對穴位的具體操作方法各有不同要點。對使用頻率在3次及以上的穴位進行統計,梳理其在《針灸大成》中關于針刺深度、留針時長和艾灸壯數的記載。見表3。

表3 《針灸大成》中涉及身心疾病的常用腧穴刺灸法分析
3 討論
3.1 取穴規律探析
3.1.1 取穴廣泛 量少質佳《針灸大成·頭不多灸策》云:“不得其要,雖取穴之多,亦無以濟人;茍得其要,則雖會通之簡,亦足以成功”。楊氏在臨床治療心身疾病時取穴廣泛,除手太陽小腸經未使用外,其余十三經脈、經外奇穴均有涉及,并且穴位涉及全身部位。可見,雖心身疾病包含種類眾多,但楊氏在治療時,可以根據疾病廣泛取穴,如同為怒氣致病,口眼斜需選用頰車、合谷、地倉等;心胸疼痛需選用大陵、內關、曲澤等;咳逆發噫需選用膻中、中脘、大陵等。楊氏單列“經外奇穴”1篇,與“穴有奇正策”互參,在心身疾病的大范圍內,結合具體病證,給出最佳的穴位治療,穴簡力專。
3.1.2 重用特定穴楊氏在治療具有心身共病表現的疾患時,特定穴占選穴總數的80.46%。特定穴主治規律強、應用范圍廣,重用特定穴對于治療常見心身疾病意義重大,如《針灸大成·心脾胃門》治療虛煩口干,獨取肺俞,因背俞穴具有治療相應臟腑、五官九竅、皮肉筋骨的作用。現代研究也證明了特定穴的療效,鮮琦琦等[11]收集近20年針刺治療單純性肥胖的145篇臨床文獻,認為單純性肥胖人群主要證型為肝郁氣滯,治療應以特定穴為主,再按證型配穴。本研究發現,《針灸大成》最常使用的特定穴為足三里,李雪梅等[12]基于窮舉法探討合募配穴法治療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的最佳選穴方案,得出兩穴方案為足三里配天樞;三穴方案為足三里、上巨虛配天樞。由此可知,臨床上特定穴的使用是提升治療效果的優質選擇。
3.1.3 多種配穴方法靈活應用研究表明,《針灸大成》主要運用本經配穴+雙特配穴、五輸穴+五輸穴、合穴+合穴等配穴方法[13]。在治療心身疾病時,《針灸大成》也有相關記載,如“或因他事所關,氣攻兩脅疼痛”所致挫閃腰脅痛,選用尺澤、委中、人中,即上下配穴法;治療煩悶不臥時選取太淵與公孫,是同名經配穴法的體現。多種配穴方法的運用,可以加強腧穴之間的協同作用,對于全身性心身障礙表現能顯著提高治療效果。臨床上不同醫家多有發揮,如符文彬教授善用四花穴、四關穴等陰陽調和組穴,療效顯著[14]。有學者運用靜息態功能磁共振掃描技術,認為遠部配穴針刺治療月經性偏頭痛,可能是通過枕葉和楔前葉達到對患者腦功能活動的調節[15],為配穴的臨床療效提供了現代研究依據。
3.2 辨治規律探析
3.2.1 審查病因 辨證論治《針灸大成·針有淺深策》言:“夫曰先曰后者,而所中有榮有衛之殊;曰寒曰熱者,而所感有陽經陰經之異”。強調針灸治療務必辨清榮衛之分、陰陽之別。楊氏醫案中,記有“辛未,武選王會泉公亞夫人患危異之疾”案,楊氏認為“考其為病之詳,變化多端”,系統分析怒、喜、悲、恐、驚、勞、思等所致病證的特點后,認為需“以五行相勝之理,互相為治”,最終“目即開,而即能食米飲”。楊氏對九氣、十多為主的情志致病理論有所發揮[16],告誡后人對疑難雜癥的病因分析應當慎重,不同的情志致病因素需靈活準確地辨證論治。
3.2.2 病涉多臟 整體治療楊氏在《針灸大成·通玄指要賦》注解中告誡后人“知行氣所在,經絡左右所起,血氣所行,逆順所會”,才能“除疼痛于目前,療疾病于指下”。當精神因素涉及多個臟腑功能性病變時,臨床應從臟腑整體觀、形神一體觀進行辨治。如《針灸大成·心脾胃門》治療煩悶不臥選用太淵、公孫、隱白、肺俞、陰陵泉、三陰交,內含手太陰肺經、足太陰脾經、足太陽膀胱經穴位,手足、陰陽經并用,形神合一。臨床上,孫建華教授基于心身醫學視角治療功能性胃腸病,認為其病位在腦、脾及腸腑,發病關鍵在于心、腦、神失調,治療尤重調神[17],與《針灸大成》觀點吻合。
3.2.3 針藥并用 善用灸法《針灸大成·諸家得失策》云:“疾在腸胃,非藥餌不能以濟;在血脈,非針刺不能以及;在腠理,非熨焫不能以達”,充分體現楊氏針、灸、藥并用之臨床診療思想。本次研究中,通過對心身類疾患的治療分析可知,除心俞的記載之一提及“不可灸”外,其余11個使用頻率在3次及以上的穴位,均可使用灸法,甚至出現“灸五百壯,少亦一、二百壯”等描述,體現楊氏對灸法的重視。在楊氏醫案中,也有“治婦人喪妹甚悲,而不飲食,令以親家之女陪歡,仍用解郁之藥,即能飲食”的記載,體現傳統中藥、心理疏導在治療心身疾病時同樣具有重要地位。
4 結語
心身醫學是近年來新生的一門醫學學科,目前各項研究主要以改善臨床癥狀為主,但總的來看,對于心身疾病的病因病機、發病機制仍不明確,臨床治療難以直接做到藥到病除。針灸等非藥物療法是中醫獨特優勢。《針灸大成》是代表楊繼洲思想的重要學術著作,通過梳理條文得知,楊氏治療心身疾病時,取穴廣泛,量少質佳,重用特定穴,多種配穴方法靈活應用,強調辨證論治,整體治療,善用灸法。當代醫家應在前人的基礎上積極結合現代醫學成果,以古鑒今,形成更加完善的防治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