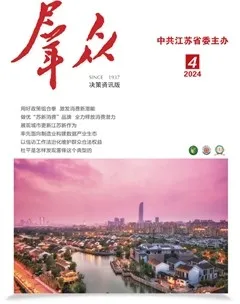探尋費城的歷史印記
曹俊
費城是美國第五大城市,也是美國最古老、最具歷史意義的城市之一。不論是前來旅行還是居住一段時間,都能夠從不同的側面感受費城這座城市的歷史底蘊。城市的歷史印記怎樣沉淀,又如何呈現給大眾?在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如何與都會空間及產業協同前行、交相輝映?這對于歷史名城的發展建設是關鍵問題,對于當代城市的結構拓展及更新演進也是重要命題。在費城研修的一年,我試圖從一個觀察者的視角切入,探尋當下費城的歷史印記,思考其對我國城鎮化建設的借鑒意義。
費城是一座有“原點”的城市。矗立在費城市中心的標志性歷史建筑是市政廳,經市政廳大樓所在的中央廣場軸向展出麥凱特大街和布魯德大街作為兩大干道,這從根本上奠定了費城城市的“十字骨架”。這一十字骨架既串聯了費城的歷史,又集聚了當代的都市功能,是歷史結構與都市結構的高度嵌合。作為原點的市政廳高約167米,建成于1901年,是當時世界第一高樓,時至今日也是美國最大的市政建筑。伴隨著以金融業為代表的現代服務業的迅速崛起,圍繞市政廳所在的中心商務區已經建起了大量的摩天樓。相對于周邊建筑,市政廳雖然在絕對高度上已然顯得“矮小”,但是因為其位于城市十字軸線的幾何中心,軸線兩側鱗次櫛比的建筑群都在引導視覺朝向中心,市政廳在“巨人”的映襯下也顯得愈發“高大”了。建成于1933年的三十街車站是美鐵系統第三繁忙的車站,東西方向的麥凱特大街軸線橫跨斯庫爾基爾河,不僅直接連接了兩岸的三十街車站與CBD建筑群,同時向西拓展串聯起歷史悠久的大學城組團,向東串聯起國家獨立歷史公園。布魯德大街作為南北方向的軸線,則連接了北部的天普大學組團以及南部的大型體育中心組團。循著軸線方向前行,仿佛剖開城市的時代斷面,展開的是一個接一個見證費城不同時期發展的標志建筑群落。
立足于市政廳的中心點,向西北方向還放射延伸出另一條特色軸線——本杰明·富蘭克林大街。軸線的另一端是全美第三大美術館費城藝術博物館,博物館不僅正立面對景市政廳,同時進入博物館前廣場需通過“洛基之路”多層大臺階的空間序列才能到達。在天氣晴朗的節假日,洛基之路本身就成為一個喜聞樂見的休憩場所——市民、游客三五成群地坐在大臺階上,視線透過近處的華盛頓雕塑噴泉,沿著富蘭克林大街的軸線,望向市政廳及遠方的城市天際線,這也成為費城的明信片景觀。在這條雖然不長但風景秀麗的林蔭大道上,布局有羅丹博物館、本杰明·富蘭克林紀念館和菲斯天文館等一系列重要文化設施,將城市的文化產業以低伏、緊湊的方式呈現出來。在襯托特色軸線空間的同時,也成為感受城市文化與藝術氣息的必由路徑。
市政廳向東約一公里的國家獨立歷史公園是歷史遺址集中分布的場域。宣布《獨立宣言》的獨立宮、國會廳、老市政廳并列在歷史公園的南部。公園東側分布著基督堂公墓、富蘭克林墓。公園西側則是通過一長條相對簡約的現代建筑群承擔游客中心的功能,在靠近獨立宮處陳列著具有國家象征意義的自由鐘,并通過局部透明的建筑界面使得自由鐘能夠被公園外部空間的人群直接感知到。北側與獨立宮正對呼應的是國家憲法中心,也構成了歷史公園南北向軸線的兩端。國家獨立歷史公園不僅在其四周薈萃了各個時代的歷史建筑群及遺址群,更為有趣的是,該公園本身就是在1730年建立的獨立廣場的基礎上向北擴建形成,層層疊疊的歷史在此交匯、共存、嵌套,讓前來參觀的游客于歷時性中感受城市深厚的歷史底蘊。
如果說軸線是以一種剛性的力量塑造了城市的結構框架,那么夾在西岸和東岸之間的斯庫爾基爾河無疑通過另一種柔性的力量與之互補。在蜿蜒曲折的河道沿岸,串聯了大大小小的綠地游憩節點——有像費爾芒特公園這樣橫跨兩岸的超大型綠地,其中包含1875年美國獨立100周年紀念會場舊址、1876年費城世博會舊址、費城動物園、競技體育場等復合型要素,公園的西區和東區之間通過跨河的步行橋連接;也有像藝術博物館北部公園、伍德蘭德公園等相對尺度較小的團塊狀的公園綠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從春園街至南街附近的濱河段設置有連續的線性濱河綠地,在局部沿河段落,城市原有的廢棄鐵軌也被作為印記保存下來、并轉化融合為濱河的線性步行道,為城市中的各類人群提供騎行、慢跑、徜徉漫步的游憩場所。從更為宏觀的視角看,斯庫爾基爾河沿岸的綠地公共空間并不是封閉的,而是與城市內部的綠地斑塊連接在一起形成網絡。典型的如賓大公園,一端通過沃爾納特天橋連向濱河西岸,另一端則向城區內部滲透,與史密斯步行道、伍德蘭德步行道、洛塔斯步行道、蘭卡斯特步行道等編織成一張綠色大網,同時,構筑了大學城區域富有特色的公共空間慢行體系。在東岸的思故河公園,經由洛卡斯特街步行3分鐘即可到達歷史悠久的里滕豪斯廣場,這個廣場也曾被著名城市社會學家簡·雅各布斯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評價為功能復合的宜人場所。
費城的歷史印記既有外顯、張揚的一面,也有相對內隱、低調的一面。例如,在三街和四街之間的看似尋常的城市街區中,富蘭克林博物館就“藏”在其中。從街道外部經過,其門頭近似于一戶普通的聯排住宅,通過極窄的巷道進入內部方別有洞天,在庭院中用構筑物行架勾勒出已經不復存在的舊址的建筑輪廓。再例如,在市中心一幢看似停用的車站建筑被保留了下來,并改造成為集市建筑——瑞汀車站市場。走進車站市場,在一個巨大的穹頂下聚集了當地最具特色的小吃美食及零售商品業態,成為游客網紅打卡地。主體位于十街的中國城片區并沒有商場、綜合體等大型的建筑,在城市中并不彰顯;連片統一的建筑肌理及商招風格,加之主街上“費城華埠”牌坊和北側具有歷史感的圍墻,使得其成為一片獨具特色的區域。
費城的歷史印記不僅鐫刻在城市中,更是烙印在大學里。費城市內共有賓夕法尼亞大學、德雷塞爾大學、天普大學等近二十所大學及學院。大學的建設史本身也是城市歷史印記的一部分。以賓夕法尼亞大學為例,其最初由本杰明·富蘭克林創建于1740年,是美國第一所從事科學技術和人文教育的現代高等學校。在校園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哥特式風格校園建筑群,如主廳、藝術圖書館、禮堂、考古與人類學博物館等,該風格的建筑是在融合了英國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建筑風格的基礎上創新發展而來。除了古典風格的哥特式建筑外,校園內還有很多現代建筑,如主圖書館、設計學院樓、商學院樓。難能可貴的是,在近三百年的校園建設中,不同時期的建筑之間并沒有因為風格和樣式的區別而顯得格格不入,相反,經歷近三百年的沉淀,古典與現代建筑有機融合在大學城整體的建成環境中。
歷史印記,不僅指代狹義的文物古跡本體,在更大的視域下更指代城市整體的歷史呈現。在費城生活近一年,既是專業研修的一年,也是全面認知和感受這座城市的一年。于我而言,費城的歷史底蘊是“多面的”——既有一鏡到底的大軸線,也有藍綠交織的公共空間網絡,既有寫在面子上的歷史,也有藏在里子中的歷史,它們剛柔并濟、顯隱互現,等待人們探尋。
(作者單位:東南大學建筑學院)
責任編輯:包詠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