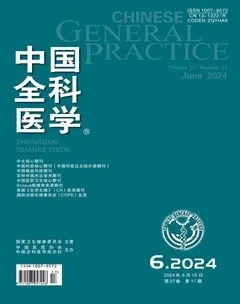生物制劑和小分子藥物治療潰瘍性結腸炎有效性與安全性的網狀Meta 分析
譚書法,張磊昌,高強強,歐艷,黃水蘭
1.712046 陜西省咸陽市,陜西中醫藥大學
2.330000 江西省南昌市,江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肛腸科
3.712046 陜西省咸陽市,陜西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潰瘍性結腸炎(UC)是一種特發性免疫介導的慢性炎癥性腸道疾病,主要累及結腸和直腸,以結直腸黏膜和黏膜下層連續性、彌漫性炎癥改變為特征[1]。隨著生活習慣的改變,UC 的全球發病率呈現顯著上升趨勢。其臨床主要癥狀表現為腹瀉、直腸急迫、二便失禁、黏液膿血便以及腹部不適,其他臨床癥狀包括體質量減輕、貧血、發熱等腸外表現,多呈現反復發作的慢性病程[2-3],長期不受控制的炎癥反應極大增加了結直腸癌的風險[4]。盡管UC 不會帶來顯著的死亡率變化,但卻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量,慢性長期的治療給患者帶來了極大的經濟負擔[5]。5-氨基水楊酸(5-ASAs)常用于輕、中度UC,對于更嚴重的UC 常采用皮質類固醇進行治療,但存在潛在的不良反應以及治療效果不佳、較高復發率等缺點[6-7]。在過去的20 年,基于全基因組關聯研究中確定的疾病機制,開發出了具有更精確作用模式的新藥用于治療UC,抗腫瘤壞死因子生物制劑(Etrolizumab、Vedolizumab、Golimumab、Infliximab、Adalimumab),其在提高黏膜愈合、深度緩解和無皮質類固醇緩解率方面實現了更好的疾病控制,并提高了患者生活質量,然而,這些選擇性更強的藥物也不是對所有患者有效,其使用可能存在包括有限的療效、原發性無反應、繼發性反應喪失等局限性[8]。有相當比例的患者對抗腫瘤壞死因子(TNF)藥物無反應,存在不良反應或隨著時間的推移失去反應。自2014 年以來,越來越多的藥物選擇(JAK 抑制劑Tofacitinib、Filgotinib、Upadacitinib)變得可用,已在歐盟和英國被批準用于治療中度至重度活動性UC 的成年患者。這是一個快速發展的領域,一些新藥在Ⅲ期臨床試驗中已顯示出療效,但既往的一些網絡薈萃分析卻并未考慮這些藥物,并且國內還沒有研究對此進行薈萃分析。傳統的Meta 分析不能得到直接比較治療療效的結論,網狀Meta 可用于評估3 種或3 種以上干預措施的相對影響,并允許對干預措施進行排序和等級比較。因此,隨著UC 先進療法數量的增加,本研究運用網狀Meta 分析臨床最佳用藥,旨在為臨床醫生治療決策提供循證醫學證據。
1 資料與方法
1.1 檢索策略
2 名研究人員獨立使用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Cochrane Library、中國知網、萬方數據知識服務平臺、維普網數據庫進行搜索,中文關鍵詞包括潰瘍性結腸炎、生物制劑、JAK 抑制劑、烏帕替尼、托法替尼、維多珠單抗、依曲利組單抗、戈利木單抗、英利昔單抗、阿達木單抗;英文關鍵詞包括UC、ulcerative colitis、Filgotinib、Biologics、Upadacitinib、Tofacitinib、Etrolizumab、Vedolizumab、Golimumab、Infliximab、Adalimumab。檢索字段包括主題詞、題目和摘要,搜索策略沒有語言或時間限制。檢索策略為:((UC)OR(ulcerative colitis))AND((((((((((Filgotinib)OR(Biologics))OR(Upadacitinib))OR(Tofacitinib))OR(Etrolizumab))OR(Vedolizumab))OR(Golimumab))OR(Infliximab))OR(Adalimumab))OR(JAK)),檢索的時間范圍為2010-01-01—2023-09-15。Meta 分析按照系統評價和薈萃分析首選報告項目(PRISMA)指南進行[9]。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1)研究對象為臨床確診為中、重度UC 患者(診斷標準為:梅奧臨床評分為6~12 分,梅奧內鏡評分≥2分);(2)研究類型為隨機對照試驗(RCT),試驗組為生物制劑或小分子藥物,對照組為安慰劑;(3)研究對象包括不同藥物的干預;(4)中英文文獻。排除標準:(1)數據有缺失則不能用于統計分析;(2)重復發表;(3)體外實驗、動物實驗、非比較研究、綜述、信件、指南、病例報告等。
1.3 文獻篩選及數據提取
將檢索所得文獻信息導入文獻管理軟件EndNote,所有標題和選定的摘要由2 位作者審閱,重復的研究和不相關的文獻被排除在外,并在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做出納入或排除研究的最終決定,獨立提取相關文獻信息、研究目標、結果和隨訪數據,使用標準數據提取表獨立提取信息,2 名研究人員逐一交叉核對,分歧通過討論解決。對于每項研究收集以下信息:(1)研究特征:第一作者、國家、發表年份、研究類型、試驗方案;(2)患者基線:干預方式、患者例數、年齡、性別、疾病持續時間;(3)研究結果:主要結局指標為臨床緩解、臨床反應、內鏡緩解、黏膜愈合,次要結局指標為不良事件。臨床緩解定義為Mayo 總分為2 分或更低,個體亞評分為1 分或更低,直腸出血亞評分為0 分;臨床反應定義為Mayo 總分下降≥3 分,較基線下降30%,直腸出血亞評分下降≥1 分或絕對直腸出血評分為0 分或1 分;內鏡緩解定義為Mayo 內鏡亞評分為0 分。
1.4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評價
2 名研究員嚴格依照Cochrane 偏倚風險評估工具對納入文獻進行偏倚風險評估,并使用RevMan 5.4 進行分析。包括隨機分配、分配隱藏、受試者及實施者盲法干預、結果盲法評價、結果數據完整性、選擇報告研究結果、其他偏倚7 個條目。每個條目按“低風險”“風險未知”“高風險”進行偏倚風險評估,若兩者評估相差較大或影響研究入選最終分析,請教第三位專家解決。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R Studio 調用gemtc 軟件包,建立貝葉斯模型進行網狀Meta 分析,繪制概率圖并進行概率排序。計算二分類變量的相對風險(RR)和95%置信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CI),計算連續變量的標準平均差(WMD)和95%CI。當各干預措施間形成閉環時,需進行不一致性檢驗,用于評估直接比較和間接比較結果的一致程度,采用節點分析法進行不一致性檢驗,若P>0.05 則表示無差異。通過計算每種方法的累積排序概率圖下面積(SUCRA)值來估計治療的總體排名,根據SUCRA 值的大小進行干預措施優劣的排序。
2 結果
2.1 文獻篩選流程圖
本研究共檢索1 867 篇文獻,最終納入25 項RCT[10-34]。文獻篩選流程及結果見圖1。

圖1 文獻檢索流程圖Figure 1 Literature screening process
2.2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
本研究納入文獻共涉及9 546 例患者,包括10 種藥物干預方案(Filgotinib 100 mg、Filgotinib 200 mg、Upadacitinib、Tofacitinib、Etrolizumab、Adalimumab、Vedolizumab、Golimumab 50 mg、Golimumab 100 mg、Infliximab)。納入研究的研究特征、患者基線、研究結果見表1。

表1 納入研究的基本特征Table 1Basic information of included RCTs
2.3 納入研究的質量評價
使用Cochrane 偏倚風險工具對25 項研究進行評估。14 項研究[10-13,15,18-20,23,26,28,31-32,34]報道了具體的隨機序列產生方法,評為“低風險”,其余11 項研究[14,16-17,21-22,24-25,27,29-30,33]均提及了隨機但未說明具體方法,評為“風險未知”。25 項研究均提及盲法,但均未對分配隱藏以及結果評價實施盲法相關內容予以描述,評為“風險未知”。25 項研究均報道了預期測量的結局指標,評為“低風險”。25 項研究均未詳細描述其他偏倚,評為“ 低風險”。文獻質量評價結果見圖2。

圖2 納入研究的偏倚風險Figure 2 Bias risk assessment results of included RCTs
2.4 網狀Meta 分析
結局指標的證據網絡、一致性檢驗及收斂性評價各結局指標構建模型的收斂性較好,規模縮減因子(PSRF)均接近1;網絡關系總體以Placebo 為中心,圓點代表該干預措施,以一線連接兩點代表存在直接比較,線的粗細代表納入研究的數量。
2.4.1 臨床緩解
2.4.1.1 網狀證據圖:20 項研究[10-15,17-22,25-26,28-31,33-34]報道了臨床緩解,涉及11 種干預方案(A:Placebo、B:Filgotinib 100 mg、C:Filgotinib 200 mg、D:Upadacitinib、H:Tofacitinib、I:Etrolizumab、J:Adalimumab、K:Vedolizumab、L:Golimumab 50 mg、M:Golimumab 100 mg、N:Infliximab)。網絡關系見圖3,閉合環的節點分析結果顯示,直接比較與間接比較的結果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圖3 臨床緩解率的網絡證據圖Figure 3 Network diagram for clinical remission rates
2.4.1.2 網狀Meta 分析:網狀Meta 分析產生了55 項兩兩對比,結果顯示Upadacitinib 的臨床緩解率展現出最佳效用,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不同干預措施對UC 臨床緩解率比較的網狀Meta 分析結果[logOR(95%CI)]Table 2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remission rat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vention regimens
2.4.1.3 SUCRA 排 序:SUCRA 概 率 排 序 顯 示Upadacitinib(94.1%)>Vedolizumab(85.1%)>Tofacitinib(74.3%)>Infliximab(72.7%)>Filgotinib 200 mg(51.5%)>Golimumab 100 mg(44.3%)>Golimumab 50 mg(39.3%)>Etrolizumab(38.9%)>Adalimumab(29.8%)>Filgotinib 100 mg(18.7%)>Placebo(0.7%),概率越大說明對UC 臨床緩解效果越好。
2.4.2 臨床反應
2.4.2.1 網狀證據圖:14 項RCT[14-15,17,19-23,25-26,30-31,33-34]報道了臨床反應,涉及9 種干預方案(A:Placebo、D:Upadacitinib、H:Tofacitinib、I:Etrolizumab、J:Adalimumab、K:Vedolizumab、L:Golimumab 50 mg、M:Golimumab 100 mg、N:Infliximab)。網絡關系見圖4,各干預措施之間無閉合環,因此無須一致性檢驗,各措施之間連接線條的粗細代表使用該兩點治療措施的RCT 數量。

圖4 臨床反應的網絡證據圖Figure 4 Network diagram for clinical response
2.4.2.2 網狀Meta 分析:網狀Meta 分析產生了36 項兩兩對比,結果顯示Upadacitinib 的臨床反應展現出最佳效用,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不同干預措施對UC 臨床反應比較的網狀Meta 分析結果[logOR(95%CI)]Table 3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the clinical response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vention regimens
2.4.2.3 SUCRA 排 序:SUCRA 概 率 排 序 顯 示Upadacitinib(98.4%)>Infliximab(84.4%)>Tofacitinib(67.2%)>Vedolizumab(58.4%)>Golimumab 50 mg(53.3%)>Adalimumab(34.6%)>Golimumab 100 mg(30.1%)>Placebo(0.4%),干預措施概率越大說明對UC 臨床反應效果越好。
2.4.3 內鏡緩解
2.4.3.1 網狀證據圖:6 項RCT[10-12,14,17,19]報道了內鏡緩解,涉及8 種干預方案(A:Placebo、B:Filgotinib 100 mg、C:Filgotinib 200 mg、D:Upadacitinib、H:Tofacitinib、I:Etrolizumab、J:Adalimumab、K:Vedolizumab)。網絡關系見圖5,各干預措施之間無閉合環,因此無須一致性檢驗。

圖5 內鏡緩解的網絡證據圖Figure 5 Network diagram for endoscopic remission
2.4.3.2 網狀Meta 分析:網狀Meta 分析結果顯示產生了28 項兩兩對比,結果顯示Upadacitinib 的內鏡緩解展現出最佳效用,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2.4.3.3 SUCRA 排 序:SUCRA 概 率 排 序 顯 示Upadacitinib(98.7%)>Tofacitinib(68.6%)>Filgotinib 200 mg(59.6%)>Adalimumab(55.2%)>Etrolizumab(46.0%)>Vedolizumab(45.9%)>Filgotinib 100 mg(23.4%)>Placebo(2.2%),概率越大說明對UC 內鏡緩解效果越好。

表4 不同干預措施對UC 內鏡緩解比較的網狀Meta 分析結果[logOR(95%CI)]Table 4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the endoscopic remiss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vention regimens
2.4.4 黏膜愈合
2.4.4.1 網狀證據圖:9 項RCT[14,17,21,24,26-27,30-31,33]報道了黏膜愈合,涉及8 種干預方案(A:Placebo、D:Upadacitinib、H:Tofacitinib、I:Etrolizumab、K:Vedolizumab、L:Golimumab 50 mg、M:Golimumab 100 mg、N:Infliximab),網絡關系見圖6,各干預措施之間無閉合環,因此無須一致性檢驗。

圖6 黏膜愈合的網絡證據圖Figure 6 Network diagram for mucosal healing
2.4.4.2 網狀Meta 分析:網狀Meta 分析結果顯示產生了28 項兩兩對比,結果顯示Upadacitinib 的黏膜愈合展現出最佳效用,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不同干預措施對UC 黏膜愈合比較的網狀Meta 分析結果[logOR(95%CI)]Table 5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the mucosal healing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vention regimens
2.4.4.3 SUCRA 排 序:SUCRA 概 率 排 序 顯 示Upadacitinib(99.7%)>Tofacitinib(77.2%)>Infliximab(65.2%)>Golimumab 50 mg(46.4%)>Vedolizumab(44.4%)>Adalimumab(33.8%)>Golimumab 100 mg(31.9%)>Placebo(1.0%),概率越大說明對UC 黏膜愈合效果越好。
2.4.5 不良事件
2.4.5.1 網狀證據圖:17 項RCT[10,14-17,19-22,24-30,32]報道了不良事件,涉及11 種干預方案(A:Placebo、B:Filgotinib 100 mg、C:Filgotinib 200 mg、D:Upadacitinib、H:Tofacitinib、I:Etrolizumab、J:Adalimumab、K:Vedolizumab、L:Golimumab 50 mg、M:Golimumab 100 mg、N:Infliximab)。網絡關系見圖7,各干預措施之間無閉合環,因此無須一致性檢驗。

圖7 不良事件的網絡證據圖Figure 7 Network diagram for adverse events
2.4.5.2 網狀Meta 分析:網狀Meta 分析結果顯示產生了55 項兩兩對比,結果顯示Filgotinib 100 mg 安全性最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6。

表6 不同干預措施對UC 不良事件比較的網狀Meta 分析結果[logOR(95%CI)]Table 6 Network meta-analysis of the adverse even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vention regimens
2.4.5.3 SUCRA 排序:SUCRA 概率排序顯示Golimumab 100 mg(96.7%)>Golimumab 50 mg(92.1%)>Placebo(68.7%)>Tofacitinib(60.8%)>Adalimumab(60.7%)>Etrolizumab(47.2%)>Upadacitinib(42.2%)>Vedolizumab(41.3%)>Infliximab(27.0%)>Filgotinib 200 mg(6.6%)>Filgotinib 100 mg(6.2%),概率越大說明治療后不良事件風險越高。
3 討論
UC 的發病機制包括免疫、遺傳、環境和微生物因素,臨床上常規的治療方式包括氨基水楊酸類、糖皮質激素、抗菌藥、中醫藥灌腸以及外科手術治療[35]。5-ASAs 被證實對輕中度UC 患者有效,糖皮質激素類藥物常被用于更為嚴重的階段,然而,這些藥物存在嚴重不良反應[7]。近年來基于全基因組關聯研究而確定的疾病機制開發出了包括生物制劑、小分子藥物JAK 抑制劑等作用模式更精確的新藥物治療[36]。為探索這些新興治療方式的臨床效果,本研究系統回顧了生物制劑(Vedolizumab、Golimumab、Infliximab、Adalimumab)、小分子藥物(Filgotinib、Upadacitinib、Tofacitinib)在成年UC 患者誘導過程中的RCT,并進行了網絡薈萃分析。
根據網狀Meta 分析結果顯示,除不良事件外,所有藥物的臨床療效優于安慰劑,臨床反應方面排名第一的藥物為Upadacitinib,其次為Infliximab;臨床緩解方面排名第一的藥物為Upadacitinib,其次為Vedolizumab;內鏡緩解方面排名第一的藥物為Upadacitinib,其次為Tofacitinib;黏膜愈合方面排名第一的藥物為Upadacitinib,其次為Tofacitinib;不良事件發生方面風險排名第一的藥物為Golimumab 100 mg,其次為Golimumab 50 mg。JAK 抑制劑是一種非受體型的酪氨酸激酶,包括JAK1、JAK2、JAK3 和TYK2[37],可阻斷一種或多種細胞內酪氨酸激酶,JAK 信號轉導器和轉錄通路激活因子與UC 的發病機制有關,其通過與細胞因子配體結合發生磷酸化,進而激活信號轉導器和轉錄激活因子(STAT),JAK-STAT 信號通路控制先天和適應性免疫、造血和細胞過程的許多功能,包括細胞增殖、分化、凋亡和遷移[38-39]。已有研究證明,JAK-STAT 可以抑制T 細胞過度活化以及浸潤調控炎癥反應進而促進腸黏膜愈合[40]。Upadacitinib是一種新型選擇性JAK1 抑制劑,對JAK1 的選擇性是JAK2 的60 倍,是JAK3 選擇性的100 倍,t1/2為6~16 h[41]。GHOSH 等[42]的一項研究表明Upadacitinib可以顯著緩解UC 患者普遍存在的急腸癥、腹痛和身體負擔。在接受Upadacitinib 治療后,糞便鈣保護蛋白和高敏C 反應蛋白也相應下降。PANéS 等[43]的一項評估Upadacitinib 在改善患者生活質量的研究中顯示,在中度至重度活動性UC 患者誘導第2 周的各種健康相關生命質量(HRQoL)評估中(胃腸道癥狀如排便急促或頻繁以及腹痛和非胃腸道癥狀如關節痛、疲勞和睡眠困難、身心功能、工作效率和日常活動的表現),相比于安慰劑和Upadacitinib 30 mg,Upadacitinib 45 mg 在誘導治療改善生活質量方面取得了更為顯著的臨床意義。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是一種主要由單核-巨噬細胞和T 細胞產生的炎癥細胞因子,研究發現,UC 患者的結腸、血液和糞便中發現TNF-α 水平顯著升高,提示腸道存在炎癥反應[44],英夫利昔單抗、阿達木單抗和Golimumab 是抗TNF-α 抗體,通過阻斷促炎因子緩解UC[45]。Vedolizumab 是一種人源化單克隆抗體和抗整合素抗體,可協助淋巴細胞從血管系統向炎性組織遷移,其主要作用機制是通過抑制α4β7 整合素與MAdCAM-1 腸道特異性黏膜從而特異性拮抗α4β7 整合素調節炎癥發揮治療作用[46-47]。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小分子激酶抑制劑Filgotinib、Tofacitinib 在誘導臨床緩解率和內窺鏡改善率方面與生物制劑相比并沒有展現出更大的優勢。
綜上,Upadacitinib 被認為臨床療效更為顯著,可以有效緩解并治愈UC。但同時值得注意的是,Upadacitinib 或許會導致較高的不良事件發生率,可增加帶狀皰疹感染以及栓塞性和靜脈血栓性心血管事件的風險[14]。在特應性皮炎、銀屑病或類風濕關節炎患者的研究表明,Upadacitinib 與嚴重感染風險增加相關,在UC 中,Upadacitinib 治療報告的大多數感染方式為巨細胞病毒感染,這與Upadacitinib 治療類風濕關節炎的研究一致,帶狀皰疹、中性粒細胞減少癥和肌酸磷酸激酶升高也在Upadacitinib 治療UC 患者中更為常見,因此,中、重度UC 患者應考慮預防性帶狀皰疹疫苗接種以減輕這些風險[48-50]。這是國內首次對新興治療方式進行網狀Meta 分析,納入研究質量較高,整體偏倚風險較低,研究結果具有較高的可靠性。但同時,本研究也有一定的缺陷:(1)比較治療沒有從成本方面進行評估,未來的研究應著眼于成本效益評估,這對于醫療提供者、支付者和患者的決策具有重大意義。(2)所有納入研究隨訪時間較短,需要進行更長時間的比較研究。因此,需要進一步的高質量研究(面對面試驗、現實生活研究和藥物經濟學分析)來驗證和擴展當前的證據。
4 小結
根據網狀Meta 分析結果顯示,Upadacitinib 可作為中至重度活動UC 患者的一種有希望的治療選擇,帶來了良好的緩解及治愈率。但同時,需要注意藥物所引起的不良事件,旨在為患者帶來更好的臨床療效和安全性。
作者貢獻:譚書法提出研究思路,設計研究方案,負責數據收集、采集、清洗和統計學分析、繪制圖表;譚書法、高強強、歐艷、黃水蘭共同參與了文獻的檢索、篩選以及數據的提取;譚書法、張磊昌負責論文的寫作及修改;張磊昌負責論文最終版本修訂,對論文負責。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