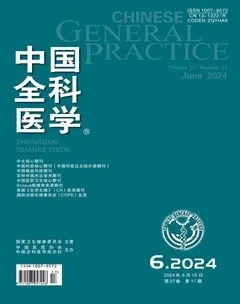Murtagh 安全診斷策略在全科教學門診中的應用:以風濕性多肌痛為例
楊玲,杜雪平
100045 北京市西城區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復興醫院月壇社區衛生服務中心
澳大利亞著名全科醫學專家約翰·莫塔(John Murtagh)提出的Murtagh 安全診斷策略在臨床中非常實用,能夠提高醫生的診斷水平、減少誤診和漏診,包括5 個方面的診斷思維[1-2]:(1)具有這種癥狀或體征的常見疾病有哪些?(2)有什么重要的不能忽略的疾病嗎?(3)有什么容易被遺漏的病因嗎?(4)患者是否患有潛在的常被掩蓋的疾病?(5)患者是否還有其他未說明的問題?
風濕性多肌痛(polymyalgia rheumatica,PMR)病因不明,不同區域患病率差異大[3]。2000—2014 年,美國奧姆斯特德縣≥50 歲人群的發病率約為63.9/10萬[4]。我國目前尚無相關流行病學調查[4]。PMR 發病與感染、遺傳、免疫和炎癥相關[4],常見于50 歲以上人群,近年來PMR發病率逐年上升。PMR臨床表現多樣,但缺乏特異性的實驗室檢查指標和病理學特點,容易被誤診或漏診。國內學者研究發現,PMR 患者在非風濕免疫科首診時,非內分泌專業醫生更多著眼于本專業疾病,導致誤診為肩周炎、頸椎病、骨質疏松癥、腰椎間盤突出癥等,誤診率高達68.0%[5]。老年人常多病共存,合并骨質疏松癥、頸椎病、腰椎退行性病變、炎癥性疾病、感染性疾病和腫瘤時常容易掩蓋病情,給明確診斷帶來一定的困難。
本文擬展示全科教學門診中,針對PMR 病例,基于Murtagh 安全診斷策略培訓全科臨床思維,引導全科住院醫師抽絲剝繭,最終確定疾病診斷和治療。
1 全科住院醫師教學門診實施
1.1 教學對象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復興醫院全科專業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基地培訓的全科住院醫師6 人。
1.2 教學目的
(1)以肌痛為切入點,引導全科住院醫師基于Murtagh 安全診斷策略診治PMR,訓練其全科臨床思維;(2)講解PMR 的治療與隨訪。
1.3 教學門診診室要求
1.3.1 獨立的全科診室:1 間獨立全科診室,用于全科住院醫師接診,設備包括洗手臺、電腦、診療床、診療桌、醫師椅、患者椅、聽診器、觀片燈、身高體重儀、軟尺、檢眼鏡、檢耳鏡、血壓計、溫度計、壓舌板等。
1.3.2 獨立教學評估室:1 間教學評估室,與全科診室鄰近。用于帶教師資和住院醫師討論、評估。配備單向玻璃或錄音、錄像設備等可視系統,用于教學觀摩,也可以兼為全科診室。
全科住院醫師教學門診內容及流程,見圖1。

圖1 全科住院醫師教學門診內容及流程圖Figure 1 Contents and flow chart of teaching clinic for general practice residents
2 教學門診病例
2.1 主訴
肩部、頸部及髖部肌肉疼痛、晨僵2 個月余。
2.2 現病史(全科住院醫師接診、帶教老師補充后)
患者,女,66 歲,約2 個月前晨間醒來出現雙側頸部、肩胛肌肉僵痛,上肢抬舉稍有受限,2~3 d 后出現髖部肌肉僵痛,下蹲、上下樓梯無受限,未出現腕及指間關節疼痛和水腫,無乏力、肌肉紅腫熱,自服“雙氯芬酸”后疼痛緩解。此后上述部位疼痛反復發作,服用“雙氯芬酸”、外用活血止痛藥后疼痛短時間內緩解,48 h 內復發。10 d 前患者于外院檢查心電圖:心率65次/min,竇性心律,ST 段改變,心肌酶指標正常,轉至康復科就診,考慮“筋膜炎”,予以康復、理療后疼痛緩解不明顯。為進一步診治來診。病程中患者無發熱、乏力加重,無肌肉萎縮。精神狀態尚可、睡眠因疼痛變差,二便正常。
2.3 體格檢查
體溫36.1 ℃,脈搏70 次/min,呼吸16 次/min,血壓104/68 mmHg(1 mmHg=0.133 kPa)。身高1.60 m,體質量50 kg,BMI 19.5 kg/m2,腰圍74 cm,臀圍90 cm。神清語利,口唇無發紺,伸舌居中。肺部查體未見異常。心尖搏動位于第5 肋間左鎖骨中線內側0.8 cm,心界不大,心率70 次/min,律齊,心臟各瓣膜聽診區未聞及病理性雜音。腹部查體無異常,肝頸靜脈回流征陰性。頭頸部動脈無怒張、波動增強或減弱、觸痛。雙下肢無水腫。頸部、肩胛肌肉、髖部肌肉無固定壓痛點。脊柱無壓痛、活動度正常。
2.4 輔助檢查
檢查結果見表1。

表1 患者社區化驗檢查和B 超檢查結果Table 1 Results of laboratory examination and B-ultrasonography in community
3 基于Murtagh 安全診斷策略的病歷分析
3.1 導致這種癥狀和體征的常見病有哪些?
該患者表現為頸、肩、髖部肌肉僵痛,臨床上這些部位的疼痛常見于筋膜炎、頸椎病、肩周炎、腰椎間盤突出、骨質疏松、頸腰椎退行性病變,以及炎癥性、感染性疾病等,鑒別診斷見表2[6-7]。

表2 引起肌痛的常見病的診斷與鑒別診斷Table 2 Diagnosis and differential diagnosis of common diseases causing myalgia
3.2 有什么重要的不能被忽略的疾病嗎?
3.2.1 急性心腦血管疾病:突發的劇烈疼痛或老年人突發的頸肩痛常預示急性心、腦血管疾病,老年人感覺器官退化,痛覺等反應減退,尤其是從未出現過的劇痛,如腦出血、腦腫瘤、高血壓及心絞痛、心肌梗死等疾病,一般會伴有劇烈頭痛或胸痛、胸悶呼吸困難、大汗淋漓或肢體運動障礙或頭暈頭痛等。突然加重或睡眠中痛醒的頸肩痛:突然改變的頸肩痛或痛的位置改變,其伴隨癥狀改變等,有可能是心腦血管疾病的先兆。
3.2.2 腦部損傷、顱內病變:伴有精神、神經癥狀、驚厥的頸肩痛。腦部損傷、顱內病變會出現意識障礙,如昏迷,癱瘓等。如出現驚厥,一般提示可能存在顱內疾病或破傷風等。
3.2.3 創傷引起的頸肩痛:若創傷后出現劇烈頸肩痛,可能有頸椎骨折、脫位、頸肩部扭挫傷。
3.2.4 惡性腫瘤:頸椎腫瘤會出現進行性頸肩痛,肢體麻木等。某些惡性腫瘤伴有骨骼肌肉疼痛,但通常合并其他臨床表現。
3.3 有什么容易被遺漏的疾病嗎?
可能遺漏的疾病見表3[8]。

表3 可能遺漏的疾病Table 3 Diseases that may be missed
3.4 患者存在多個癥狀,是否有不容易被識別的疾病?
3.4.1 系統性紅斑狼瘡等風濕病:累及多個系統、器官,實驗室檢查多種自身抗體陽性。皮膚、關節,漿膜、心臟、腎臟,中樞神經系統、血液系統等系統和臟器會出現損傷[9]。早期可僅有1 個臟器受累的表現,同時伴有自身抗體(尤其是抗核抗體,簡稱ANA)陽性。該疾病臨床表現變化無常,起病方式多變,可幾個臟器同時起病,也可相繼出現幾個臟器受損的表現,多數都有一定的起病誘因(感染,日曬,情緒受刺激),早期癥狀最常見的是發熱、關節炎(痛)、疲勞,體質量減輕,較常見的是皮損、多發性漿膜炎、腎臟病變、血液異常、消化道癥狀、中樞神經系統損害等。
3.4.2 PMR 與巨細胞動脈炎(GCA):PMR 多發生于老年人,以雙側對稱性肩胛帶肌、骨盆帶肌和頸部肌肉疼痛和僵硬為主要臨床表現,伴ESR 顯著增快和非特異性的全身癥狀。該疾病病因不明,一般為良性,并且與年齡密切相關,隨年齡增長發病增多,50 歲之前患病較少,女性比男性多2~3 倍,糖皮質激素治療效果顯著。PMR 與GCA 關系密切,兩者易相互合并出現。PMR 患者若出現以下情況,需除外合并GCA:小劑量激素治療反應不佳,顳動脈怒張、搏動增強或減弱、觸痛陽性,且伴有頭痛、頭皮痛或視覺異常等,需完善顳動脈彩色超聲、血管造影、顳動脈活檢等檢查[10]。
3.5 患者是否還有其他未說明的問題?
溝通之后發現患者對持續肌痛、口服解熱鎮痛藥等治療不見效等有質疑,擔憂是否患有疑難雜癥,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患有骨癌或白血病,希望盡快明確病因、緩解疼痛、恢復正常生活狀態。
4 病例診斷
4.1 診療要點
女性,66 歲,雙側肩部、頸部及髖部肌肉疼痛、晨僵2 月余,服用非甾體抗炎藥效果不佳。社區就診檢查紅細胞沉降率(ESR)、C 反應蛋白(CRP)升高、類風濕因子(RF)陰性、腫瘤標志物陰性。診斷考慮疑似PMR。轉至風濕免疫科,檢查結果見表4,考慮PMR,予以復方倍他米松注射液1 mL(二丙酸倍他米松5 mg ∶倍他米松磷酸酯二鈉2 mg)肌肉注射1 次,反應迅速,患者自述24 h 內疼痛減輕80%,確診為PMR,第2 日改為糖皮質激素口服。

表4 風濕免疫科檢查結果Table 4 Results of rheumatology and immunology
4.2 PMR 診斷標準
目前常用的PMR 分類標準為Healey 的分類標準(1984 年)、2012 年美國風濕病學會(ACR)和歐洲抗風濕病聯盟(EULAR)制定的PMR 分類標準。主要依據臨床經驗進行排除性診斷。
4.2.1 Healey 的分類標準(1984 年):(1)疼痛持續至少1個月并累及下列至少2個部位:頸部、肩和骨盆帶。(2)晨僵持續>1 h。(3)對潑尼松治療反應迅速(<20 mg/d)。(4)排除其他能引起骨骼肌肉系統癥狀的疾病。(5)抗核抗體及類風濕因子陰性。(6)年齡>50 歲。(7)ESR>40 mm/1 h。符合上述7 條即診斷PMR。
4.2.2 2012年ACR 和EULAR 制定的PMR 分類標準:該標準見表5。不包括超聲檢查結果的診斷靈敏度為68%,特異度為78%。包括超聲檢查結果的診斷靈敏度為66%,特異度為81%。總體特異度為57.7%~81.5%,靈敏度為68%~92.6%[11],敏感性和特異性較好,可以用來輔助區分PMR、類風濕關節炎、肩骨關節炎和肌病等疾病[12]。
5 PMR 治療
該患者確診PMR 當日予以“復方倍他米松注射液1 mL(二丙酸倍他米松5 mg∶倍他米松磷酸酯二鈉2 mg)”肌肉注射1 次,當日肌痛緩解80%,第2 日予以甲潑尼龍16 mg/d 口服,1 周后復查ESR 45 mm/1 h、CRP 23 mg/L,2 周左右疼痛基本消失,3 周左右ESR、CRP 降至正常。4 周后甲潑尼龍開始逐漸減量,3 個月后減至維持量4 mg/d。綜合醫院風濕免疫科復診,9 個月左右加用免疫抑制劑雷公藤多苷片20 mg/次,3 次/d,口服。治療遵循《風濕性多肌痛和巨細胞動脈炎的診療規范》2023 年版標準如下。
5.1 激素
激素治療為首選用藥,目前尚無激素治療PMR 的標準方案
5.1.1 起始治療:以最小有效劑量作為起始治療。一般醋酸潑尼松片12.5~25.0 mg/d 頓服。病情較重、肌痛、活動明顯受限、存在復發高危因素且不良事件發生率較低的情況下,可選擇藥量范圍內較高劑量的激素用量,對有合并其他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壓等)及存在激素相關不良反應的高危因素時,可使用藥量范圍內較小的激素用量,不鼓勵激素(潑尼松)起始劑量≤7.5 mg/d及強烈不推薦激素(潑尼松)起始劑量>30 mg/d。通常治療后1 周內疼痛迅速緩解,CRP 短期恢復正常,ESR逐漸下降,2~3 周可獲得疾病控制。
5.1.2 激素減量方案:PMR 復發高峰在治療半年內,激素緩慢減量、加強宣教及嚴密監測ESR 能減少疾病復發[13]。應基于患者病情活動性、實驗室檢查指標及潛在不良反應,制訂個體化的激素減量方案。糖皮質激素減量過早、過快或停藥過早是導致PMR 復發的主要原因。PMR 復發患者的治療方案是將口服潑尼松逐漸加量至復發前的劑量,4~8 周再逐漸減量至復發時的劑量。繼初始減量成功和復發治療達到緩解后推薦的減量方案為,每4 周潑尼松減量1 mg(或減量1.25 mg,如潑尼松10 mg/7.5 mg 交替口服方案),在保證維持臨床緩解狀態下直至停藥。該診療規范建議激素減量方案還可以選擇2~4 周后潑尼松緩慢減量,每周減2.5 mg,維持量為5~10 mg/d。隨著病情穩定時間的延長,部分患者的維持量可減為3~5 mg/d。
應用激素治療后,如癥狀改善不明顯,需重新考慮診斷是否正確。目前關于激素的療程無具體推薦,需考量激素的獲益和風險,綜合評價激素相關不良反應的危險因素、并發癥、合并用藥、復發及延長治療等。激素逐漸減量的療程不應<12 個月。大多數患者在2 年內可停用激素。國外研究發現PMR 激素維持治療的平均時間約為3 年,少數患者需小劑量維持多年。停藥后需長時間隨訪觀察,一般認為5 年不復發即為病情完全緩解。
5.2 非甾體抗炎藥
對初發或輕癥者可試用非甾體抗炎藥,如雙氯芬酸、吲哚美辛等。10%~20%的患者單用非甾體抗炎藥可以控制疼痛。應用激素替代非甾體抗炎藥,如患者合并其他原因的疼痛,需短期應用非甾體抗炎藥和/或抗炎鎮痛藥。
5.3 免疫抑制劑
長期使用激素有潛在不良反應,需考慮加用有助于更好控制病情、減少激素用量的治療策略,即在激素治療的基礎上早期聯合免疫抑制劑,如甲氨蝶呤,尤其是使用激素有禁忌證者、激素療效不足者、復發風險高或激素減量難者、存在發生激素不良反應的危險因素或出現激素不良反應者,均可聯用免疫抑制劑。保留糖皮質激素的輔助甲氨蝶呤治療可能對某些患者有益[14]。PMR 合并GCA 者,起始糖皮質激素劑量較單純PMR者大,也可以聯合免疫抑制劑,病情緩解后逐漸減量。
5.4 其他
已開展生物制劑治療的相關研究。目前暫無證據表明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拮抗劑治療PMR 有效,不推薦應用TNF-α 拮抗劑治療PMR[15]。白介素6(IL-6)受體拮抗劑托珠單抗,單藥或聯用糖皮質激素治療PMR/復發性PMR,在控制癥狀、減少激素用量、減少復發等方面顯示出益處,但尚需更多的臨床研究進一步證實[15-16]。
6 預后
PMR 及時診治者病情大多可迅速緩解或痊愈,預后良好,也可能遷延不愈或反復發作。疾病后期如果出現失用性肌萎縮等嚴重并發癥,需進行個體化的體育鍛煉、肢體康復等,降低跌倒風險,對于長期服用糖皮質激素的老年骨質疏松癥患者也能改善其預后。
7 隨訪
7.1 監測腫瘤
該患者治療隨訪第6、12 個月時均檢查胸部、腹部、盆腔CT,風濕免疫指標,腫瘤標志物等未見腫瘤征象。根據報道,PMR 患者確診后的6 個月內腫瘤診出率顯著升高,因此,通過影像學檢查監測腫瘤[17-18]。國外Meta 分析結果顯示,哥倫比亞和拉美地區24%的患者表現出潛伏性多自身免疫(PolyA),惡性腫瘤發生率7.59%,因此常規臨床隨訪應考慮惡性腫瘤、GCA 和潛伏性PolyA[19]。
7.2 預防骨質疏松癥
該患者治療口服糖皮質激素1 個月左右檢查“25羥基維生素D”12.94 ng/mL(>20 ng/mL 為充足,12~20 ng/mL 為不足,<12 ng/mL 為缺乏),予以“維生素D2軟膠囊800 U,2 次/d”“碳酸鈣D3片600 mg,2 次/d”“骨化三醇軟膠囊0.25 μg,2 次/d”預防骨質疏松癥,3~6 個月復查骨代謝、雙能X 線骨密度測量(DXA)。BMI 較高的患者和接受較高劑量糖皮質激素治療的患者25(OH)維生素D 水平低的風險較高,口服鈣二醇補充劑比膽鈣化醇更有效地達到足夠的25(OH)維生素D 水平。糖皮質激素對腸道、甲狀旁腺、性腺、腎臟等的影響導致鈣/磷代謝的改變,這些患者需要口服鈣、維生素D 以及強效雙膦酸鹽,口服雙膦酸鹽不耐受的情況下可選擇靜脈注射雙膦酸鹽[20]。
8 討論
全科住院醫師在全科教學門診中按照Murtagh 安全診斷策略,系統、全面地詢問病史和仔細地查體可獲得患者的癥狀、重要陽性體征,合理選擇能夠提示診斷方向或排除某些疾病的輔助檢查,最后綜合分析,抽絲剝繭,逐步排除常見疾病、嚴重疾病、心理疾病等情況,最終確診為不容易被識別的PMR,糖皮質激素治療迅速顯效。教學門診中利用全科臨床思維指導臨床實踐,提升全科住院醫師對PMR 的診療水平。
PMR 為排他性診斷,無特異性指標,在排除慢性感染、腫瘤和其他風濕免疫病后才能診斷[11]。臨床中容易出現誤診和漏診。沒有及時進行ESR、CRP、RF等檢查也是誤診和漏診的原因之一。PMR 臨床主要表現為對稱性的頸、肩、髖及四肢肌肉僵痛,也可局限單側發作,嚴重者會出現肢體活動受限,甚至不能翻身和起床。伴有ESR 顯著增快。除肌痛癥狀外,還有發熱、乏力、貧血、體質量下降、關節疼痛、頭痛等非特異性臨床表現。因此,全科醫生在社區接診頸肩髖及四肢肌肉僵痛的患者,在詢問病史、體格檢查時要注意患者的肌肉疼痛是否為對稱性、是否伴有雙上肢上舉受限、下蹲起立困難或爬樓梯受限等,患者是否伴有發熱、體質量下降、頭痛、關節痛、乏力等不適,在排除創傷、運動過度、他汀藥物不良反應、炎癥、腫瘤等情況下,利用社區可及性資源,及早完成ESR、CRP,以便早診斷、早治療。社區現有條件不能完成自身免疫相關抗體等檢查者,及時轉診風濕免疫科進一步診治。
作者貢獻:楊玲進行文章的構思與設計,文獻/資料收集及整理,撰寫論文;杜雪平進行文章的可行性分析,負責文章的質量控制及審校,對文章整體負責,監督管理;楊玲、杜雪平進行論文的修訂。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