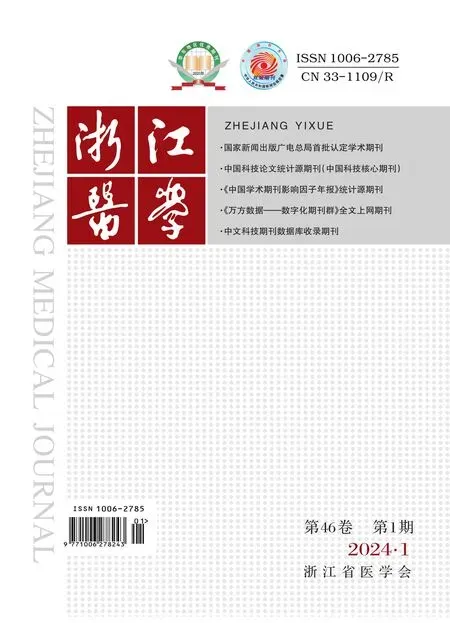類器官技術在肺部疾病研究中的應用
周夢雪 盧錫南 俞萬鈞 王華英
在成人器官中,生理功能的完成取決于以三維(3 dimensional,3D)結構構建的各種類型細胞的協同相互作用。目前大多數體外實驗均使用二維(2 dimensional,2D)細胞培養,無法模擬器官間相互作用的復雜生理病理學和藥代動力學過程。類器官是一種來自于多能干細胞和器官特異性成體干細胞的體外3D 培養細胞結構,是具有類似于體內器官或組織的結構特點并兼備部分功能的一種體外模型。目前科研人員已成功建立多種正常組織及腫瘤組織來源的類器官,涉及人體內各大系統。
肺作為人體內最大的呼吸器官,與人類健康息息相關。近年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支氣管哮喘、間質性肺疾病(interstitial lung disease,ILD)、各種病原體所致肺部感染及肺部腫瘤的發病率均有增高趨勢,嚴重危害國民健康。隨著類器官技術的發展,其在肺部疾病中的應用探索日漸增多,在非特異性炎癥、感染及肺部腫瘤等方面均有涉及。因此,本文就類器官技術在肺部疾病研究中的應用作一綜述,以期為肺部疾病的研究發展提供參考方向。
1 肺類器官的培養
既往文獻報道,基底細胞、Club 細胞和2 型肺泡細胞(alveolar type II cells,AT2)分別是肺氣管、支氣管和肺泡的主要內源性干細胞群,并且可在支氣管肺泡上皮細胞受損時被激活,參與肺修復與再生過程[1-5]。位于支氣管肺泡管交界處的支氣管肺泡干細胞也被證實在肺修復和再生過程中具有多能性和自我更新能力,發現這些細胞的多向分化能力為肺類器官的培養奠定了理論基礎[6]。自Rock 等[2]成功使用氣道基底細胞首次培養類器官以來,肺類器官陸續成功地從成體干細胞、人類多能干細胞(包括胚胎干細胞和誘導性多能干細胞)中生長出來,并在肺纖維化、COPD、感染性疾病及肺癌等肺部疾病的研究中廣泛應用。
呼吸道類器官的培養根據所要得到的疾病模型的差異,具體培養方法也不盡相同。如上文所述,“類器官”這個術語通常用于描述具有多個細胞譜系和組織結構的3D 結構,但有學者提出該術語僅限于包含上皮和間充質細胞的培養物[7]。因此同時包含上皮和間充質細胞的氣液界面培養物也被某些學者稱為類器官[8]。
培養人氣道肺類器官的樣本可取自氣管抽吸物、支氣管肺泡灌洗液、活檢組織、惡性積液及手術樣本[9],培養成功率與樣本中的干細胞豐度相關。在研究COPD[10]、流感病毒感染等與纖毛細胞高度關聯的病理模型時,氣液界面模型及纖毛細胞在外的極化肺類器官模型更為適用,能夠高度模擬人體中氣道纖毛細胞受損的過程。Zhou 等[11]在評估新型流感病毒的傳染性過程中同時建立了纖毛細胞朝向腔內的3D 類器官及纖毛細胞朝向氣液平面的2D 類器官模型,比較兩者后得出這種具有纖毛頂端暴露在外的2D 類器官模型更加符合人類呼吸道流感病毒感染的自然模式。但在進行類器官培養時,相較于3D 模型,氣液界面模型培養所需細胞數較多,而這些細胞難以直接從患者身上獲得。為彌補氣液界面模型培養過程中細胞數量不足這一缺點,Eenjes 等[12]提出一種基于3D 擴增的氣液培養模型,以從氣道上皮細胞數量較少的患者樣本中獲得足夠數量的細胞。頂端細胞在外的3D 氣道類器官[13]被開發出來作為研究病毒感染及篩選抗病毒藥物的工具,彌補了傳統氣道類器官的極化結構,且比傳統氣液界面模型擁有更高的研究宿主-病原體相互作用的敏感性。
2 肺部疾病模型
2.1 細菌感染模型
2.1.1 肺結核 肺結核是一種由結核分枝桿菌(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MTB)引起的傳染性疾病,嚴重危害人體健康。現今已有研究人員將人肺類器官應用于模擬MTB 感染及產生的免疫應答,為臨床上肺結核的治療提供參考。多項研究結果表明,MTB 主要通過入侵肺泡巨噬細胞并在吞噬體內復制引起肺部的感染。Iakobachvili 等[14]首次使用氣道類器官作為人類體外3D 系統來研究MTB 感染的早期步驟。通過顯微注射的方法將MTB 注射入含有基底細胞、纖毛細胞和杯狀細胞的人氣道類器官管腔內,建立感染模型。該團隊進一步研究發現MTB 感染的氣道類器官上皮細胞中IL-8 和β-防御素1 表達顯著增加,可能是感染早期炎癥控制的原因。此外,該團隊還發現MTB 顯著下調了與氣道分泌物產生有關的黏蛋白5B 和黏蛋白4 等基因的表達,MTB 對這些黏蛋白基因表達的抑制可能有助于其在氣道中定植。
鑒于巨噬細胞在肺結核中的重要地位[15],Iakobachvili 等[14]將人單核細胞來源的巨噬細胞與注射了MTB 的氣道類器官進行共培養,觀察到巨噬細胞遷移到氣道類器官基底邊緣并與其相互作用,捕獲和攝取細菌,與細支氣管周圍巨噬細胞遷移到感染部位和吞噬病原體物質的自然過程相類似。以上結果表明氣道類器官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3D 系統來評估MTB 與人類氣道的早期相互作用。
類器官技術應用于肺結核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目前相關報道較少。氣道類器官模型中肺泡細胞的缺失、免疫微環境的缺乏、3D 囊性結構使MTB 感染模型的場所受到限制等都是阻礙類器官技術在肺結核中研究應用發展的原因。而現今氣液界面模型及纖毛細胞在外的極化肺類器官模型培養技術已較成熟,但這些模型在肺結核中的研究應用還有待完善。
2.1.2 銅綠假單胞菌肺部感染 銅綠假單胞菌表達磷脂酶ExoU,ExoU 通過一種特征不明確的途徑觸發病理性宿主細胞壞死[16]。Bagayoko 等[17]培養正常人肺類器官,并通過顯微注射銅綠假單胞菌感染類器官,結果顯示ExoU 在人支氣管類器官中引發病理性脂質過氧化依賴性細胞壞死,類器官完全崩解。能引起肺部感染的細菌多種多樣,目前肺類器官模型對于肺部細菌感染的研究開展相對較少,仍待進一步發展。
2.2 病毒感染模型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可能導致急性呼吸窘迫綜合征、多器官衰竭和死亡。COVID-19 由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征冠狀病毒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引起,傳染性極強,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即引起全球范圍內的大流行。在COVID-19 疫情的大環境下,不少研究人員嘗試探索COVID-19 的研究模型及治療方案。
早在COVID-19 疫情之前,人氣道類器官就已被用來建立流感感染體外模型。在正常肺類器官中,甲流病毒(influenza A virus,IAV)感染后的未成熟及成熟類器官之間的病毒載量無明顯差異,同樣在腫瘤類器官中,IAV 可以感染并從人肺腫瘤細胞建立的類器官中復制。3D 肺類器官在IAV 感染后激活先天免疫反應基因,并且AT2 細胞可能在損傷后的肺再生中發揮重要作用[18]。
原代人支氣管呼吸道上皮細胞可以在氣液界面上分化為成熟的呼吸道細胞[9]。有研究組發現使用小氣道基底細胞建立的氣液界面類器官模型很容易被SARS-CoV-2 所感染[19],同時還發現纖毛細胞是SARSCoV-2 的主要靶點,并通過IFN-K1 驗證該模型可用于SARS-CoV-2 的藥物篩選。此外,在探索COVID-19 引起的過度活躍的免疫反應導致的肺部廣泛受損的機制中也運用了上述培養方法[20]。既往研究發現近端氣道會引起持續的病毒感染,但致命性的過度活躍的免疫反應主要與遠端肺泡細胞有關,單純的近端氣道或遠端肺泡3D 類器官模型SARS-CoV-2 感染很難引起彌漫性肺泡損傷,無法高度還原人體中的病理狀態[11]。由支氣管肺泡干細胞所形成的模型可模擬支氣管肺泡室的3D 形態和細胞組成[21],增加了肺類器官內部多元性及復雜性,最大程度模擬人體中肺的生理病理狀態。
COPD 是COVID-19 患者預后不良的高危因素。最新研究發現,SARS-CoV-2 在COPD 類器官中表現出更高的復制能力,且與正常肺類器官相比,COPD 模型中的IL-6 和IFN-β 顯著減少,并且有抑制C-X-C 基序趨化因子配體10 的趨勢[22]。因此證明類器官病毒感染模型不僅可以在正常肺類器官上建立,還可以在COPD 等疾病狀態下的肺類器官模型上建立,極大程度地模擬了患COPD 等基礎疾病患者感染病毒后的病理生理變化。
2.3 寄生蟲感染模型 腸道是隱孢子蟲的主要感染部位,呼吸道同樣可被感染,從而導致呼吸道隱孢子蟲病。然而呼吸道隱孢子蟲感染的病理生理學機制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未知,有研究者在進行人類小腸類器官研究的同時,嘗試使用人肺類器官來模擬寄生蟲的呼吸道感染[23],將隱孢子蟲的卵囊顯微注射至類器官中,在不同時間節點收集類器官,以證明隱孢子蟲可在人小腸類器官及肺類器官中繁殖并完成其整個生命周期,該研究發現從類器官中新產生的卵囊具有傳染性,其結構及生物學行為同在宿主體內無較大差異。
2.4 COPD 模型 肺類器官可作為研究COPD 病理生理學和治療發展的體外模型。COPD類器官模型可通過暴露于香煙煙霧提取物(cigarette smoke extract,CSE)[24]或細顆粒物2.5(particular matter 2.5,PM2.5)[25]形成,也可直接使用取自COPD 患病個體鼻咽及支氣管上皮細胞[22]建立。Chen 等[24]研究發現COPD 類器官中磷酸化混合譜系激酶結構域樣蛋白和高遷移率族蛋白B1 高表達,且以受體相互作用蛋白激酶3 依賴性的細胞壞死途徑參與COPD 的發生、發展。暴露于PM2.5 的COPD 類器官中的AT2 細胞分化為1 型肺泡細胞的進程被抑制,這可能是PM2.5 導致COPD 的原因之一[25]。支氣管杯狀細胞化生是COPD 的病理生理基礎之一,Li 等[26]發現抑癌肝激酶B1(tumor suppressor liver kinase B1,LKB1)可消除肺上皮細胞促進杯狀細胞化生,并使用小鼠肺類器官模型印證氣道Club 祖細胞LKB1 缺陷會促進抵抗素樣分子-α 的表達,從而推動氣道杯狀細胞分化和肺巨噬細胞募集。
近年來,關于COPD 的組織再生療法成為一個熱點。Wu 等[27]在尋找用于COPD 肺修復的新的潛在藥物靶點的過程中確定E 型前列腺素受體(eseries of prostaglandin receptor,EP)和前列環素受體(prostacyclin receptor,IP)兩個潛在靶點,并使用肺類器官進行藥物篩選,得出EP4 及IP 激動劑對于CSE 暴露受損的類器官顯示出有益作用。晚期糖基化終產物受體(receptor for advanced glycation end-products,RAGE)與COPD 的病理生理學有關,在類器官中,RAGE 配體降低了類器官形成效率和上皮細胞分化為肺類器官的能力,而類器官的平均直徑增加[28],推測RAGE 抑制劑可能是肺氣腫肺組織修復的潛在靶點。
2.5 肺纖維化模型 ILD 是一組主要累及肺間質及肺泡腔,導致毛細血管功能單位喪失的彌漫性肺疾病,可最終發展成彌漫性肺纖維化,導致呼吸衰竭而死亡。絕大部分肺纖維化原因不明,稱為特發性肺纖維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是ILD 中的一大類。近年來IPF 發病率有明顯上升的趨勢,嚴重危害人體健康。
白化病-血小板病綜合征(hermansky-pudlak syndrome,HPS)是一種罕見的常染色體隱性遺傳病,通常以血小板功能障礙、眼皮膚白化病、蠟樣脂褐素在溶酶體中的積累、肉芽腫性結腸炎和肺纖維化為特征,HPS 患者的肺纖維化稱為HPS 相關間質性肺炎(HPSassociated interstitial pneumonia,HPSIP)[29]。Chen 等[30]首次通過HPS1 基因缺失誘導了纖維化樣肺類器官。Strikoudis 等[31]以此為基礎也成功誘導出HPSIP 類器官,認為其可作為IPF 的早期模型。同時他們利用HPSIP 類器官模型發現IL-11 表達增加,認為IL-11 可能是驅動IPF 發生的重要因子。Kim 等[32]使用轉化生長因子β1 誘導后的肺類器官表現出間質區域的膠原蛋白積累和纖維化變化,成功誘導出肺纖維化類器官模型,并在此基礎上進行體外藥物測試,證實乳脂球表皮生長因子8 的短鏈形式擁有與尼達尼布和吡非尼酮同樣的抗纖維化作用。
囊性纖維化是由囊性纖維化跨膜電導調節因子(cystic fibrosis transmembrane conductance regulator,CFTR)基因突變引起的[33]。有研究使用氣液培養的氣道類器官進行藥物篩選,證實FDA 新批準的CFTR 調節劑Trikafta 三重組合的功效顯著優于單獨CFTR 調節劑[34]。與其他類器官培養技術不同的是,該研究提出了培養重編程條件(culture reprogramming condition,CRC),該技術可在體外培養出高效擴增的氣道上皮干細胞,CRC 培養物在體外重復傳代后仍保持干細胞表型,遺傳缺陷得以維持,即使在低溫保存后,也保證了大量擴增和儲存這些細胞以供后續研究的可能性。這種CRC 技術可被用于擴增大量培養類器官所需的原代細胞。
2.6 肺癌模型 類器官技術在肺癌中的研究較為成熟,對肺癌的大規模基因組分析表明,個體患者之間的表型和基因組多樣性表現為腫瘤間和腫瘤內的異質性。癌細胞株一般不能保持其原始的異質性和3D器官結構;因此,它們在表現肺癌的復雜性方面是有限的。類器官代表了一個由干細胞和分化細胞組成的功能單元。此外,腫瘤類器官比人源腫瘤異種移植模型建立所需時間更短,并已證明即使在長期擴增后也能穩定地保留致瘤性,如惡性腫瘤的細胞學特征、異種移植物的形成、突變的保存、拷貝數畸變等,還保留了匹配的親本腫瘤對靶向治療的敏感性[35],逐漸被廣大研究者所采納,作為肺癌相關研究的有效體外模型。Kim 等[36]提取不同患者原發性肺癌組織和配對的非腫瘤性氣道組織,成功培養出來源于腺癌、鱗狀細胞癌、腺鱗癌、大細胞癌和小細胞癌及正常氣道上皮的類器官,他們發現不同肺癌亞型的類器官培養成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源自腺癌的肺癌類器官(lung cancer organoid,LCO)產生腺泡或大腺體模式,并保留肺腺癌標志物napsin-A、甲狀腺轉錄因子1 和細胞角蛋白7 的表達[37]。鱗狀細胞LCO 顯示出明顯的細胞邊界和細胞質角化,符合鱗狀細胞癌組織的組織學特征,還高表達鱗狀細胞癌的特征標志物p63 和細胞角蛋白5/6[38],腺鱗狀LCO 保留了在原始患者腫瘤組織中觀察到的腺癌和鱗狀細胞癌的混合組織學特征[37]。
LCO 可應用于肺癌生長、侵襲及轉移等機制的探索。Lin 等[39]通過建立小鼠的LCO,經Fascin 抑制劑處理后進行下游因子的分析得出Fascin 通過促進糖酵解和PFKFB3 的表達促進肺癌的生長和轉移。
類器官技術可用于建立一個高效的藥物篩選平臺[36,40-41],應用于各種肺部疾病新藥療效及藥物聯合使用方案的療效評價,主要用于肺部腫瘤藥物的篩選。在對建立的各肺癌類器官及正常氣道上皮類器官使用細胞毒性藥物多西他賽及不同靶向藥物測試后發現,相比靶向藥物,正常氣道上皮類器官更容易受到多西他賽損傷,不同個體中獲取培養的腫瘤類器官對藥物的反應也不盡相同[36]。
嵌合抗原受體(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CAR)工程化T 細胞的免疫療法在血液系統惡性腫瘤中取得了顯著的成功[42],但在實體瘤中僅表現出適度的臨床活性。Li 等[43]發現非小細胞肺癌中表達Ⅰ型跨膜蛋白B7-H3,靶向B7-H3 的CAR-T 細胞在體外對腫瘤細胞系和肺癌類器官表現出抗腫瘤活性,這可能是肺癌治療的一個新方向。
類器官同時也是一種高效的臨床預測模型,包括藥物測試中類器官的變化能夠預測患者用藥后的臨床反應。Kim 等[40]從惡性積液、腦轉移灶、骨轉移灶及肺原發腫瘤取得樣本并培養出LCO,在臨床批準酪氨酸激酶抑制劑(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治療患者的隊列中,對其相應LCO 進行TKI 單藥處理,結果顯示LCO 能夠以75.0%的準確度預測患者無進展生存期,并能夠成功預測患者用藥后的臨床反應。最新發布的一項研究中,在納入肺癌類器官藥物篩選測試的5例患者中,其臨床藥物應用后的反應與相對應的肺癌類器官藥物篩選測試100%一致,化療藥物測試中的結果也大致相同[44]。
3 類器官技術在肺部疾病中的臨床應用
類器官技術自2016 年起被納入臨床試驗中,且有逐年遞增的趨勢。截至2023 年10 月10 日,在FDA 官方備案的肺相關類器官的臨床試驗已有19 項,半數以上研究旨在探索類器官技術指導肺癌患者臨床用藥和個體化醫療的臨床價值。
一項臨床Ⅱ期研究通過從HER2-A775_G776YVMA 插入突變的晚期肺腺癌患者腫瘤標本建立的LCO,分別用阿法替尼及吡咯替尼刺激后得出吡咯替尼這種泛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TKI 對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 外顯子20 突變的非小細胞肺癌具有強大的抗腫瘤活性[45]。肺癌類器官也可作為臨床研究中重要的體外部分的補充及完善。Yun 等[46]發現埃萬妥單抗抑制上皮生長因子受體(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外顯子20插入驅動突變型非小細胞肺癌類器官的生長,且呈濃度依賴性。對于雙靶點突變的肺癌患者,類器官依然是有效的體外藥物測試模型。使用達拉非尼、曲美替尼聯合處理源自某位同時攜帶EGFR 和鼠類肉瘤濾過性毒菌致癌同源體B1 基因突變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的LCO,可觀察到明顯的類器官生長抑制,然而布加替尼、西妥昔單抗單藥使用或布加替尼、西妥昔單抗聯合處理方案反而導致腫瘤類器官生長,該患者接受達拉非尼及曲美替尼聯合治療后在影像表現上病灶明顯縮小,與其LCO反應一致[40]。
4 小結
類器官具有與人體器官組織的高度同源性,長期保持原始組織特征及遺傳一致性,由不同類型的上皮細胞形成的3D 空間結構,所需樣本量較少,構建時間短等優點,彌補傳統2D 細胞培養和動物模型的缺陷,是作為肺部疾病研究、藥物篩選、疾病預測的高效體外模型,同時滿足實驗的倫理要求,因此在肺部疾病中的研究運用越來越廣泛。隨著類器官技術的發展,其在個性化醫療領域也顯現出良好前景。以患者來源的非小細胞肺癌類器官的藥物篩選所制定的個性化治療方案在臨床上已被小范圍應用,也表現出令人滿意的治療效果。
當前的類器官模型仍受限于無法有效模擬人體中腫瘤微環境,無法重現人體中各組織或器官相互作用等,無法完全還原所建立的疾病模型在人體中的實際狀態。如果能夠攻克這些難題,類器官技術在解決肺部疾病甚至是人體各系統中疾病的研究中將具有更為廣闊的應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