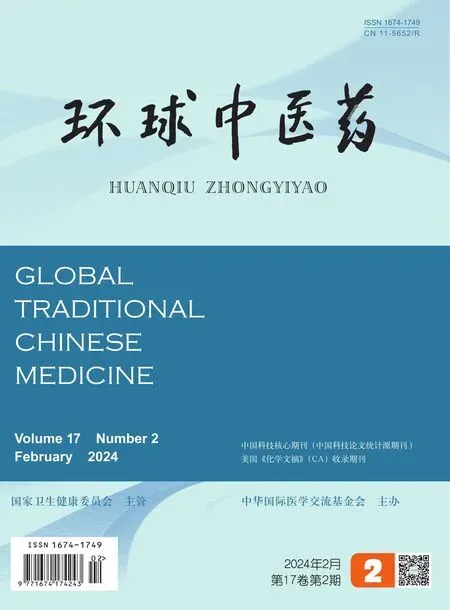淺議“肝氣虛”在青春期后中重度痤瘡治療中的辨治意義
胡博 曹云松 王東峰 李方凱 任雪雯 姚榮
痤瘡是臨床常見的毛囊皮脂腺的慢性炎癥性疾病,在臨床中屬于典型的易診難治性皮膚病。本病的全球發病率目前約為9%,是全球的第八大疾病,我國發病率在8%~80%[1]。反復發作的中重度痤瘡在中青年人群中比例更高,因為它的皮損中囊腫、結節、膿皰等大量出現且容易遺留瘢痕等損容性結果,不但破壞了人們膚白貌美的祈愿,同時嚴重的影響到人們的社交、婚戀及身心健康。現代醫學認為遺傳、情緒、免疫激素引起的皮脂異常分泌、毛囊導管過度角化以及細菌感染是本病發生的重要因素。中醫學的主流觀點認為痤瘡的發生與風熱、痰瘀、濕熱、沖任不調、陰液虧耗等病因相關,涉及五臟。其中,青春期后中、重度痤瘡的病因病機多與痰瘀互結、肝郁化火、腎之陰陽不足相關[2]。然而,我們在臨床實踐發現許多患者以倦怠、乏力、便溏、情緒低落、少氣懶言、咽干、腰酸、多夢、五心煩熱等“氣陰兩虛,虛火浮越”的伴隨癥狀為主,究其原因,可能與作息無律、壓力較大、缺乏運動、藥物攻伐等后天因素導致的肝氣不足的病機更加吻合。故本文擇肝氣虛為討論重點,淺析青春期后中重度痤瘡的從肝氣虛角度著手的辨治思路。
1 肝氣虛在青春期后中重度痤瘡辨治中的意義和必要性
青春期后中、重度痤瘡是一種慢性炎癥性皮膚病,中醫學認為它與臟腑功能失衡相關,現代醫學也認為本病受內分泌、皮膚菌群失調等多因素影響。《素問·靈蘭秘典論篇》云“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強調肝之功能異常相當于臟腑失去了“調節器”,調節不當則機體有恙,情志失常;現代醫學也認為肝臟具有重要的免疫調節作用,因此“從肝論治”本病,發揮肝的“調節功能”近年來越發受到臨床醫生的重視。從中醫“治肝”歷史發展的角度梳理亦或《中醫基礎理論》的教材中,我們都能看到關于“肝氣虛”的認識,認為治療時有氣、血、陰、陽之分,然前人多論“肝氣肝陽常有余”,讓“肝氣虛”的辨治尚缺乏系統性[3]。臨床實踐中筆者發現青春期后中、重度痤瘡患者人群的病理特點或許更加符合該證候的描述,但鮮有論述。因此,對此類痤瘡患者“肝氣虛”證的辨識,不僅能夠完善該病“從肝論治”體系的完整性,亦能豐富對痤瘡病機的認識,提供不同的治療角度和方法。
1.1 “從肝論治”是痤瘡治療的重要切入點,但鮮有論“肝氣虛”者
痤瘡的中醫治療歷史源遠流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本病的治療多則之于肺經風熱,故有“肺風粉刺”一名。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明清之后逐漸形成了從肺、脾、胃等多維度論治的辨治體系;而近代醫家通過對其病因病機的不斷完善,尤為重視從肝論治痤瘡。從五臟生理關系角度來看,肝之疏泄功能與痤瘡的發生密切相關。若其失常,可影響肺臟宣發肺氣、輸布津液功能,氣血滯澀、木火刑金而發病;可干擾脾胃升降之序,進而導致胃腸濕熱而發病;可助心火,心火上炎而成疾;亦常與腎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肝腎陰虧,水不涵木皆可至病。從經絡循行角度分析,肝經縱橫聯系,作用廣泛。痤瘡之發病與肺經關系密切,該經起于中焦與大腸相表里,與肝經、胃經相交匯。與此同時,肝經亦與任、督、沖脈交匯,具有廣泛溝通與調節作用。肝經在面部循行過程中“上出額”“從目系下頰里,環唇內”均為痤瘡的好發部位。
從CNKI上挖掘近30年“從肝論治”痤瘡的文獻130余篇,研究發現肝郁氣滯、沖任不調、肝郁化火證占據了“從肝論治”本病證型的前三位;而診出最少的三個證型則為肝郁濕熱證、陰虛內熱證、肝火痰瘀證,而肝氣虛證的診出數為0[4]。痤瘡的總體辨證以虛實夾雜為主,其中屬實多為肝氣郁、肝經濕熱、肝火;屬虛弱者多為肝陰虛,肝血虛,肝氣虛的辨證尚為空白。
1.2 “肝氣虛”的辨識是對“從肝論治”理論的完善
與肝氣虛的相關的概念首見于《素問·四氣調神大論篇》,“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暗指情志不遂可能導致肝氣不足。《靈樞·本神》中明確提出了肝氣虛的名詞,“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并認為害怕是其主要表現之一。宋元時期進一步豐富了肝氣虛辨治體系,如《儒門事親·卷十四·病機》釋中提到“下,謂下焦,肝腎氣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認識到了肝氣不足,可導致便溏、腹瀉。清代可謂肝氣虛理論的成型時期,其代表人物為傅山和王旭高。其中,傅山明確提出肝氣虛而郁的理論,其中《傅青主男科重編考釋·臟治法門·腎肝兩虛》指出“補肝必須補腎中之水,補腎中之水又不可不補肝木”[5],強調了肝腎同病、同治的重要性,補充了“肝腎同一治”前期理論治一臟而療兩臟的局限,并據此擬定了處方,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理—法—方—藥辨治體系。王旭高在其《西溪書屋夜話錄》中打破了肝無補法的束縛,不但系統總結了治肝三十法,并著重論述了肝之虛證當分為氣、血、陰、陽,提出了“氣虛為陽虛之始,陽虛為氣虛之漸”觀點,明確了補肝氣的重要性[6]。陳家旭等[7]較為系統的總結了肝氣虛的證的主要表現:第一,有氣虛證的臨床表現;第二,肝氣虛眩暈的特點;第三,有情緒波動或情志變化;第四,肝經循行部位出現癥狀;第五,舌淡胖,有齒痕,脈虛無力或弦細。這些理論、認識較為系統的梳理了“肝氣虛”的概念,完善肝藏象的系統辨治體系。
1.3 “肝氣虛”是青春期后痤瘡的重要病機
青春期后痤瘡主要指25歲及以上的痤瘡患者。包括持續性痤瘡(痤瘡由青春期痤瘡延續而來);成人遲發性痤瘡(24歲之后首次出現發病);復發性痤瘡(青春期痤瘡治愈后復發)。其中成人遲發性痤瘡多與內分泌疾病、短期的作息不規律、情緒壓力等因素相關,或皮損爆發但愈后較好。中重度痤瘡是按照目前國內公認的痤瘡的分級方法-3度IV級(Pillsbury國際改良)定義的[8]。一般認為中度II的典型皮損包含粉刺和炎性丘疹;中度III級的痤瘡以一定數量典型的粉刺、丘疹以及膿皰為主要表現;重度IV級的分類除上述皮損外,還有囊腫、結節以及聚合性損害及潰瘍的出現。持續、復發性痤瘡人群往往較大概率出現囊腫、膿皰、聚合性皮損等重度痤瘡表現,同時也更容易遺留色素沉著、瘢痕、皮膚萎縮等皮膚問題。較青春期患者而言,此類人群有更多的生活壓力,工作、家庭、人際關系等往往進一步壓縮了時間和空間;煙酒、熬夜、久坐少動成為他們的標配,過度的消耗透支了他們的先、后天之精,進而各種激素水平異常、菌群失調、植物神經功能紊亂是此類患者經常背負的病理“標簽”。
從中醫學的源流來看“肝氣虛”的概念有狹義和廣義之別。廣義之“肝氣虛”多指其疏泄和藏血功能的減退;而狹義之“肝氣虛”則特指肝氣“升發之力不足,溫煦,調暢之力下降”引起的疏泄不及。肝氣疏泄的生理效應主要體現在:調暢氣機、耐受疲勞、女子以肝為先天、情志、生殖、發育、衰老等諸多方面。除皮損分布特點外,上述紊亂、失調且伴隨的口干、肢困、疲勞、乏力、便溏、嗜睡、月經不調、陰囊墜脹、情緒低落、眼干等癥狀恰是疏泄功能失常重要體現,進一步說明了“肝氣虛”在中重度痤瘡發病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1.4 青春期后中重度痤瘡患者“肝氣虛”的病因復雜而多樣
較青春期痤瘡患者而言,青春期后中重度痤瘡患者往往病程較長,飲食、作息不規律,缺少運動,且工作、學習壓力較大。這些特定狀態下的生活特點往往是皮疹反復和加重的重要因素,從中醫角度來看,它們與肝氣虛的關系體現在以下方面。
1.4.1 飲食不潔,熬夜縱欲使得肝癆腎傷 《素問》載“食氣入胃,散精于肝,淫氣于筋”,飲食無度,胃氣受損,化源不足,無以養肝;《備急千金要方》載“其讀書博弈等過度患目者,名曰肝勞”[9],說明用眼過度會導致肝的虛損。子午流注理論也證實丑時為肝經當令之時,若不能休息則疏瀉不暢,藏血不足,而成肝腎自虛之證。此外,《壽世保元》也提到“大醉入房,氣竭肝傷……陽屢不舉”,說明縱酒縱色能使肝氣衰竭,腎精虧耗。當代學者郭桂華[10]認為酒毒傷肝同樣是導致肝氣虛的重要原因。
1.4.2 病程日久傳變,失治誤治所致 《難經·八十一難》提及“假令肺實而肝虛微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損不足而益有余。此者中工之害也”,說明金旺乘木是導致肝氣虛的重要原因。我們稍作延伸,痤瘡初期多以肺經風熱之證論治,屬金旺之像,若失治誤治亦有成為肝氣虛出現的病理基礎。與此同時,長期以來痤瘡的臨床治療常以肝氣無虛不補立論,治以苦寒之品為多,多從瀉肝伐肝出發,久則損其氣。張錫純[11]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曾大聲疾呼:“不知人之元氣,根基于腎,而萌芽于肝。凡物之萌芽,皆嫩脆易傷于損。”告誡人們要提高對肝之虛證的重視。
1.4.3 學習工作壓力,化生情志之變 《雜病源流犀燭》載曰:“諸郁,臟氣病也,其原本由思慮過深,更兼臟氣弱,故六郁之病生焉。”[12]提示我們情志所變可能初為肝氣實而郁,然氣血運化失常,疏泄失職,日久化為肝氣虛而郁。
1.4.4 缺乏運動,久臥傷氣 長期以來,我們都將脾氣虛視為氣虛的主體,伐肝之余不忘健脾。《張錫純醫案》中有從肝氣虛角度治療“脾胃虛弱”的案例[13],書中載有王氏女,年僅二十,感胃中寒涼,納食漸少,而伴見左半身下墜感,左側睡眠等證。諸醫以脾胃虛弱,相火不足治療1年未效,后以肝氣虛為證治療而愈。這從一定角度提醒我們,肝氣虛的癥狀易被掩蓋,扶土不效時,勿忽視補肝。
1.4.5 年齡的增長,導致肝腎不足 《靈樞·天年》云“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素問·上古天真論篇》“五八,腎氣衰,發墮齒槁”,提示年齡的增長能夠導致肝氣虛衰,腎精不足,是機體衰老的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年齡不單出只是數字的改變,從另一方面看,長期的壓抑,生活無律也會加速機體的衰老,耗損肝腎之氣。
2 青春期后中重度痤瘡“肝氣虛”的辨治要點
診斷時望診可見患者皮膚晦暗,無光澤,油皮或混合型皮膚,可見明顯毛孔粗大。除一定數量的典型粉刺樣皮損外,可見反復發作的膿皰、深部囊腫、聚合性皮損。皮損以面部,顏色多淡紅或暗紅、口周、兩頰、額頭、胸背部多發。除皮損表現外可伴有神疲乏力,肢體困重,易驚善恐,大便溏泄或便秘,腹脹綿綿,精神不振,情緒低落,心煩郁悶,頭暈嗜睡,咽干目澀,月經量少,陰囊潮濕、墜脹,腹脹,納差,舌淡胖或淡黯、有齒痕,脈虛無力或細緩。
補肝之法:肝之生理特點為體陰而用陽,故其補法可分為二,一曰固其體,二曰強其用。所謂固其體:多指補益其氣、血、陰、陽。強其用多體現在維持其生理功能正常,以調他臟的方法來達到補肝的目的。固其體方面:肝之血、陰、陽之虛補法不再贅述。縱觀古代醫家補肝氣之法,多以升補為主,如張錫純在《醫學衷中參西錄》中指出肝氣虛的病機為郁、虛、陷為主,后世醫家多沿用之[14]。本人治療時更注重恢復肝之疏瀉功能,以氣為主,補中有散,散時注斂,故采用益氣(黨參、黃芪、白術)、柔肝(柏子仁、密蒙花、白芍)、辛散(細辛、生姜、桂枝)、風生(防風、天麻、谷精草等)的補肝氣之法。強其用方面:更多的體現在五臟的生克關系上,這里重點討論肝腎,肝肺關系。肝腎關系上,我更認可傅山的相關認識,如《傅青主男科重編考釋·臟治法門·腎肝兩虛》“……蓋腎為肝之母,肝又為命門之母也,豈有肝木旺而不生命門之火者哉?命門是一身主宰,當生五臟之氣,不宜為五臟所生。然而五臟疊為生克,肝既是木,豈有木不能生命門之火乎?……”說明既為肝腎同病,便不可以補腎代替補肝,當同病同治。常以生、熟地,菟絲子,山萸肉、山藥,肉桂,附子為補腎之品。王旭高在“治肝三十法”中曾直言肝腎關系同治之法名曰:補母。他認為如水虧則易損及木,清之不應時當益腎水,此為虛則補其母之法,并列舉六味地黃丸等藥物[15]。恰如頑固性痤瘡之浮火并非由肝氣太過化火所致,實為腎水虧耗母病及子所得。究其病因實乃腎水不能滋養肝體,造成肝腎俱虛。肝肺關系方面,肝經循行上注于肺;《臨證指南醫案》言:“人身氣機合乎天地自然,肺氣從右而降,肝氣從左而升,升降得宜,則氣機舒展。”提示二者聯系緊密,若肝之升降不及則氣機不展,故有下陷之險。痤瘡之發病初期多以肺實,病久合并肝氣不足治療時當秉承《難經》“……肺實而肝虛微少氣,用針不補其肝,而反重實其肺損不足而益有余……”之意,清肺之余,不忘補肝之虛。
3 驗案舉隅
患者,女,33歲,公司職員,于2022年6月12日以“反復面部皮疹2年余,加重兩周”就診。
患者自訴反復面部皮疹伴痛癢2年,就診于北京多家三甲醫院,多予口服抗生素、丹參酮、裸花紫珠顆粒等藥物;外用阿達帕林凝膠、夫西地酸乳膏,間斷“刷酸”治療后皮疹仍反復發作。兩周前,患者因情感因素皮疹爆發,疼痛較重,間斷口服阿奇霉素、外用夫西地酸乳膏后皮疹改善不明顯。刻下:面部泛發皮疹,個別皮疹疼痛較著,無發熱,口干,無口苦,口黏,少語懶言,情緒低落,納少,小腹墜脹,睡眠不實,小便黃,大便溏、日2~3行,月經量少色淡,常三日而盡。查體見患者面部泛發鮮紅至暗紅色丘疹、斑丘疹,局部可見脂栓嵌入。其間可見膿皰、暗紅色結節及囊腫,主要分布于前額、兩頰及口周。舌淡黯,苔黃膩有齒痕,脈細弱。診斷:痤瘡。中醫診斷:粉刺(肝腎不足,痰瘀互結)。治以抗感染、修復屏障聯合中藥補肝氣、滋腎陰、解毒化瘀散結。予患者美滿霉素50 mg/次,一天兩次,連續口服2周。中藥處方:枇杷葉10 g、生側柏葉10 g、桑白皮10 g、黃芪40 g、柴胡10 g、白術15 g、茯苓20 g、陳皮10 g、半夏9 g、生薏苡仁15 g、枳殼10 g、黃芩10 g、黃連6 g、生山楂20 g、菟絲子10 g、白花蛇舌草30 g、皂角刺10 g、山茱萸15 g、夏枯草15 g、土貝母15 g、大腹皮15 g、肉桂6 g、三七6 g、升麻10 g,14劑,水沖服,日一劑分服。
二診(2022年6月27日)。服藥2周后,患者部分皮疹消退,仍色紅,疼痛及瘙癢緩解,自覺面部出油較前減少,腹脹減輕,小便可,大便溏,仍覺口淡無味,乏力,善太息。查體見患者面部油脂較前減少,結節、膿皰基本消退。余癥未變,鼻部可見較多黑頭粉刺。舌淡胖,有齒痕,脈沉細。原方加黨參10 g、川芎15 g以益氣活血,去大腹皮。因就診不便,予繼服28劑。中西外用藥物同前,囑原量繼服美滿霉素1周。
三診(2022年7月29日)。首診6周后,患者訴面部皮疹大部消退,瘙癢感減輕,皮疹少量新發,但消退較快。乏力好轉,諸癥皆消。查體見患者面部油脂較前減少,兩頰及額部散在較多暗紅色丘疹、斑丘疹、色沉,可見較多細碎脫屑。方中去黃連、皂角刺,加僵蠶10 g、生姜6 g以滌余邪、散寒毒。繼服28劑。
四診(2022年8月30日)。首次治療10周后,患者前癥好轉,僅面部散在少量暗紅色色沉及暗紅色丘疹、斑丘疹,局部皮膚可見萎縮性痕。舌淡黯,苔薄白,脈細滑。前方去夏枯草、土貝母、白花蛇舌草,加桂枝6 g、防風12 g、赤小豆30 g以辛散通絡、除濕解毒。繼服14劑后囑停用中藥口服。
按 此案中、重度痤瘡患者為虛實夾雜之證。其實者多濕熱瘀毒,其虛者為氣陰兩虛,虛火上浮。為所謂氣虛之象,概女子以肝為用,病久或用苦伐太過易傷肝氣,或始為氣實而郁,但現為肝氣升之不及致氣虛而郁,故有腹墜、乏力、情緒低落之癥。治療時急責重其標,緩則治其本,用藥時當注重寒熱并用、攻補兼施、平和緩瀉[15]。急性期核心病理可概括為濕熱瘀阻,治療宜清熱除濕,解毒散結為主,益氣滋陰為輔。予李元文教授自擬方“消痤湯”加減,該方以枇杷清肺飲合黃連解毒湯為主方加減,以清熱利濕,扶正解毒為法[16]。在此基礎上加用軟堅散結,逐瘀化痰之品,對改善膿皰、結節、囊腫等皮損具有良好效果。在患者濕熱之象有所緩解后,則側重復其肝氣,通絡滌邪,滋其腎源。自古善補陰著注陽中求陰,適當加入辛散藥物,如桂枝、肉桂既可升散肝氣,又可助陽化陰,溫化濕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