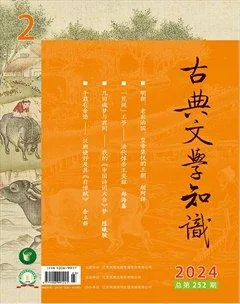錢鍾書解讀孟郊《長安旅情》
張培鋒
盡說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
玉京十二樓,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門,何門薦孤士。
【錢鍾書賞評】
《詩經(jīng)·小雅·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讀《既醉》《節(jié)南山》《正月》諸什,亦可曰:國治家齊之境地寬以廣,國亂家哄之境地仄以逼。此非幅員、漏刻之能殊,乃心情際遇之有異耳。……岑參《西蜀旅舍春嘆》:“四海猶未安,一身無所適。自從兵戈動,遂覺天地窄。”李白《行路難》:“大道如青天,我獨(dú)不得出。”……柳宗元《乞巧文》:“乾坤之量,包容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以至《水滸》中如第一一回林沖、第一六回楊志等皆嘆:“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哀情苦語,莫非局蹐靡騁之遺意也。……歌德名篇寫女角囚系,所歡仗魔鬼法力,使囹圄洞啟,趣其走,女謝曰:“吾何出為?此生無所望已!”王爾德名劇中或勸女角出亡異國,曰“世界偌大”,女答“大非為我也;在我則世界縮如手掌小爾,且隨步生荊棘”。蓋斯世已非其世,群倫將復(fù)誰倫,高天厚地,于彼無與,有礙靡騁,出獄猶如在獄,逃亡亦等拘囚。……即以孟郊為例,《長安旅情》又曰:“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而《登科后》曰:“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豈非長安隨人事為“寬窄”耶?(《管錐編》)
【品讀】
古代著名的詩題《行路難》,到底要表達(dá)一種怎樣的感情?錢先生從《詩經(jīng)·小雅·正月》篇說起,指出天地雖大,但我卻無路可走,堪稱古來詩人的同感共慨。其內(nèi)在之理,錢先生亦作出深刻概括:“此非幅員、漏刻之能殊,乃心情際遇之有異耳。”也就是說,這類作品大多數(shù)寫在動蕩的亂世,或者雖然是“盛世”,但對詩人個人而言,卻處于人生逆境之時,這時候就會覺得天地沒有那么廣闊,有一種走投無路的感覺,這并非實(shí)際的地理、時間有什么變化,而是詩人的心境造成的。錢先生舉出《詩經(jīng)》以來的一系列作品,乃至《水滸傳》中人物的感嘆、歌德名篇《浮士德》中的一個情節(jié)、王爾德話劇《一個無足輕重的女人》中女主角的感喟之言等等,可見這是人類的一種共通的感受。
在眾多作品中,中唐詩人孟郊尤其典型。古來有所謂“郊寒島瘦”之說,孟郊的“寒”表現(xiàn)在哪里呢?《長安旅情》一詩就堪稱典型。錢先生引用了他“我馬亦四蹄,出門似無地”一句,實(shí)際上整首詩都反映了孟郊作為“寒士”那種窮困潦倒、走投無路的心態(tài)。但錢先生又指出:這是孟郊尚未登科時所寫,他那首著名的《登科后》寫道:“昔日齷齪不足夸,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長安的街道到底是寬是窄呢?
顯然在孟郊眼中是不同的,這就有如同樣的所謂“客觀時間”,在不同人的心中有著不同的感受,而孟郊的作品則顯示空間層面上的“主觀構(gòu)造”。可見時空既是“客觀”的,也是“主觀”的,客觀與主觀結(jié)合,才共同構(gòu)成這個所謂“真實(shí)”的世界,古往今來的詩歌往往反映著“主觀世界”的這一層面,不容忽視。而如果排除了詩歌所創(chuàng)造的“主觀世界”,所謂的“客觀世界”是不完整,更是不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