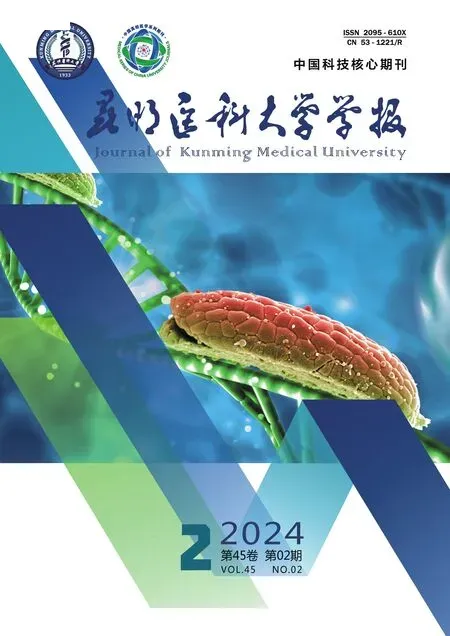腸道菌群代謝物TMAO 與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關系
李媛媛 ,宋亞賢 ,徐玉善 ,曾曉甫 ,袁 惠 ,徐 兆 ,江 艷
(1)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內分泌一科;2)超聲科,云南 昆明 650032)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是目前全球最常見的肝臟疾病之一,在我國,成人NAFLD 總患病率為32%,明顯高于全球患病率,且呈逐年上升趨勢,是我國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1]。目前,NAFLD 在全球范圍內表現出最顯著的肝硬化增長,是全世界引起肝硬化發病的高危因素[2]。
腸-肝軸是肝臟與胃腸道在解剖上緊密聯系,許多的證據表明,腸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謝產物直接影響腸道形態和免疫反應,導致炎癥和腸道內毒素血癥的異常激活;腸道微生態失調也會導致腸道肝臟功能障礙,膽汁酸代謝途徑的改變[3]。
腸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謝產物可以作為腸道和肝臟之間的分子載體,一些特定的腸道微生物群和代謝產物,包括短鏈脂肪酸、膽汁酸、脂多糖、膽堿和三甲胺(trimethylamine,TMA),會隨著疾病的嚴重程度和纖維化階段而發生變化,這表明這些物質具有作為診斷NAFLD 標志物的潛力,因此,有必要對腸肝軸進行進一步的研究[4]。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20 年11 月至2021 年11 月期間在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內分泌一科住院及門診體檢就診者共計118 例。根據研究對象超聲定量肝臟脂肪含量結果,分為2 個組。肝臟脂肪含量≥9.15%為NAFLD 組,共86 例,男49 例,女37 例,平均年齡(50.63±15.02)歲;肝臟脂肪含量<9.15%為健康對照組,共32 例,男12 例,女20 例,平均年齡(40.34±12.47)歲。
所有研究對象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并經昆明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2022 倫審L 第10 號 )。
NAFLD 診斷標準根據2010 年中華醫學會肝臟病學分會脂肪肝和酒精性肝病學組制定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診斷標準》[10],排除有大量飲酒史、肝纖維化、惡性腫瘤,伴有病毒性、藥物性、自身免疫性、全胃腸外營養、肝豆狀核變性等明確損肝因素導致脂肪肝的特定疾病。
健康對照組為體檢健康人群,排除有高血壓、血脂異常、冠心病、腦梗、糖尿病、惡性腫瘤病史;調查前1 個月內及調查中未使用可能影響糖代謝的藥物,如糖皮質激素、甲狀腺素、噻嗪類藥物等。
1.2 臨床指標收集
詳細采集研究對象相關臨床資料:性別、年齡、身高、體重、腰圍、臀圍、吸煙史、飲酒史、既往疾病史、用藥史、家族史,并準確記錄受試者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紅蛋白(HbA1C)、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LDL-C)、天冬氨酸氨基轉移酶(AST)、丙氨酸氨基轉移酶(ALT)、γ-谷氨酰轉肽酶(γ-GGT)、血清總膽汁酸(TBA)、尿酸(UA)、腎小球濾過率(GFR),根據公式計算出胰島素抵抗指數(HOMA Insulin Resistance,HOMA-IR)[11],公式如下:
1.3 飲食結構問卷調查及超聲定量肝臟脂肪含量
由本課題組的醫生對所有受試者進行飲食結構問卷調查,調查方式采用一對一、面對面問卷調查。所有受試者使用Hitachi 超聲診斷儀4C 突陣探頭在受試者仰臥位,充分暴露肝區情況下采集受試者肝臟右葉肋間切面圖及肝右腎矢狀切面圖,見圖1、圖2,聯合運用超聲肝臟回聲衰減和肝腎回聲比值這2 項定量參數估算肝臟脂肪含量,以超聲定量肝臟脂肪含量9.15%作為診斷脂肪肝的切點[12]。

圖1 肝臟右葉肋間切面圖Fig.1 Sagitta plane of right liver and kidney

圖2 肝右腎矢狀切面圖Fig.2 Intercostal view of right lobe of liver
1.4 TMAO 及其前體代謝物檢測
采集研究對象清晨空腹靜脈全血2~3 mL,在4 ℃、3 000 r/min 離心10 min 分離出血清,取200~300 μL 分裝于2 mL 凍存管,于-80 ℃冰箱保存備用。在提取代謝物后,通過用高效液相色譜-質譜分析(5500 QTRAP 質譜儀AB SCIEX)檢測出TMAO 及其前體代謝物水平。
1.5 糞便DNA 提取及PCR 反應
基于本課題組前期研究[13],用qRT-PCR 法檢測糞便中目標細菌DNA 的表達量。收集研究對象的新鮮糞便標本200~300 mg,采用QIAGEN的 QIAamp PowerFecal Pro DNA Kit 試劑盒,按照操作步驟提取樣品DNA。
(四)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了初步概括,奠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奮勇前進強大精神力量的初始基礎
引物及內參序列,見表1,配制PCR 反應體系(總體積25 μL)。設置PCR 反應條件:直腸真桿菌、多行擬桿菌采用兩步法進行反應,95 ℃10 min 為預變性階段,95 ℃ 15 s、65 ℃ 1 min 為PCR 擴增階段,共40 次循環;雙歧桿菌反應條件為:95 ℃ 5 min 為預變性階段,95 ℃ 15 s 溶解、60 ℃ 1 min 退火、72 ℃ 45 s 延伸為PCR 擴增階段,共35 次循環;乳酸桿菌反應條件為:95 ℃ 10 min為預變性階段,95 ℃ 15 s、61.6 ℃ 1 min 為PCR擴增階段,共35 次循環;內參GAPDH 反應條件為:95 ℃ 30 s 為預變性階段,95 ℃ 45 s 溶解、61 ℃ 30 s 退火、72 ℃ 34 s 延伸為PCR 擴增階段,共40 次循環。待反應結束后,分析溶解曲線和擴增曲線,結果使用軟件以2-△△Ct法進行相對基因表達分析,各目標菌群擴增曲線,見圖3。

表1 引物及內參序列Tab.1 The sequences of primer and internal reference

圖3 腸道目標菌群PCR 擴增曲線圖Fig.3 The real-time PCR curve of the target intestinal flora
1.6 統計學處理
數據運用SPSS 26.0 和Graphpad Prism 9 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和圖形制作。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表示,2 組數據間比較采用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P25,P75)表示,數據間比較采用非參數秩和檢驗;等級資料使用非參數秩和檢驗分析;相關分析采用Pearson 相關性分析;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研究對象基本信息及一般臨床指標比較
NAFLD 組與健康對照組相比,年齡、BMI、腰圍、臀圍、FPG、HbA1C、HOMA-IR、TG、ALT、γ-GGT、TBA、UA、GFR 升高,HDL-C降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2 組間性別、TC、LDL-C、AST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 組受試者的一般臨床指標比較 [M(P25,P75)/ ]Tab.2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P25,P75)/ ]

表2 2 組受試者的一般臨床指標比較 [M(P25,P75)/ ]Tab.2 Comparison of the general data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P25,P75)/ ]
*P <0.05。
2.2 研究對象TMAO 及其前體代謝物比較
與健康對照組相比,NAFLD 組TMAO、TMA及膽堿水平均明顯高于健康對照組(P<0.05)。但2 組間甜菜堿和左旋肉堿的水平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進一步對2 組肝臟脂肪含量與TMAO、TMA 及膽堿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肝臟脂肪含量與TMAO 的水平具有正相關性(P<0.05),見表4。
表3 2 組受試者TMAO 及其前體代謝物比較 [M(P25,P75)/ ]Tab.3 Comparison of TMAO and its precursor metaboli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P25,P75)/ ]

表3 2 組受試者TMAO 及其前體代謝物比較 [M(P25,P75)/ ]Tab.3 Comparison of TMAO and its precursor metabolit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M(P25,P75)/ ]
*P <0.05。

表4 肝臟脂肪含量與TMAO、TMA 及膽堿相關性Tab.4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r fat content and TMAO,TMA and choline
2.3 研究對象腸道目標菌群表達量比較
與健康對照組相比,NAFLD 組乳酸桿菌、直腸真桿菌表達量明顯增多,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雙歧桿菌、多形擬桿菌數量明顯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2 組受試者4 種腸道菌群表達量比較 [M(P25,P75)]Tab.5 Comparison of the expression levels of intestinal microbiota in the two groups [M(P25,P75)]
2.4 研究對象TMAO 和腸道菌群之間的關系
將4 種腸道菌群表達量的計算結果與TMAO水平進行相關性分析,結果顯示TMAO 水平與直腸真桿菌表達量呈正相關(r=0.280,P<0.05),與雙歧桿菌的表達量呈負相關(r=-0.332,P<0.05),與乳酸桿菌、多形擬桿菌表達量無明顯相關(P>0.05),見表6。
2.5 研究對象飲食結構比較
對研究對象飲食結構問卷的結果進行差異分析(等級以A=4,B=3,C=2,D=1 進行分析),結果顯示NAFLD 組與健康對照組受試者在膳食搭配、每周食用魚類頻率的差異上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余飲食結構無明顯差異(P>0.05),見表7。進一步對飲食結構與肝臟脂肪含量進行相關性分析發現,肝臟脂肪含量越高,受試者膳食搭配上葷菜占比越多(r>0,P<0.05),每周食用魚類的次數越少(r<0,P<0.05),見表8。

表7 飲食結構在2 組間的差異Tab.7 Differences in dietary structur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表8 肝臟脂肪含量與飲食結構的相關性(n=118)Tab.8 Correlation between liver fat content and diet structure(n=118)
3 討論
許多證據表明,肝臟和肝外脂質代謝異常是NAFLD 進展過程中的中心驅動因素[14],血脂異常是NAFLD 的共同代謝特征,其特征為TG 升高、HDL-c 降低、LDL-c 升高[15]。NAFLD 與肥胖密切相關,肥胖人群中NAFLD 的患病率及其危險因素已經引起了相當大的關注[16]。
本研究結果顯示,NAFLD 患者年齡、BMI、腰圍、肝功能、血脂、尿酸、糖代謝指標明顯異常,提示年齡、BMI、腰圍、血脂異常都是NAFLD 的危險因素,與糖脂代謝密切相關,肝臟脂肪堆積影響肝功能,特別是ALT 和GGT,可促進NAFLD 的進展。與健康對照組相比,NAFLD組胰島素抵抗指數(HOMA-IR)明顯升高,進一步驗證了胰島素抵抗在NAFLD 發病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在飲食結構方面,若葷菜比例較高、魚類等白肉較少的飲食可能促進NAFLD 發展。
目前NAFLD 的臨床診斷涉及各種程序,如血液檢查、B 超、瞬時彈力描記術和MRI,但在臨床實踐中很難區分非特異性癥狀(HBV 相關肝炎、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這表明臨床應用中仍然需要有效和可重復的生物標志物[17]。
TMAO 作為腸-肝軸的代謝產物,對心腦血管疾病、慢性腎臟病等疾病的影響得到越來越多證據的支持[18-19],而與NAFLD 關系的研究相對較少。Flores-Guerrero JL 等[20]發現血漿TMAO 濃度與NAFLD 患者的全因死亡率相關。在本研究中,NAFLD 組相比健康對照組TMAO 及前體物質TMA 水平明顯增高,且TMAO 水平與肝臟脂肪含量呈正相關性,顯示血清TMAO、TMA 水平與NAFLD 的存在和嚴重程度存在不良關聯,推測TMA/FMO3/TMAO 作為腸道菌群驅動的一個通路,可能促進NAFLD 進展。
有研究顯示,TMAO 可能是通過降低總膽汁酸池大小、限制膽汁酸的腸肝循環;并通過改變膽汁酸的合成和運輸來逆轉膽固醇運輸、葡萄糖和能量平衡的方向,影響肝臟胰島素抵抗及脂質沉積,從而導致脂肪組織炎癥反應[21-22]。
膽堿作為人體必需的營養物質,具有多種生物學功能,參與多個體內代謝過程,如果膳食攝入膽堿減少、膽堿內源性生物合成受損,或膽堿的生物利用度降低,都會增加肝內脂質,導致脂肪肝形成[23]。在本研究中NAFLD 組相比健康對照組,血清膽堿水平明顯升高,推測NAFLD 患者可能是膽堿生物利用度降低,導致肝臟脂質堆積。
大量臨床和動物研究表明,NAFLD 的發展與腸道微生物群失調密切相關,其中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之間的平衡改變發揮重要作用,多種菌參與調節腸道內TMA 的合成[24-25]。Cho C.E 等[26]研究顯示,血清TMAO 水平較高的人群厚壁菌門與擬桿菌門的比值增高,而TMAO 水平較低人群的厚壁菌門與擬桿菌門比值減小。本課題組前期研究也發現了腸道菌群結構在NAFLD 患者的改變,其中乳酸桿菌、直腸真桿菌數量明顯增多,雙歧桿菌、多形擬桿菌數量明顯減少,其中多形擬桿菌為擬桿菌門代表菌,直腸真桿菌為厚壁菌門代表菌[13],本次研究結果與之相符。筆者研究還發現血清TMAO 水平與直腸真桿菌表達量存在正相關性,與雙歧桿菌存在負相關性,2 種菌群都只是各種所屬菌門中的1 種,這可為我們探索TMAO 與各菌門之間關系提供依據和方向。
本研究的不足之處:首先,TMA/FMO3/TMAO作為一個物質代謝通路,本研究僅檢測了研究對象血清TMA 和TMAO 的水平,未能采集到足夠的肝臟樣本檢測肝組織FMO3 表達水平。其次,TMAO 及其前體代謝物水平受飲食因素影響較大,筆者進行飲食結構問卷上著重調查受試者日常的飲食結構,未明確到取樣前的飲食攝入種類及量,未能更好體現TMAO 及其前體代謝物與飲食的關系。另一方面,在本研究中納入的健康對照組例數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更多的證據支持,進一步探索TMAO 在NAFLD 中的作用。
綜上所述,腸-肝軸是NAFLD 發生和發展的關鍵組成部分,連接腸道微生物群和肝臟的確切機制是復雜的,且腸-肝軸的靶向性一直是代謝性疾病的焦點,并可能成為未來預防和治療NAFLD 的當務之急,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以TMAO 為靶點探索NAFLD 的防治手段,首先推薦改善生活方式和控制飲食,飲食成分是增加人體循環中TMAO 及其前體代謝物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合理的膳食搭配可能對NAFLD 起到積極的影響。從TMAO 生成的途徑看,腸道微生物群在其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可將改變腸道菌群的組成作為策略,同時,抑制TMA/FMO3/TMAO途徑有望成為治療NAFLD 的新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