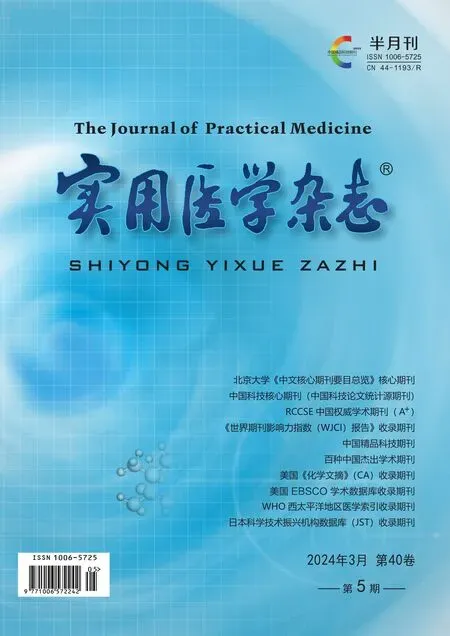肥大細胞在膿毒癥中的作用研究進展
王君靈 湛萌萌 張釗龍 何韶衡 秦秉玉
1鄭州大學人民醫院河南省人民醫院重癥醫學部 (鄭州 450003);2錦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變態反應與臨床免疫研究中心 (遼寧錦州 121001)
膿毒癥是由細菌、病毒、真菌等病原微生物感染引起的機體的免疫功能失調所致的危及生命的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以機體早期過度的炎癥應答和后期免疫抑制為表現的免疫功能紊亂為主要特征,以寒戰、發熱或體溫過低、心慌、氣促、精神狀態改變等為主要癥狀[1-2]。近年來,盡管抗感染治療和器官功能支持技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膿毒癥的病死率仍高達70%,已超過心肌梗死,是重癥醫學病房內病死率較高的疾病之一[3]。因此,膿毒癥是嚴重威脅人類的生命健康的疾病,給家庭、醫院和社會帶來了沉重的醫療和經濟負擔。
肥大細胞(mast cell,MC)是機體抵抗病原微生物入侵的第一批免疫細胞之一,作為天然和適應性免疫應答中的經典效應細胞,MC不僅通過直接吞噬病原微生物、形成胞外陷阱和釋放抗微生物介質等直接發揮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活化后還可通過分泌預先儲存的炎癥介質和細胞因子等誘導吞噬細胞和炎癥細胞募集、活化等調節機體的免疫應答進而參與膿毒癥發病[4-6]。雖然迄今據PAUL EHRLICH首次報道MC已有近150年的歷史,然而,直到近年來隨著免疫、分子和基因組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們才逐漸揭開MC的神秘面紗,把曾經忽略的MC放在免疫學的重要位置[7-10]。鑒于此,本文就MC及其前體細胞在膿毒癥中的作用研究做一總結,期望為以后探索MC在膿毒癥中的作用機制提供新的靶點。
1 MC的來源
MC起源于骨髓的造血祖細胞,在血液循環中分化為肥大細胞前體細胞(mast cell progenitor,MCp),而后進入與外界環境相通的結締組織和黏膜組織的血管和神經周圍,最終在局部生長因子如IL-3、IL-4、IL-9、IL-10、IL-33、CXCL12、NGF、TGF-β等的作用下發育為成熟的MC[11],并且成熟的MC一般不參與血液循環[12]。2016年DAHLIN等[13]學者首次報道人外周血MCp的鑒定分子:Lineage-CD34+CD117+FcεRIα+外周血單個核細胞,然而,其在人外周血單個核細胞中的比例僅為0.005 3%,其中約75%分化為CD117+FcεRIα+Tryptase+的MC。值得注意的是,在過敏性哮喘患者誘導痰中鑒定出了Lineage-CD34+CD117+CD13++/- FcεRI+MCp;此外,WU等[14]于2022年用單細胞測序技術揭示了人外周血CD34+造血祖細胞中FcεRI的出現和MC的基因特征間的時間相關性,并發現長期培養FcεRI+造血祖細胞可形成形態、表型和功能成熟的MC。但是,至今尚無鑒定人血液MCp的其他相關報道。目前僅有一項報道稱造血干細胞因子預處理的小鼠盲腸結扎穿刺(cecal ligation and puncture,CLP)4 d后其存活率顯著增加,并與MC密切相關[15]。鑒于造血干細胞因子可誘導MCp增殖和分化為MC,并可誘導MC成熟和募集[16],上述研究提示造血干細胞因子可能通過促進MCp增殖分化為MC并誘導其成熟進而在膿毒癥中起保護作用。此外,人們雖然對小鼠骨髓Lineage-CD117+Sca-1-Ly6c-FcεRIα-CD27-integrinβ7+T1/ST2+MCp和外周血Lineage-CD117++ST2+integrinβ7++CD16/32++MCp進行了廣泛研究[17],但是,迄今尚未開展膿毒癥患者和膿毒癥動物模型血液MCp的相關研究。
2 MC通過直接殺傷病原微生物而在膿毒癥中起保護作用
MC是機體免疫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膿毒癥小鼠模型的研究發現,CLP誘導的膿毒癥小鼠脾臟、淋巴結、回腸和結腸組織MC數量增加[18];各種微生物及其產物如超抗原和毒素或化學合成物刺激靜止的MC后,可誘導MC活化并進入一個多階段的過程:核膜解體、染色質釋放到細胞質中、含抗病原微生物肽LL-37和組蛋白、類胰蛋白酶等的細胞質顆粒黏附在新出現的DNA網上,而后形成胞外陷阱并釋放到細胞外[19];分泌抗微生物肽如抗菌肽[20]、防御素[19]和血清滅菌蛋白[21],表達模式識別受體如TLR2和TLR4、糖化蛋白如CD48、補體受體如CR3和CR5、免疫球蛋白受體如FcγR和FcαR等[4-5]直接吞噬、內化、殺死病原微生物,從而降低病原微生物負荷、防止病原微生物進一步傳播進而抑制膿毒癥的發生[22-23](圖1)。總之,MC可通過直接殺傷病原微生物而在膿毒癥中起保護作用。此外MC表達可與T細胞相互作用的MHC I、MHC II和共刺激分子,然后發揮其提呈抗原的功能進而促進機體清除病原微生物[24]。

圖1 MC在膿毒癥中的保護作用Fig.1 The protective effects of MC in sepsis
3 MC在膿毒癥中的間接保護作用
眾所周知,MC通過誘導血管舒張、增加血管通透性、募集炎癥細胞、促進適應性免疫應答、調節血管生成和纖維化等進而參與過敏和其他炎癥性疾病。MC表達多種受體,如IgE、IgG、干細胞因子、補體和細胞因子受體,活化后可激活相關信號通路最終釋放一系列生物活性物質,主要包括預先儲存的炎癥介質如肝素、組胺、類胰蛋白酶、類糜蛋白酶等;新和成的炎癥介質如LTB4、LTD4、PDG2等;以及細胞因子如IL-5、IL-6、TNF-α等,進而誘導吞噬細胞和炎癥細胞募集、活化等調節機體的免疫應答[25]。如圖1所示,基于MC分泌產物的研究發現,MC可能通過分泌溶神經素降解神經緊張素和分泌類糜蛋白酶降解內皮素-1來調控血壓進而提高膿毒癥鼠的存活率[26-27];通過釋放預先儲存和新合成的介質如類糜蛋白酶、組胺、5-羥色胺、肝素、TNF-α等誘導巨噬細胞和中性粒細胞等吞噬細胞募集、活化進而發揮抗微生物作用[4-5,28],而IL-15可通過抑制類糜蛋白酶活性進而降低膿毒癥鼠MC介導的抗菌活性[29]。此外,MC可分泌誘導白細胞、血小板、內皮細胞和上皮細胞黏附分子表達上調進而募集炎癥細胞至感染部位、促進細菌清除的TNF,可分泌誘導B細胞增殖分化漿細胞并分泌抗體、增強吞噬細胞吞噬殺菌功能的IL-6,可分泌抑制內源性肽如內皮素和神經緊張素毒性的CPA3等在膿毒癥預后中起重要的保護作用[28]。過繼轉輸LPS體外刺激后的CD4+CD25+Treg細胞可誘導多菌性膿毒癥鼠腹腔MC募集和分泌TNFα,并提高其細菌清除率和生存率[30]。而MC耗竭的膿毒癥鼠中性粒細胞遷移增加、全身炎癥反應加重且病死率增加[31]。值得注意的是,過敏原致敏似乎可通過增強MC脫顆粒誘導的急性炎癥反應進而提高膿毒癥小鼠的存活率[32]。總之,MC分泌的細胞因子和炎癥介質在抑制膿毒癥發病和提高膿毒癥鼠的預后中起重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保護作用似乎在中度膿毒癥中較為明顯[28]。此外,目前尚未開展人MC及其分泌的細胞因子和炎癥介質在膿毒癥發病中的作用研究。
4 MC在膿毒癥中的致病作用
盡管如上所述,但是MC在膿毒癥中是一把雙刃劍,有報道稱MC在膿毒癥中起重要的致病作用(圖2):MC可誘導機體反應失調進而增加感染的發病率和中重度膿毒癥病死率[28],可降低LPS誘導的膿毒癥鼠的體溫[33],通過抑制膿毒癥鼠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進而加重膿毒癥[34]。此外,MC分泌的IL-6和二肽基肽酶I可增加膿毒癥鼠的死亡率[35-36],分泌的IL-4可抑制巨噬細胞吞噬細菌的功能[37]。MC脫顆粒可誘導大腸桿菌誘導的膿毒癥豬毛細血管通透性增加[38],多菌感染性膿毒癥腹膜炎小鼠MC脫顆粒后其病死率增加[39],而蛋白酶抑制劑烏司他丁可能通過抑制CLP誘導的膿毒癥大鼠小腸組織MC脫顆粒增加而改善其預后[40],更重要的是,MC穩定劑色苷酸鈉預處理小鼠可通過抑制膿毒癥小鼠的炎癥反應進而降低其病死率[41-42]。最近的研究發現,肥大細胞活化可通過組胺依賴途徑誘導膿毒癥小鼠血腦屏障損傷和認知功能障礙[43]。可見,MC在膿毒癥惡化和病死率增加中也起重要作用。鑒于此,也有學者提出MC在膿毒癥中的保護和致病作用可能與膿毒癥的嚴重程度和肥大細胞的活化狀態有關[28]:MC在中度膿毒癥中起保護作用,在重度膿毒癥中則發揮其致病作用;抑或與僅感染部位或全身MC活化有關。但是,尚需進一步證實。

圖2 MC在膿毒癥中的致病作用Fig.2 The pathogenisis of MC in sepsis
此外,也有研究報道大鼠細菌代謝產物LPS處理后其丘腦組織MC脫顆粒減少[44],這似乎為人們了解MC在膿毒癥中的活化程度增加了疑問。而金黃色葡萄球菌可體外誘導MC分泌致炎因子IL-3、IL-13和TNF-α但對其誘導的腹腔感染無顯著影響[45]的發現提示MC可能不是清除膿毒癥致病微生物的主要細胞群。
5 展望
綜上所述,MC可能根據其分泌的細胞因子和炎癥介質的微環境調控其病原微生物清除能力及周圍炎癥細胞的功能,進而在膿毒癥中發揮保護或致病作用。近年來,人們雖然通過動物實驗對MC在膿毒癥中作用進行了廣泛研究,但是,目前膿毒癥急性期、緩解期、中度和重度患者血液MCp的數量、組織MC的活化狀態及MC分泌的炎癥介質和細胞因子在膿毒癥發病中的作用及其相關機制研究均尚未開展。鑒于此,基于MC活化開展膿毒癥發病機制的相關研究對于了解膿毒癥的發生發展、診療及其相關生物制劑的研發以及提高和保障膿毒癥患者的生活質量和身體健康有著極其深遠的意義。
為了進一步了解MCp、靜息狀態下的MC和活化的MC及其分泌的細胞因子和炎癥介質在膿毒癥中的作用及其相關機制,有必要開展以下工作:(1)收集膿毒癥不同時期患者和鼠的血液標本和PLF,分析MCp和MC的數量,及MC的活化狀態,檢測其分泌的細胞因子和炎癥介質的水平;(2)開展人和鼠源的MC系如HMC-1和RBL-2H3的相關試驗,檢測MC系的活化狀態及其分泌的細胞因子和炎癥介質的水平;(3)建立膿毒癥動物模型前后,體內注射上述水平發生變化的細胞因子和炎癥介質,然后分析MCp和MC的數量,及MC的活化狀態,并探究上述指標與實驗動物的癥狀、體征和病死率的相關性;(4)免疫磁珠分選膿毒癥患者和動物的MC,蛋白質和轉錄組測序以探究上述細胞因子和炎癥介質在膿毒癥發病中的潛在機制;(5)Western blot和RT-PCR明確其具體機制。本文期望為以后開展MC和MCp在膿毒癥中作用研究提供理論和實驗基礎,進而對膿毒癥的預防和診療提供新的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