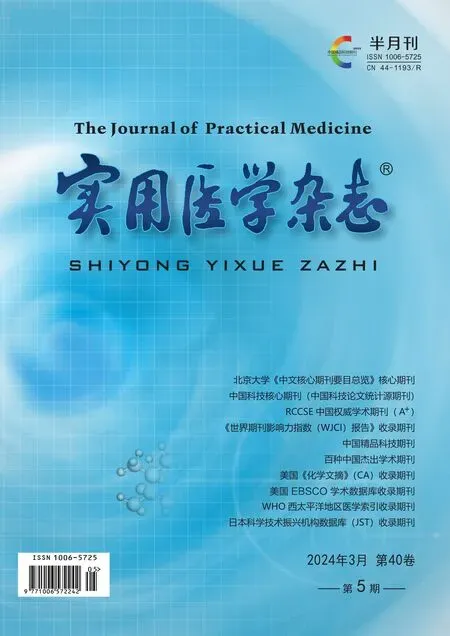腺病毒介導的血管內皮生長因子聯合干細胞生長因子治療嚴重肢體缺血的實驗研究
鐘睿 王家寧 張蕾 郭凌鄖 楊建業 鄭飛 晏譽文 余丹麗 譚利國
湖北醫藥學院附屬人民醫院1心內科,2臨床研究所,3消化內鏡中心 (湖北十堰 442000)
近年來缺血性疾病在臨床上愈發多見[1],其中由嚴重肢體缺血(CLI),導致的截肢、致死事件受到了重點關注[2],其危害性不遜于冠心病或中樞血管疾病[3-4]。目前CLI主要治療方式包括外科手術治療、藥物治療、腔內介入手術治療等[5],但遠期效果均不十分理想[6],1年肢體保存率僅為5%[7],如何提高CLI的治療效果一直困擾著臨床醫師。CLI治療的關鍵在于血管重建,近年來以進血管生成生長因子(VEGF)、肝細胞生長因子(HGF)為目標的基因治療已經成為CLI治療研究的熱點[8-9]。VEGF可作用于血管內皮細胞,促進血管內皮細胞增殖,誘導血管新生[10],是當前研究較多的促血管生成因子。動物實驗指出VEGF可通過激活動脈特殊信號增加血管密度,調控動脈形成[11]。臨床研究[12]則發現,肌肉內注射質粒VEGF治療血栓閉塞性脈管炎的效果顯著,可減輕患者靜息痛,降低患者截肢風險。HGF同樣是一種強效促血管生成因子,國外研究[13-14]已證實,肌肉注射裸體HGF質粒可顯著改善肢體缺血,且治療安全性良好,但目前鮮有將兩種促血管因子聯合用于治療CLI的相關報道。本研究將從細胞學實驗和動物實驗模型的基礎上探討腺病毒介導的VEGF-HGF(Ad-VEGF-HGF)基因治療對缺血組織血管生成的影響,以期為臨床治療CLI提供一種新的治療方法。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用基因本實驗所用基因Ad-VEGF、Ad-HGF、Ad-VEGF-HGF由湖北醫藥學院附屬十堰人民醫院臨床研究所提供,通過實驗動物福利倫理委員會審查(編號:2023010)。
1.2 試劑BCA試劑盒,ECL化學發光試劑盒(Yeasen 公司,36208),兔α-Tubulin 抗體(Sigma 公司,05-829),兔VEGFA多克隆抗體(武漢三鷹公司,19003-1-AP),兔HGF多克隆抗體(Abcam 公司,ab24865),辣根過氧化物酶(horse radish peroxidase,HRP)標記的羊抗抗小鼠(Jackson公司,C0152)及羊抗兔二抗(Jackson公司,C0151),兔CD31多克隆抗體(Abcam 公司,ab32457),小鼠SMA單克隆抗體(Santa Cruz公司,sc-53142),小鼠VEGF(武漢欣博盛,EMC103.48)及HGF ELISA試劑盒(武漢欣博盛,EMC037.48)。
1.3 構建下肢缺血模型昆明小鼠84只,SPF級,6 ~ 8周齡,體質量22 ~ 30 g,購于湖北積步醫療科技有限公司,喂養于湖北醫藥學院附屬人民醫院動物實驗動物中心。將84只昆明小鼠隨機分為假手術組4只,空白對照組、VEGF組、HGF組、VEGF+HGF組各20只小鼠。
異氟烷氣體麻醉,常規消毒,以左下肢近卵圓窩處為起點,剪開皮膚,鈍性剝離,充分暴露股動脈和靜脈,使用4-0無菌縫合線結扎股動脈及靜脈制備下肢缺血模型。將0.5 mL 1010 pfu:Ad-VEGF,Ad-HGF,Ad-VEGF-HGF以鹽水5 mL稀釋10倍注入對應分組小鼠左下肢肌肉中,每只小鼠注入0.2 mL。后于術后7、14、28 d分次用測下肢血流量,計算左側患肢與右側健肢血流比值。
1.4 HE染色和免疫組化將石蠟包埋好的各組腓腸肌組織按5 μm/片進行連續切片。將切片置于二甲苯溶液中浸泡20 min,隨后按照降濃度梯度原則先后將切片置于無水酒精、95%酒精、75%酒精、45%酒精中浸泡5 min,最后將切片轉至蒸餾水中浸泡5 min,最后再進行切片染色。HE染色將切片先用蘇木精染液染色15 min,1%鹽酸酒精分化10 s,然后再用1%伊紅染色3 min,最后用酒精梯度脫色后樹脂封片,顯微鏡下觀察并拍照。
免疫組化:切片常規脫水后,首先利用0.01 mol枸櫞酸鈉緩沖液(pH為6.0)進行抗原修復,3%H2O2溶液封閉內源性過氧化氫酶,然后分別加小鼠CD31多克隆抗體(1∶200)及小鼠SMA多克隆抗體(1∶100),37 ℃恒溫環境中孵育40 min,PBS沖洗3 ~ 4次,每次5 min,后向每張切片上滴加50 μL HRP-羊抗小鼠二抗,室溫避光孵育20 min,PBS清洗3次,每次5 min。最后用DAB顯色液,顯微鏡下觀察并照相,計數新生血管。
1.5 Western blot提取各組小鼠左側下肢腓腸肌組織蛋白,BCA工作液測定蛋白濃度,然后按每孔20 mg的量進行SDS-PAGE凝膠電泳,電泳結束后將含有蛋白的凝膠轉印至PVDF膜上,將膜用5%的脫脂奶粉室溫孵育30 min進行封閉,然后加入兔VEGFA抗體多克隆抗體(1∶500),兔HGF多克隆抗體(1∶500),4 ℃孵育過夜,TBST清洗3次后,室溫孵育二抗2 h,ECL化學發光試劑顯影并拍照。
1.6 ELISA使用ELISA法檢測Ad-VEGF-HGF小鼠血清的VEGF和HGF的表達水平,操作嚴格按照說明書進行。建模24 h后,采集各組小鼠左心血(5 mL),分離血漿。空白孔中滴加標準品,其余反應孔中加入不同濃度的標準液或標本溶液,每個反應孔中液體量均為100 μL/孔,隨后用用封板膠紙封閉反應孔,將孔板置于36 ℃恒溫孵育90 min,每個實驗組3個重復。流水沖洗5次后,向每個反應孔中滴加生物抗體工作液100 μL,封板,36 ℃恒溫孵育30 min。100 μL/顯色底物36 ℃恒溫孵育15 min,最后每個反應孔中滴加100 μL終止液,振蕩混勻后上機,檢測OD450值并記錄。
1.7 安全性分析統計建模成功率以及各組小鼠治療期間有無不良反應發生。
1.8 統計學方法使用SPSS 26.0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多組間對比采用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P<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采用Graphpad Prism 9.4版本軟件對圖形進行繪制。
2 結果
2.1 缺血后肢血流流量建模成功后,各組小鼠缺血后左下肢血流流量均顯著下降;術后第7天,各組小鼠缺血后左下肢血流流量均明顯優于術后即刻(P< 0.05),且Ad-VEGF-HGF組小鼠缺血后左下肢血流流量明顯優于其他各組(P< 0.05);術后第28天 Ad-VEGF-HGF組小鼠缺血后左下肢血流流量逐步穩定,組間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0.05),見表1及圖1。
表1 建模前后左側缺血肢體血流流量/右側健肢血流流量Tab.1 Blood flow of left ischemic limb / right healthy limb before and after modeling ±s

表1 建模前后左側缺血肢體血流流量/右側健肢血流流量Tab.1 Blood flow of left ischemic limb / right healthy limb before and after modeling ±s
注:與術后即刻相比,#P<0.05;與同期空白對照組相比,*P<0.05。與同期VEGF組相比,△P<0.05;與同期HGF組相比,▲P<0.05
時間空白對照組VEGF HGF VEGF+HGF術后第28天0.82 ± 0.76#0.89 ± 0.85#0.86 ± 0.82#0.97 ± 0.93#*術前1.03 ± 0.98#1.05 ± 1.03#0.99 ± 0.97#1.02 ± 0.98#術后即刻0.47 ± 0.40 0.40 ± 0.36 0.36 ± 0.34 0.42 ± 0.40術后第7天0.67 ± 0.61#0.69 ± 0.68#0.65 ± 0.63#0.80 ± 0.77#*△▲術后第14天0.79 ± 0.74#0.89 ± 0.85#0.85 ± 0.83#0.99 ± 0.95#*

圖1 缺血后下肢血流流量比值Fig.1 Lower limb blood flow ratio after ischemia
2.2 Western blot術后第7、14、28天時假手術組、對照組的HGF、VEGF的表達水平最低,Ad-HGF組、Ad-VEGF組、Ad-VEGF-HGF組HGF蛋白、VEGF蛋白表達水平均明顯高于對照組(P< 0.05),且術后第14天Ad-VEGF-HGF組的表達水平達到相對峰值,見圖2-4。

圖2 Western blot檢測Fig.2 Western blot detection

圖3 術后各組不同觀察節點VEGF、HGF表達水平Fig.3 Expression levels of VEGF and HGF at different observation nodes in each group after operation

圖4 VEGF-HGF組術后不同觀察節點VEGF、HGF蛋白表達水平Fig.4 VEGF and HGF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at different observation nodes in vegf-hgf group after operation
2.3 ELISA檢測注射Ad-VEGF-HGF組小鼠VEGF蛋白、HGF蛋白表達水平在術后第7天開始逐步升高,并于術后第14天達到相對峰值,術后第28天時表達水平逐步降低,術后第14天時與其他各時間節點表達水平相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 0.001),見表2及圖5。
表2 VEGF、HGF蛋白表達水平變化Tab.2 Changes of VEGF and HGF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s

表2 VEGF、HGF蛋白表達水平變化Tab.2 Changes of VEGF and HGF protein expression levels ±s
注:與術后第14天相比,#P < 0.05
指標VEGF HGF P值< 0.001< 0.001術前34.24 ± 1.05#1.89 ± 0.80#術后第7天36.99 ± 9.80#5.19 ± 1.75#術后第14天88.79 ± 23.22 7.26 ± 0.38術后第28天23.98 ± 0.46#4.20 ± 0.73#F值83.86 14.01

圖5 ELISA檢測Fig.5 Changes of detected by ELISA
2.4 免疫組化法檢測缺血后下肢新毛細血管密度術后第7天、術后第14天、術后第28天時觀察和計數新生血管,Ad-VEGF-HGF組血管新生較為明顯且數量較多,組間a-SMA所標記新生血管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01),其中對照組各時期的a-SMA所標記新生血管水平最低,術后第14天VEGF+HGF所標記新生血管水平最高,見圖6。

圖6 SMA水平Fig.6 Levels of SMA
免疫組化CD31染色結果顯示,術后第7天、第14天、第28天時觀察和計數新生血管,組間CD31所標記新生血管水平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0.001),其中對照組各時期的CD31所標記新生血管水平最低,術后第14天Ad-VEGF-HGF組的CD31所標記新生血管水平處于相對峰值,見圖7。

圖7 CD31水平Fig.7 Levels of CD31
3 討論
CLI的主要治療方法是恢復患肢血流,緩解缺血疼痛癥狀,血運重建,具體方法包括外科手術治療以及藥物治療等[15],但臨床觀察發現部分CLI患者臨床獲益并不顯著,截肢率并未見顯著下降[16-17]。隨著醫療技術的不斷發展,基因治療逐漸展示出優勢[18],血管生成基因治療試驗被視為對不同類型缺血的一種較有前景的新興療法[19],其中VEGF和HGF基因是目前研究最多的基因[20-21],M?KINEN等[22]使用經皮腔內血管成形術向CLI患者注射重組腺病毒-VEGF165基因,結果顯示這兩種基因工程構建體能增加血管化。BAR?等[23]研究指出,與VEGF相比HGF可能在血管生成過程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且HGF對血管內皮細胞的促進和增殖作用強于VEGF[24],故HFC可能是治療缺血性疾病中某些關鍵因素。基于上述研究推測VEGF與HGF在促進血管新生方面具有協同增效作用,聯合這兩種基因有望進一步提高CLI的治療效果,但目前尚且缺乏實驗論證。
本研究Western blot檢測結果證實Ad-VEGFHGF組小鼠體內VEGF、HGF蛋白持續高表達,術后第14天后即達相對峰值,此后逐漸降低,除術后第28天外,Ad-VEGF-HGF組小鼠體內VEGF、HGF蛋白表達水平均明顯高于其他各組。同時,研究通過血流儀探測發現,術后第14天時,Ad-VEGF-HGF組小鼠的血流流量便出現了明顯恢復,血流恢復速度明顯優于VEGF組、HGF組及對照組,這與Ad-VEGF-HGF組VEGF、HGF蛋白的表達狀態變化基本一致,由此可見Ad-VEGF-HGF雙基因注射后可發揮協同作用,進一步上調VEGF蛋白和HGF蛋白的表達水平,另一方面也證實了HGF和VEGF均可促進血管新生,這與RIAUD等[25]動物實驗結果較為類似,該研究指出VEGF和HGF基因的共轉移在缺血性骨骼肌中產生了強大的血管生成效應,并可能成為治療缺血性疾病的潛在治療組合。但在促進血管新生過程中,是VEGF還是HGF發揮了主導作用尚且無法明確。安全性一直以來都是基因治療重點關注的問題。早期病毒載體的基因治療研究[26]指出以腺病毒為載體進行VEGF基因治療冠心病缺血的效果良好,且未發生嚴重不良反應,而本研究以腺病毒為載體聯合了VEGF基因和HGF兩種基因,這兩種基因是否會增加基因治療風險著實需要重點關注。本研究結果顯示小鼠建模成功,各組小鼠實驗期間均未出現嚴重不良反應,未出現死亡小鼠,由此可見Ad-hVEGF-hHGF基因治療的安全性。
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未明確VEGF聯合HGF如何調節血管內皮細胞功能,促進血管內皮細胞增殖,哪種基因發揮了主導作用,作用劑量是否會對其促血管作用產生影響等,上述問題仍有待今后進一步深入探究。
綜上所述,Ad-VEGF-HGF基因注射可顯著提高小鼠體內VEGF和HGF蛋白的表達水平并快速達到相對峰值水平,繼而進一步促進下肢缺血后的血管生成,增加血流量,改善下肢循環。